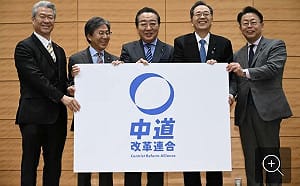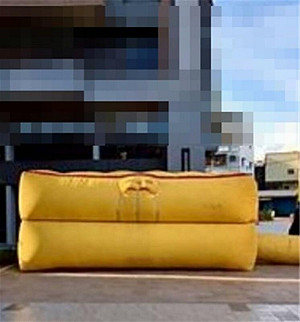《馮光遠(儘量)回憶錄》連載第十四篇,講述在留學期間做過的校內清潔、圖書上架、餐館和賣鞋等工作,因緣際會還曾服侍過桑塔格穿鞋子。對馮光遠而言,打工在某種意義上,其實也象徵著一種工人子弟出身的認同。
去康州唸書,兩個好處,一是,這是全美最富裕的幾個州之一,二是,鄰近紐約市。富裕,打餐館工的話小費高;近紐約市,週末去紐約市方便。而這些算計,後來都派上用場。
前情提要:
懷念年輕時那些打工的日子(上)

出國還是要打工:校內清潔、圖書上架、餐館、賣鞋
第一個學期,功課大致安定之後,我先是申請合法的校內打工,結果校方提供的是清潔工(custodian)的職位,修剪樹木、清潔大樓、整理教室,這些活,挺簡單但是無趣。
做了一陣子,工頭告訴我,圖書館有個缺問我想不想去,原來是負責圖書上架的 shelving supervisor。去面試,館長一看我圖書館背景,馬上錄用。
從此,手下有十幾二十個工讀生歸我調度,更重要的是,因為既然已是學校教職員,除了有工資,上課修的學分也免費,這讓爸媽鬆了口氣。
為了看電影而賣鞋
邊工作邊修課已屬忙碌,可是我還是利用週末去打餐館工,甚至去紐約市一家鞋店賣鞋子,這兩個工,考驗我的是與陌生人互動與應變的能力。
我尤其懷念鞋店的工作,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因為那個店緊鄰格林威治村重要的電影院 Bleecker Street Cinema,鞋店打烊,就是我去隔壁看電影的時間,看完,回鞋店睡覺(跟老闆的協議之一)。第二天,再繼續看電影及工作。
一個週末,應該都可以看上兩部電影,這很重要,因為 Bleecker Street Cinema 是一個放舊片以及藝術電影、獨立電影的戲院,我這輩子看過最難忘的一些電影,都是在這個小戲院看的。
打工:沒有負擔、刻意的叉路、放空...
打工這事,對我人生的一個重要影響是,它讓我在生活上,跳脫了千篇一律的白領族群的思維方式。我的意思是,在打工的這段時間裡,我不必去擔心五年之後的我;或者,盤算著年終獎金什麼的;又或者,寫一個你得翻找政府公報才寫得出來的文章。
那是一段相較之下比較沒有負擔的人生。因為你正在做的,可能與你原先設想的人生也許相去很遠,所以你毫不在乎;也許,那根本就是一段你刻意要走的岔途小路,你樂在其中;或也許,你就是需要一段時間的放空。
更重要的是,你會因此遇見許多在你設定的人生軌道裡,絕對無法遇見的人與事。
我也插得上話 「我服侍過桑塔格穿鞋子」
以鞋店的工來講,因為店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中心區,夏天,總是營業到很晚。
有一回,一個喝太多的義大利裔妹子跟朋友走進來,一個踉蹌,她就這麼絆倒在試鞋沙發區,上圍兩個雄偉的藝術品,就這麼極其自然地滑出,搞得大家都很尷尬。幸好店裡人不多,她的男友(大概吧)不動聲色地在她毫無知覺的情況下把它塞回去,沒有造成太大的騷動。
另一回,則是(美國的作家、評論家、文化觀察家及社會活動家) Susan Sontag 與兒子進來買鞋子,驚呆,後來,我在台北聽到文化人談桑塔格如何如何時,我也因此能驕傲地插話,「喔,桑塔格的腳挺大的,我服侍過她穿鞋子。」

打工作為一種認同:出身工人子弟
之所以始終懷念打工的日子,因為,打工,於我而言,在某種意義上,其實也是一種認同。
我是一個在三重埔長大的小孩,記得上中學時,有一天,父親跟我聊起印製廠的工作,父親的一句話我始終印象深刻,「爸爸的工作雖然是會計,可是我是印製廠的人,所以,我是工人,不是公務員。」
工人子弟,如果真要論,這就是我的出身。
早年的三重埔,還沒有真正的建設,家住在淡水河附近,有一天,小學下午沒有課,便偷偷地騎著母親的腳踏車(前面沒有擺小孩座椅的那一條橫槓),在家附近亂逛,越逛越遠,直至淡水河畔。
日常就足以佇留獃望
我記得在河堤上看到遠處一排房屋,夕陽下,幾位女子坐在屋前聊天、收拾著晾曬的衣服、嗑瓜子,我就安靜地在河堤上,隔著一段距離,望著她們的日常,看至出神。
那個景,雖然已經幾十年了,還是歷歷在目;當天晚上回去,急得到處在找我的父親,還沒有等我停好腳踏車,藤條便已上身,一頓好打。那一幕,印象清晰,跟了我幾十年,記憶中,這也是我小時候唯一挨打的一次。
其實,諸如在河邊佇留獃望的往事,如今回想起來,竟然隱隱約約,都與階級之事有關。之所以提此事,因為,某種生活樣貌,於我而言,就是比較親切,就是與自己個性契合,就是與自己對生活的一些想望合拍。

閃現的遠早鏡頭
於是,某個懶散的下午,要我腦裡回憶一些遠早鏡頭的話,也許會是:
冬天清早坐 24 路公車去台北上學,擠在前面,享受司機旁邊引擎蓋散發出來的溫暖;去三重金國戲院看完電影,出戲院,再在腳踏車停車棚看幫派鬥毆;父親請鄰居家拉三輪車的阿伯載奶奶去醫院;擠在有電視的鄰居家窗口,緊張地觀看台灣與菲律賓籃球賽轉播。
這些,以及後來讀某些作家(如魯迅、王拓、黃春明、王禎和等人)的小說,看新寫實主義的電影(在台北「台映」放映室、紐約的 Bleecker Street Cinema 等影院)。
雖然,這些鏡頭在時空上都相距甚遠,似乎毫無瓜葛,可是,經由丁點蒙太奇的概念、些許基本連結的能力,在回憶那些日子、作品的瞬間,再連結到打工之事,竟然就是很自然地想到那個晚上,父親淡淡地跟我講的那句話,「我是工人,不是公務員」。
關於【馮光遠(儘量)回憶錄】
「馮哥(我們都這麼叫馮光遠),你有講不完的故事,寫個回憶錄吧?!」
他半開玩笑又不失真實地說道:「寫回憶錄的人,多少有些自戀耶」
看來他拒絕。
「回憶應該是紀實,寫得開心,不小心就虛構起來了。」他繼續說道。
「沒關係,寫多少是多少,太…真實,大家壓力也大。」我們小心地應著。
「好,那我就儘量囉!」馮哥啜飲著泥煤威士忌,邊回答。
《馮光遠(儘量)回憶錄》企劃於焉形成。
這是兩年前的事。
不過,認識馮哥都知道,他已經很「儘量」了。
作者:馮光遠,曾任記者、作家、編劇、攝影、劇場工作者及政治人物,《中國時報》主筆、副總編輯。馮也是《給我報報》、憲政公民團創辦人,也曾受聘金石堂書店擔任行銷創意總監,主持電視評論節目及發表幽默與政治諷刺文章。自稱「國寶級白目」,曾因《囍宴》得到金馬獎最佳編劇,馮光遠也以嘲諷幽默表現方式,介入公民運動進、政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