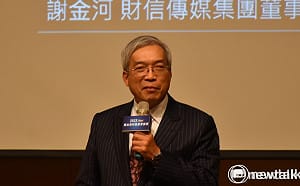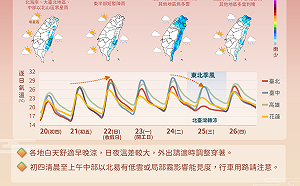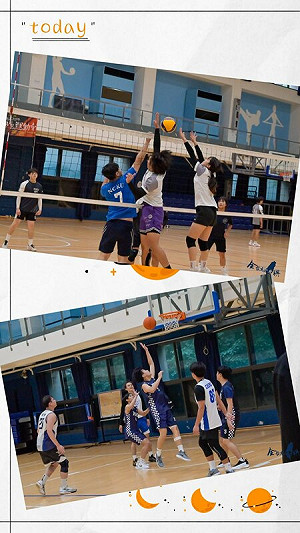本文嘗試透過解密的官方文件稍稍撥開歷史迷霧,將真相還給一整代的台灣人原日本兵及其子孫後代。
二戰期間,多達二十萬七千多個台灣子弟在日本殖民下,以軍伕、軍屬、勞務、志願兵等身分投入戰場(以下統稱為台灣人元日本兵),大約有五萬人戰死或失蹤;這在台灣歷史上是極為重大的悲慘經歷。
國民黨凍結日本海陸軍部台銀存款 薪資安家撫卹...都終止
數十年來,如此重大的歷史卻被中國國民黨政權禁斷或掩沒。而無論戰歿或順利生還的台灣人原日本兵,其權益及補償竟然也遭中國國民黨政權出賣了。
國民黨政權這段可恥的羞史,同樣地被它以政治力隱匿,如今台灣人原日本兵幾乎即將凋零殆盡。本文嘗試透過解密的官方文件稍稍撥開歷史迷霧,將真相還給一整代的台灣人原日本兵及其子孫後代。
在戰爭期間,台灣人元日本兵除了薪津由日本軍方發放之外(戰爭末期因情勢混亂曾出現應領而未領的情況),在台家屬也由日治下的台灣總督府發放安家費,如遇傷亡,台灣總督府也有一定數額的撫卹。
日本投降後,所有作業都被迫中止,初期,由台灣總督府改組的「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曾提撥臨時軍事費,對返台者發給在海外應領的薪津,但是,後來日本海陸軍部在台灣銀行的存款,遭國民黨正府全面凍結,而無法發放。
現正最夯:冬奧中國突破零金牌 謝金河批台灣部分人「愛別人國家、阻礙自己」

國民黨一拖再拖 台灣人原日本兵無法善後
返鄉的台灣人原日本兵及其家屬在那段過渡期不斷陳情,當時為了解決他們的生活困境,在國民黨政權控制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曾決定由「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出具證明,持向國民黨政府府軍政部特派員辦公處借領台幣三百元。
但軍政部不願承辦【註一】台灣銀行也已無款可墊推辭,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該署財政處幾度更改救濟辦法,幾個單位依舊互相推託,直到「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撤銷,國府一拖再拖經年搞得下文不明。
至於台灣人戰歿者,是由日本政府入祀日本靖國神社,可是,戰歿者家屬及生還者的補償就一直懸宕未決。
日本政府在戰後對戰爭期間徵召的軍人訂定了《恩給法》及《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等援護法》,分別對戰歿者遺族及生還者進行補償。
然而,其中竟有國籍限制的條款,也就是只針對具有日本國籍者才予以補償,台灣人原日本兵戰後因喪失日本籍而被排除在外。
補償排除台灣人元日本兵 杉山美也子:日本違反國際人權
日本學者杉山美也子批評:「這是違反了國際人權規約 B 規約第二十六條(內外人平等原則)的規定、而通過這些法律的日本國會議員也是有重大的責任問題。」
她批評:「從其他國家的殖民地補償事例來看。比如英國對印度、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義大利對利比亞、美國對菲律賓等在戰後獨立成為不同國籍時、對戰死傷者的補償還是由本國政府支付給當事者本人、並沒有因喪失國籍而不予補償。」【註二】
後來當日本學界及法律界協助台灣人元日本兵推動索賠時,日本輿論也針對日本政府的責任進行檢討。《朝日新聞》在一九八五年以社論同樣特別舉出其他兩個戰敗國的例子,提到國家道德問題:
「跟日本一樣,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的西德及義大利,戰後,對其舊殖民地出身的戰歿者遺族,完全跟本國人同樣地支付各種補償金,台灣人元日本兵及其遺族的補償問題,是屬於日本的國家道德問題,絕不得再擱置下去了。」【註三】
這種主張正是後來索賠運動展開時日本學界與律師界義務協助的重點精神,更是促使日本國會通過補償法案的核心動力。

美國主導 《日華合約》處理雙方財產依據
經過延宕後,有關台灣人原日本兵的身分及補償問題又牽涉到兩個條約:《舊金山和約》和《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簡稱《中日和約》或《台北和約》,本文以下使用通稱的《日華和約》)。
日本是在 1951 年與美國及其它同盟國成員簽訂了《舊金山和約》,結束戰爭狀態,放棄了台灣及澎湖諸島的主權。
那麼,台灣人原日本兵戰歿者遺族及戰傷病者的撫慰,以及被積欠的薪資與軍事郵政存款等債務問題如何處理呢?
由於國民政府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並未受邀參加《舊金山和約》的簽訂,因此,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才在美國主導協助下與日本簽訂《日華和約》,作為處理雙方財產、債權的依據。
《日華和約》第三條載明:「關於日本國及國民在台灣及澎湖之財產,及其對於在台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所作要求(包括債權在內)之處置,及該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在日本國之財產及其對於日本國及日本國國民所作要求(包括債權在內)之處置,應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國政府間另商特別處理辦法。本約任何條款所用『國民』及『居民』等名詞,均包括法人在內。」

蔣介石擺爛不處理 大內宣為「以德報怨」
根據這項條文,台灣人原日本兵的財產及債權,必須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國政府「另商特別處理辦法」,這是在日本無情的國內法——《恩給法》及《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等援護法》——之外的補救處理。
日本政府根據該條文分別於一九五五年六月七日、一九六○年十一月、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以及一九六五年七月,「共計三次(筆者註:應為四次)主動向台灣的中華民國提出交涉,要求共同處理兩國人民財產的問題。可是,中國國民黨政權對於日本的要求卻是從頭到尾都沒積極回應過。」【註四】
日本政府這四次交涉無功而返,到了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日華和約》失效後更無所謂的交涉協商。
重點是國民黨政權自始即對日本主動交涉一事的消息全面封鎖,反而以「以德報怨」進行大內宣洗腦,極力為蔣介石造神。

主動放棄索賠? 國民黨四度拒絕協商
曾被以「戰犯」關押在新幾內亞達五年之久的簡茂松,獲釋後定居於日本,他在日本向中國國民黨政權提出第二次交涉之前的一九五八年,和三十餘位同樣滯留日本的台灣人BC級「戰犯」組織了〈台籍戰犯同志會〉,兩度向日本政府展開索賠行動,引起國民黨政權的注意。
當時,廖文毅正在日本如火如荼推展台獨運動,國民黨蔣政權為了反制台獨運動而亟思攏絡居留日本的台灣人,便邀請該團體改以〈留日青年同志會〉名義返台參觀。
該會後來於一九七一年向蔣介石寄送陳情書,他們一廂情願地希望國民黨政權出面協助處理補償問題,沒想到竟受到蔣介石的接見。

簡茂松在其口述傳記《我啊!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簡茂松的人生》(濱崎紘一著)一書中描述,他們向蔣介石表示,「中華民國不應該在中日和約中,明言放棄對日本索賠的權利,並且應儘快與日本政府展開請求權的談判。」
國民黨兩面手法 體恤日本又操作日本虧欠台灣人日本兵
簡茂松等人顯然受國民黨政權的錯誤宣傳影響,而且尚不知道國民黨政權已經四度拒絕日本的主動協商的事,蔣介石在會見時也刻意迴避他們有關談判索賠的訴求,顧左右而言他的答覆竟然是:
「日本人在戰敗之後陷入空前的困境,藉此機會趁火打劫,實非我輩所應為。」、「我們應該原諒日本的罪行,反過來讚揚他們的功績才對!」【註五】
蔣介石所謂體恤日本困境、原諒日本的罪行,其實都是托詞,是在掩飾絲毫不顧台灣人元日本兵困境與權益的咎責。
簡茂松:台灣人被日本人欺負 還被外省人糟蹋
長期以來,中國國民黨政權不但體恤日本而犧牲台灣人權益,更且非常可惡地刻意操作形塑日本虧欠台灣人日本兵的印象,結果讓台灣人原日本兵不斷在台、日之間疲於奔命地進行索賠行動。
蔣介石隱匿日本政府曾四度要求跟國民黨政權協商的內情,顯然深藏不道德的政治謀策。
簡茂松說:「事後回想起來,我心中不禁暗自叫屈:『哼!說的比唱得好聽!你們這些外省人從大陸撤退到台灣來,不費一兵一卒便接收了所有日本人的資產,對你們來說當然划算,可是我們台灣人可慘了,不但被日本人欺負,還得被外省人糟蹋,你老的這一套我們可受不了!』」(同註五)

在蔡岳熹著《叢林中的山櫻花——高砂義勇隊二十八問》一書中,明白指出中華民國政府規避交涉協商的原因是:
「因為在一九六○年代,日本人的在台財產不是被霸佔成黨產就是已經成為私產,所以,中華民國當局當然是能賴就賴,能推就推!」、「中華民國政府只想將日人財產據為己有,所以,就連帶將台灣人日本兵的權益出賣掉!」
國民黨拒絕協商 林啟旭: 不讓被統治的台灣人受益
長期在日本與王育德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林啟旭【註六】,涉入旅日台灣人結合日本學界發起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的行動甚深,他在一九八五年從日方獲知國民黨政權在斷交前四度拒絕日本政府的協商,便撰文指出:
「國民黨政權為迴避其二十年來不替台灣人元日本兵向日本政府討債的責任,謊說如果向日本政府討債,日本政府一定會向國民黨政權要求日本人留在台灣的財產,這是詭辯。....其實,國民黨政權真正的心態是『(依照日華合約)這種協議就算成功,其受益者也只不過是被統治者台灣人而已,對統治者中國人來說,這種問題完全無意義。』」【註七】
林啟旭還指出:「日本政府不早日補償台灣人元日本兵及其遺族,實有失國格及信譽,這一血債不管如何費時日,如何費精神,非討回不可。」
更深層原因 避免助長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印象
他強調:「但我們同時也不可以忘記,這一問題為什麼會拖到現在還不能解決的原因,這是因為國民黨政權不想也不願替台灣人討回這一筆血命所致的債。」,索討補償的行動漫長、艱鉅,他更揭露了一個少為人知的內幕:
「十數年來,國民黨及中國對在日本推動補償運動的『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一貫採取阻礙的態度,國民黨及中國不但不願意看到舊敵人——台灣人原日本兵領到日本支付的補償金,同時也怕這一運動的成功,助長日本人認為台灣人異於中國人的想法。」【註八】
日本《朝日新聞》在一篇專訪報導中,也同樣透露了國民黨政權處處破壞的內情,證實林啟旭的指控:
「這一補償問題....使台灣人王育德為中心的『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十數年來,不眠不休的奉獻所造出來的成果。國民黨政權不但不同心協力,處處造謠,想破壞『思考會』的運動,藉以促使台灣人元日本兵及其遺族領不到補償金,....日本人不能理解國民黨政權為何阻礙。」【註九】
中村輝夫印尼叢林躲藏 30 年 台灣人日本兵始受日本社會矚目
有關台灣人原日本兵的補償問題,必須回溯到中村輝夫成為國際矚目新聞這件事。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台灣人元日本兵中村輝夫(中文漢字名為李光輝、原住民名為史尼育唔)在印尼模羅泰島叢林躲藏了將近三十年後被發現,滯留印尼治療期間一度發生遣返哪裡的問題。
國民黨政權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用盡各種計謀讓日本同意將他遣返台灣。
期間因日本政府只發給中村輝夫微薄的欠餉費、歸鄉費,共六萬八千日圓,卻與先前發給日本軍人至少一千萬至二千萬日圓相比,根本天差地別,引起日本國內輿論的強烈譴責。之後,有關台灣人元日本兵權益問題才受到日本社會矚目。
針對中村輝夫的賠償,日本民間有志人士結合國會議員展開支援行動,日本政府後來才又發給三百五十萬日圓補償費。
台灣人日本兵補償 王育德、郭榮桔分進合擊
受到中村輝夫個案的啟發,一九七五年在日本先後出現了兩個團體:〈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一九七五年成立)、〈台灣人元日本兵軍事貯金遺族年金要求委員會〉(一九七七年成立);前者由日本明治大學教授宮崎繁樹領銜,時任同校教授的台灣人王育德擔任事務局長;後者是由旅日〈台灣同鄉會〉會長郭榮桔主導推動成立。
兩個支援團體成員包含了日本國會議員,以及學者、律師等民間有志人士,展開訴訟行動,受挫後改走立法途徑,才有一九七七年由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組成〈台籍前日本兵補償問題探討議員懇談會〉予以應援。
追索過程非常冗長,最後是透過日本國會於一九八七年九月、一九八八年五月,相繼特別立法通過《有關對台灣住民戰歿者遺族等之弔慰金等之法律》、《有關特定弔慰金等實施支付之法律》,規定台灣人原日本兵的遺族及戰傷病者當事人若提出申請並獲認可,每人將獲得二百萬日圓的特定弔慰金。
1995 年日本決定補償 120 倍率 國民黨主導立法院事不關己
有關懸而未決的積欠薪資及軍事郵政存款等,是屬於日本對台灣人原日本兵的「確定債務」,支援團體主張必須考量台灣經濟成長率、日本自衛隊薪資水準及物價等因素,要求賠償倍率要定為一千倍到七千倍才合理。
日本超黨派國會議員於一九九四年三月組成〈台灣戰後處理問題議員懇談會〉來台,立法院此時倏然甦醒過來,應景成立〈立法院處理民間對日債權委員會〉作為溝通對口。
結果,等到日本政府於隔年(一九九五年)決定償還債務金額落差甚大的一百二十倍,台灣的立法院這個時候竟反而事不關己地噤聲。

連戰:國民黨對日「債務多於債權」
不過,在日本國會懇談會1994年訪台時,國民黨政權也知道長期出賣台灣人元日本兵權益的真相已經無法繼續隱瞞,才由時任行政院院長的連戰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六日,以〈台八十三外字第一六二四二號〉公函回復立法委員質詢時坦承:
「依民國四十一年中日和約第三條規定,中日兩國政府及人民間債權債務之處理,應由兩國政府商議特別辦法解決,日方並要求雙方債權債務須同時處理。和約簽訂後,台省同胞屢次要求政府協助索還對日債權,日方亦曾多次要求我國依照中日和約第三條規定,商訂特別處理辦法,以解決兩國間債權債務問題,惟我政府以對日債務多於債權,對日方請求會商處理辦法,均設詞婉拒。」
連戰的行政院函文雖然刊載於立法院公報上,可是,不僅原本提出「書面質詢」的立法委員只是為了湊熱鬧作秀,一點都不在意行政院的答覆而不了了之,並且立法院公報也少有人看,因而並沒有引起外界的關注。
「日本虧欠台灣人原日本兵」的印象依舊普遍存在於台灣社會。
至於行政院函文中所提到的「債務多於債權」,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誠如上述簡茂松、蔡岳熹所說的,日本在台灣五十年統治期間的公、民產業投資,以及為了大東亞戰爭所做的軍經儲備,都極為龐大,再加上終戰時多達三十萬日本僑民的民間財富就更難以計數【註十】。
「設詞婉拒」原因 中國國民黨獨吞日本財產
中國國民黨政權進行軍事接收及遣返日僑時,日僑均赤貧如洗地離開台灣,國民黨政權把他們留下的財產全部當作「戰利品」獨吞。
軍事接收後,能被國民黨軍所用的物資都運往中國支援國共內戰,其餘的也頻生私吞的情形,整個接收過程形同「劫收」【註十一】,當然必須橫心耍賴「設詞婉拒」了。至於究竟有多少債權、多少債務,幾十年來始終成謎,外界根本無法窺探一二。
最近筆者翻查解密的官方機密文件發現,1951 年國民黨政權被拒參加的《舊金山和約》簽署後,台灣民間獲知日本即將與國民黨政權簽署和約,便紛紛透過各縣市議會及台灣省臨時省議會陳情,要求國民黨政權務必向日本請求清償台灣人的戰爭損害及保險賠償金。
國民黨政權 1945 年以占領者姿態瘋狂收刮,根本帳目不清,但為敷衍蜂擁民怨,才開始著手盤查跟日本之間的債權、債務。
當時國民黨政權駐日代表團曾密電外交部,要求委派會計專家赴東京,對日方有關資料作進一步的調查,但國民黨政權顯得漫不經心,下令駐日代表團隨便指定人員負責辦理即可【註十二】。
接著,一九五二年四月《日華和約》簽署後,國民黨政權的外交部及財政部又根據該和約規定召開緊急會議,會商如何進行蒐集及調查國民黨政權接收的日產,以及台灣人民對日有關財產債權債務及作戰損失等事項有關資料。做出三點重要的結果:
「....(二)台灣省公產管理處所接收之日產,應由該處再加整理,提出最後報告。....(四)台灣省人民在日本之財產及其對於日本及其國民(包括法人)之要求(包括債權),應呈由行政院「密令」台灣省政府「密請」台灣省議會主辦調查事宜,省議會在辦理中遇有必要時,應表示係該會「自動辦理」。....(六)台灣公產管理處所保管之日產,應儘速設法出售。」【註十三】

其中最奇怪可疑的是第四點與第六點,為什麼必須「密令」、「密請」?又為什麼要省議會說謊揹責任是「自動辦理」?主要原因是國民黨政權早有計謀耍詐搞騙局,這從第六點下令儘速設法出售日產便可得到證明,因此,這項蒐集及調查的結果完成後,即被國民黨政權列為極機密長期隱匿。
接著來看「債務多於債權」的真相。解密的檔案資料顯示,一九五二年六月,台灣省公產管理處根據查報作成「台灣省接收日人財產統計報告」,該報告臚列接收的「日人財產」只有日本人私有財產及日本人企業財產兩大類。其價值均以一九四五年八月終戰時的價值為準,截至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五日的總價值如下:
——日本人私有財產價值:舊台幣(係指日據時期之台幣,下同)十四億零五百零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三元六角九分。
——企業財產價值:舊台幣九十八億九千七百五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六元七角二分。
——以上兩類合計共達:舊台幣一百一十三億零二百五十八萬五千七百六十元四角一分。

至於台灣人在日財產及對日債權,經台灣省政府整理統計後,總計為舊台幣八十億三千二百四十七萬一千七百八十七元八角三分。【註十四】
兩者差額達舊台幣三十二億七千餘萬元,也就是: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劫收」的日產,比台灣人在日的財產,多了舊台幣三十二億七千餘萬元,這是「債務多於債權」真相或實像的一部分。
為什麼說是「一部分」?因為數額極為龐大的公產部分,則完全沒有計算在內。國民黨政權是以日本已在《舊金山和約》及《日華和約》內,「放棄或承認放棄其對於台澎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為由,主張其在台澎之公產亦應隨之放棄,日方不能再提歸還要求。至於接收日人財產部分,其實遭國民黨政權官方隱匿或運往中國,以及接收官員私吞分贓,數量多到無從統計而同樣根本未列入。此處就不再贅述有關「管轄權」的複雜問題了。
繞了一大圈談「債務多於債權」,證明國民黨政權對於實質的財產清算如此公然耍賴,對於清查龐雜的台灣人元日本兵權益當然更虛應故事了,況且台灣人元日本兵要索賠的軍郵儲金、簡易保險及欠餉等等是屬於「確定權益」,國民黨政權明知與一般債權債務性質不同,竟仍刻意迴避而不想由政府出面,完全推責給雙方國會議員磋商。
結果,國民黨政權的國會自始作壁上觀,全靠日本國會設法處理。除了前述林啟旭所言的原因之外,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國民黨政權政策上要抹除台灣人曾參與太平洋戰爭的這段歷史記憶,而只能有黨國強力灌輸的八年抗戰史。
因此,它在一九九○年代以前的數十年間拒談這段歷史,台灣人原日本兵在極權高壓下當然更懼談這段歷史,即使對自己親人亦復如此。

相對於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卸責,同樣遭遇類似問題的南韓在一九六五年就已解決,當時南韓是以政府對政府跟日本簽訂兩項條約:《日韓基本條約》及《財産及び請求権に関する問題の解決並びに経済協力に関する日本国と大韓民国との間の協定》(日本和大韓民國關於財產和索賠問題的解決和經濟合作的協議)來進行處理。蔡岳熹認為,南韓能坦然、迅速解決的關鍵,就在於沒有像中國國民黨政權「將日人財產據為己有」,更沒有「霸佔成黨產或已經成為私產」。
韓、日簽約解決的時間,正是日本政府第四次找國民黨政權協商之際,如果國民黨政權沒有拒絕日本政府的話,也許可以談妥對台灣人原日本兵更為有利的條件。
日本國家道德問題遭到檢討,國民黨政權則刻意排拒維護台灣人元日本兵權益、卸責諉過的醜態,在行政院前項〈台八十三外字第一六二四二號〉公函中暴露無遺之外,行政院在該公函中竟然厚顏攬功地指出:
「政府為爭取國人權益,經多年努力,洽促日方結果,日方已同意人道精神自七十七年起支付台籍原日本兵本人或家屬每名二百萬日元弔慰金,....近兩年來,復鑒於台籍原日本兵軍郵儲金、欠餉等與中日間一般債權債務性質不同,迭透過各種管道,洽促日方儘速考慮,幣值變動等因素,以合理倍數償還我方債權人。」
整份公函充斥了無恥謊言,國民黨政權在整個索賠過程中只有想方設法破壞,哪來「政府為爭取國人權益,經多年努力,洽促日方結果」?竟將台、日雙方民間長達十餘年的努力成果一概抹煞。
當然,日本政府的決定仍然引發了許多抗議與反彈聲浪,可是,日本官方認為補救措施開始實行後,有關台灣人元日本兵的賠償問題「已獲得解決」。
由於國民黨政權拒絕官方接觸,而其立法院純為作秀,與日本國會懇談會的會商流於形式,最後,日本的補償作業被迫只能透過雙方的紅十字會,根據日本官方的統計,截至申請期限為止,透過兩國紅十字會的對口提出申請者只有二萬九千九百餘件,支付的金額合計五百二十九億九千萬日圓。
申請件數占台灣人原日本兵復員總數還不足二成,其原因是:國民黨政權敷衍的公告未能普遍週知,以及眾多不滿歧視性的微薄補償而拒絕領取。
日本政府最終的處理定案後,日本國內的聲援團體「功成身退」,但要求合理賠償及維護尊嚴的行動並沒有停止。
在台灣國內仍有許昭榮領導的〈全國原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繼續奮力訴求,另有部分台灣人原日本兵在人權律師及〈社團法人自由人權協會〉協助下,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控訴日本政府。
近年更有年邁的台灣人元日本兵向日本法院訴訟爭取「日本人身分」國籍,可以理解,時隔數十年之後,這些行動只是了卻不甘的心願而已。
惟隨著索賠問題塵埃落定及台灣人元日本兵逐漸凋零,許昭榮開始致力於對台灣人國府兵、台灣人原日本兵的關懷,以及喚醒台灣人歷史記憶的推動,後來繼承許昭榮遺志所成立的〈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也肩負起追趕歷史列車的口述記錄和台灣戰爭史的學術研討。
後續的發展是大家所熟知的,那就是:對於台灣人每三戶就有一戶子弟參與太平洋戰爭的重大歷史記憶,中國國民黨政權不但絕口不提或徹底禁斷,反而三不五時炒作「慰安婦」的議題。
台灣人原日本兵在戰時是「日本人」,是中國人的「敵國」,國民黨政權出賣他們的權益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似乎顯得理直氣壯、心安理得,反過來又政治操作「慰安婦」議題,其實不是矛盾,而是充斥著詭詐與虛偽,說到底,避談台灣人原日本兵的權益是怕自己的瘡疤被揭開,只談「慰安婦」議題則旨在進行仇日的情緒動員。
台灣人原日本兵遭受國民黨政權的仇視或歧視,再試舉一例說明。終戰後,各機關、事業機構除了主管職位多數由中國人佔有,原基層職務的台灣人幸運者在職缺緊縮景況下尚能保有職位,當時有少數在戰爭末期被日本徵召,服務地點是在台灣島內,終戰後獲得復職,他們自己因曾「替日軍服役」,如果他們有眷屬在「省外」,就不能比照中國人申請「眷屬津貼」;即使他們沒有被徵召,但其眷屬在「省外」曾「替日軍服役」,同樣不能申請「眷屬津貼」。這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於一九四六年的明令規定,具見了仇視台灣人/台灣人原日本兵的顯著差別待遇。【註十五】

有不少台灣人原日本兵後來涉入二二八事變而受害,時隔多年後,仍有一些台灣人元日本兵遭到秋後算帳,試舉一九五七年的兩個例子略作說明昨為本章的小結。
第一例受害的是兩個人。盧陳貴富(原名陳忠寶,時年三十七歲,台北縣人,業商)、謝錦德(時年三十九歲,彰化縣人,業商),他們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在香港日軍服役時,因獲悉日軍南洋戰況失利心存畏懼,乃共商偕同盧妻吳麗英投奔中國,因為對中國複雜的情勢不了解,誤入中共東江縱隊政治部駐地「白鶴寺」,被迫接受共黨身家調查,交付自傳,參與學習檢討為時約半月。
不久,日軍投降,他們復受中共「巴萊隊」指揮,等到「巴萊隊」領導人林真宣佈解散後,盧陳貴富由英軍收容至民國一九四六年一月遣送返台。謝錦德則由國民黨軍收容於第二十集宿所,同年三月遣回台灣。
他們返台後曾向治安機關坦白自首登記,並沒有為中共工作活動情事,但在一九五六年被翻出舊帳而莫名其妙遭逮捕;軍事檢察官竟以他們曾受過中共的訓練,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將他們裁定交付感化。【註十六】

第二例的受害人是鄭春河(日名上杉重雄,時年三十八歲,台南縣人)。他在太平洋戰爭時是台灣人原日本兵(昭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入陸軍兵志願者訓練所),終戰返鄉後一直擔任豐成粉廠業務員,數年間,他都曾與當年同時服役的日本人保持通信來往,早就被國民黨特務鎖定監控,一九五七年有三封信遭到查扣羅織罪名而逮捕。
一封是當年二月二十一日,寫給在日本鄉公所擔任總幹事的友人江籐利男,信中提到:「....此間所皆知之大轉變為百八十度也,弱肉強食,俗語有錢便生、無錢便死,有了金錢死刑也可得無罪,想起來甚為羞恥之現象,現在有勢之人全部於抗日時之人所掌著」等語。
另兩封是當年五月二十六日,分致身染肺病賦閒在家的日人福岡卓郎,及在日開雜貨店的高木榮,函中都提到:
「....報上閱到樺太千島列島將歸還,這也許十年來國民不斷努力之表現,將快成為事實,是值得我們無限欣慰,我們亦確信台灣總有此一天的來臨,且盼望早一日為之,祈禱世界局勢時刻有轉變之可能,我們亦應備待臨機應變的姿態趕上....」【註十七】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雖然認為他「尚非通謀日本政府或其派遣之人,核其所為尚與通謀外國或其派遣之人意圖使中華民國領土屬于他國之情形有別」,但是,「其不滿現狀捏造荒謬事實並希望台灣隸屬外國」,有必要進行思想改造,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裁定交付感化。
這三個案例都是中國國民黨仇日意識型態下的受害者,在那幾年間類似的受害案例不勝枚舉,這與國民黨政權在台灣長期實施仇日教育也息息相關,黨國專制極權統治者無所不用其極地抹除、禁斷、變造、扭曲台灣人的歷史記憶,毫無疑問成為必然的作為與結果,誠如周婉窈教授所言:
「由於台灣人參與日本的對外征戰,在中日戰爭中和中國人站在對反的立場,戰後這段歷史注定要被刻意遺忘的。」、「台籍日本兵為他們因出生、因教育而認同的國家,盡忠盡力,至死無悔,我們在他們身上,不也能看出一些人類社群的高貴情操嗎?」【註十八】
台灣人原日本兵不僅「確定權益」被國民黨政權出賣,以及有些案例遭「秋後算帳」,而且他們絕大多數在終戰初期一年多,還險些被國民黨政權遺棄於南洋及海南島,有關他們在海外的悽慘遭遇,筆者另有專篇詳述,總之,台灣人元日本兵自始即受到國民黨政權惡意的仇視或歧視對待。
然而,日本投降後依國際規範放棄台灣這塊殖民地,台灣人便失去日本國籍,國民黨政權趁盟軍總部交付接收任務之際,曾以行政命令宣稱台灣人自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應一律恢復我國國籍」,撇開這項違反國際法的命令當時已遭盟軍多國反對與質疑不談。
事實上,國民黨政權當年只有佔領掠奪台灣的政治考量,並沒有真正將台灣人/台灣人原日本兵當作「中華民國國民」,才會把整段歷史記憶禁斷達數十年之久,因此,如何在台灣正史上復原重建這段歷史記憶,實在是迫不及待的工作。

作者:邱國禎,資深媒體人。筆名馬非白,出生於台灣台南市,十七歲後常居於高雄市。從事新聞工作之前曾經營出版社,進入新聞界後,歷任民眾日報記者、特派員、採訪組主任、民眾日報社史館館長,編輯部總分稿,以及言論部主筆等職務。為推廣台灣意識,於2000年開辦《南方快報》。著有:《高雄黨外風雲》、《馬可仕的獨裁愛死症》、《搶救台灣》、《近代台灣慘史檔案》等書。
【註一】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財簽字第一一三號。
【註二】杉山 美也子,在「台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的〈關於太平洋戰爭時期的舊日本軍從軍台灣人的戰後補償問題——日本國內法的觀點為中心〉。
【註三】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社論〈追究日本的道義責任,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
【註四】在《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舉辦的,「台灣近代戰爭史(一九四一~一九四九)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彭琳淞發表的〈一視同仁——台灣人老兵運動〉論文,提到這三次日本提出的交涉。此外,蔡岳熹著《叢林中的山櫻花——高砂義勇隊二十八問》,p一三九。蔡岳熹在書中另說:「那些在戰爭期間將薪水存入日本郵政儲金的台灣老兵以及高砂義勇隊員,其實應該找中華民國政府負責才對。」
【註五】《我啊!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簡茂松的人生》一書提到簡茂松事後感想寫道:「事後我回想起來,當天蔣介石所說的一字一句,根本都是與現實不符的謊言。」
【註六】林啟旭於一九五九年加入明治大學講師王育德創立的《台灣青年會》,該會後來改名《台灣青年社》,擴大組織後又改名《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併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後成為該聯盟日本本部;戰後那幾年,全世界只有該聯盟在日本為戰歿台灣人元日本兵,結合旅日台灣人社團舉辦慰靈祭,中華民國駐日代表處竟粗魯拒絕受邀。林啟旭一直是組織重要幹部,在中國國民黨政權聯手日本政府取締該組織時,曾因簽證因素遭日本逮捕而險些遭遣返。
【註七】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發表社論〈追究日本的道義責任,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林啟旭翻譯後刊於一九八五年九月九日在美國發行的《台灣公論報》,這段引述是林啟旭的譯註。
【註八】林啟旭,〈重視政治原則,建立台灣獨立共識〉,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刊於在美國發行的《台灣公論報》。
【註九】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五年九月二日專欄報導〈訪問死傷補償原告代表鄧盛的未亡人鄧蘭英〉,漢譯刊於同年九月十二日《台灣公論報》,譯者林啟旭註解。
【註十】根據「台灣日僑遣送應行注意事項」,遣返歸國的日僑的攜帶行李以一人一擔(三十公斤),限於自己能搬運者為限。對於行李種類、數量都有限制,比方:洗面具種:洗面器一、漱口用杯一、肥皂盒一、毛巾一、牙刷一、....。衣服鞋類(不分男女能穿於身上部分除外):冬服三、夏服三、内衣一、外套一、内褲三、....。其他寢具類、炊飯具類、日用品類等就不贅述。另外,每人僅得攜帶現金一千圓,各準備八天的糧食(集中營四天、船上四天),也就是說,日僑必須赤貧如洗離開台灣。
【註十一】參與台灣接收的海軍少將韓仲英談到「劫收」問題時曾說:「....各地『劫收』的情形,有『四化』(良的化為劣的,多的化為少的,有的化為無的,公的化為私的),有『五子』(鈔子、金子、房子、車子、女子),都是駭人聽聞的事情。」
【註十二】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41=12.6=5=0001=virtual001=0040。
【註十三】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41=12.6=5=0001=virtual001=0021。引文內的「」為筆者所加。
【註十四】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41=12.6=5=0001=virtual001=0049。
【註十五】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通令辰儉(三五)署財字第○五七一二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職員眷屬在省外者眷屬補助費發給標準通令案」(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八日),〈頒發來臺人員旅費及省外眷補費支給辦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24100009002。
【註十六】一九五七年五月六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裁定書(四六)審聲字第三十一號。
【註十七】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裁定書(四六)審聲字第六九號。
【註十八】周婉窈教授《海行兮的年代》中〈日本在台軍事動員與台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一文,該文原刊於一九九五年六月《台灣史研究》第二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