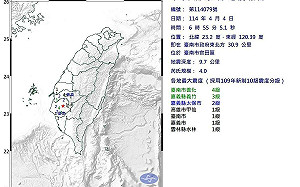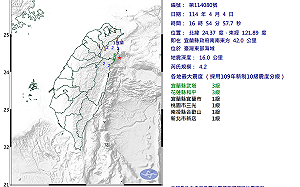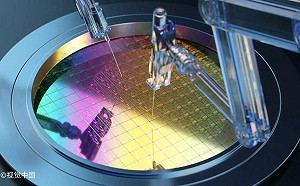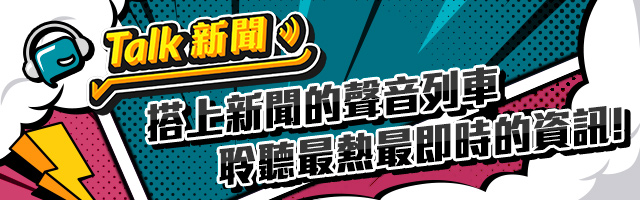2025年,你不離身的手機是否為iPhone系列?而且覺得非常好用。
為何一張由蘋果聯合創始人Steve Jobs用黑色墨水簽名的1983年「蘋果電腦」名片,能以18萬1183美元(約台幣580萬元)的價格售出?
2007年Steve Jobs在發表會上端出首支 iPhone,並強調蘋果「重新發明電話」(reinvent the phone)他高喊了有 5 次之多,這是人類真正創造力入世,正向改變全球的結果。
中國在世界崛起,曾被世界各國期待,而中國教育體制能培養出下一個Steve Jobs嗎?
答案目前未經修正的制度是不行。
我仔細研究中國教育系統,其出了大問題的關鍵在其高考制度的限制。檢視中國高考歷史,2014年9月,中國國務院發佈《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拉開新一輪高考改革的帷幕。目前已經有14個省市啟動高考綜合改革方案,浙江、上海作為首批試點省市,已經完成首輪改革試點,2017年9月全面實行新高考。之後京、津、魯、瓊等第二批試點省份開始分步實施,其他省市區也將完善或發佈高考改革方案。新高考對基礎教育和高校招生開始產生廣泛影響。
再從改革實踐來看,新高考已初顯成效。一是高職院校與普通院校分類考試,減少錄取批次,適應了不同類型高校人才選拔與培養的客觀要求,有利於擴大考生與高校的雙向選擇。二是高校招生標準從單一考試走向多元評價,正在推動高中教育轉型和育人方式變革,引領中學生全面發展。三是高中學業考試改革,擴大了教學科目組合,減少了文理分科弊端。四是結合高考綜合改革,統籌實施和推進修訂後的普通高中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改革教學方式方法,完善教育教學管理,全面系統考核學習成績和綜合素質,促進了中學素質教育的發展。
然而,中國新高考制度實施也面對許多問題和挑戰,包括提出新高考改革面臨價值阻力、制度阻力、社會阻力和自身阻力,而應試教育文化中的考試主義仍如影隨形,學人邊新燦等觀察到公平與效益的兩難制衡及對統一筆試評價模式的路徑依賴,是「應試教育」產生的制度誘因和助燃劑;學歷文憑的出現使教育的功利應試傾向更趨複雜;個體過度功利化、短視化,是「應試教育」產生的直接原因;社會「集體無意識」在公眾道德和文化心理層面給「應試教育」行為提供了支撐,這樣的功利導向,也出現善於考試技術的考生連考三年,錯用高考制度的限制,進行不當獎金獲利。
我也觀察到中國應試文化所帶來的考試主義,仍深刻影響新高考制度的改革成效,包括新高考制度的五項改革措施分1.語數外和選考科目試題或將統一命題;2.實施新課程省份不再制定考試大綱;3.所有科目合格性考試由各省份命題;4.技術和理化生實驗操作可能納入學業水準考試;5.高一最多參加四門科目學考;其改革的目標分別為1.讓考試內容標準化,促進教育公平,提升教育效率;2.解開考試領導教學對學校、老師、學生的長久限制;3.讓地方賦權,增權賦能;4.強調實作能力,不只停留過往只重考試知識和技術;5.讓學校有實施全人教育的制度空間,不讓學生被考試主義所單一限制,但至今大眾所關心的新高考政策解讀,內容大多是選報怎麼樣的學科組合,才能獲得最高分。綜合上述,新高考制度背後所要達到的改革目標,都可能因為應試文化所帶來的考試主義,而產生被忽略等負面的影響。
教育思想家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曾提到:「意識是這個世界偉大的創作者,唯一的再造者」,由此可見意識對於人類的重要性,長久以來,「意識是甚麼?」這一直是人類追問的基本哲學問題。而意識覺醒的定義是什麼?其最主要的功能是什麼?哪一種類型的思維必須以意識覺醒為基礎?弗雷勒認為發展此種批判思維的基礎是個體需有意識覺醒(conscientization),其作用是使個體能察覺,並省思既存現象的形成脈絡與意圖等,據以進行批判,以及引導重建的意向與行動,在這種重新導向追求解放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是在於受壓迫者本身意識的覺醒(conscientization),由於受壓迫者心靈自由必須先於身體自由,而透過教育的過程,使得受教者能先一步擺脫外在不合理的壓迫,與奴役所加諸的心靈枷鎖進而恢復身體的自由,就成了意識覺醒中的最大任務目標。
故下面我將以弗雷勒理論中的意識化教育/受壓迫者本身意識的覺醒(conscientization)、囤積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與提問式(problem-posing)的教學做為本研究的概念分析工具,並一說明如下。
意識化教育/受壓迫者本身意識的覺醒(conscientization)
教育思想家弗雷勒曾提到:「意識是這個世界偉大的創作者,唯一的再造者」,由此可見意識對於人類的重要性,長久以來,「意識是甚麼?」這一直是人類追問的基本哲學問題。而意識覺醒的定義是什麼?其最主要的功能是什麼?哪一種類型的思維必須以意識覺醒為基礎?弗雷勒認為發展此種批判思維的基礎是個體需有意識覺醒(conscientization),其作用是使個體能察覺,並省思既存現象的形成脈絡與意圖等,據以進行批判,以及引導重建的意向與行動,在這種重新導向追求解放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是在於受壓迫者本身意識的覺醒(conscientization),由於受壓迫者心靈自由必須先於身體自由,而透過教育的過程,使得受教者能先一步擺脫外在不合理的壓迫,與奴役所加諸的心靈枷鎖進而恢復身體的自由,就成了意識覺醒中的最大任務目標。
承上,因此「意識覺醒」不僅具備使個體能獨立思考的意義,並包含能讓整體社會重新改造的定義。弗雷勒指出此種「意識覺醒」是歷經「意識半未轉移」(semi-intransitivity of consciousness)、「意識轉移」(transitivity of consciousness)以及「批判意識」(critical consciousness)的進程,而上述「意識半未轉移」意指:「具有此種意識的人是無法領會生物必須性領域之外的問題……意識半未轉移代表人與他們的存在本質產生脫離。在此種狀態,自我覺察是困難,人疑惑於他們對事物的知覺以及對環境的挑戰。」,而「意識半未轉移」的下一階段目標為「意識轉移」,這兩者的差異在於當事者產生滲透覺醒性(permeable),而此種滲透覺醒性的發生,弗雷勒認為是由於以下的原因導致:「當人們發揮自身力量,對自身所處情境所浮現的建議與問題進行感知與反應,並且增加自身能力以進入對話,這不僅與其他人對話,也與他們所處的世界作對話,於是他們意識已開始轉移的。上述引文對話的基礎是來自,個體能對外界進行察覺的思辯,而此種自我覺察能力源自個人的思維,顯而易見,弗雷勒將此種主體性視為人的本有潛能,也是構成人之所以存在意義的原因之一。而「意識轉移」的開始階段是「素僕轉移」(naïve transitivity),弗雷勒曾表示其意義為:「素僕轉移是具有意識的人,這類人幾乎仍然是社會大眾的一部分,發展對話能力,仍然較為薄弱的以及限於容易扭曲的境地,如果未能將此種意識提升到批判的轉移階段,持續下去的話,個人反而被偏執的非理性而形成的狂熱主義所轉移。」。承上所述,接續的階段為「批判轉移意識」(critically transitive consciousness),進入此一階段,個體具有高度的摻悟性,因而能以開放的視野以及主動的態度來檢視既存現象,並對問題作深度的詮釋,弗雷勒曾對其提出一番解釋:「批判轉移的特徵即為真實的民主制度,以及符合生活中高度摻悟、質疑討論與不斷對話等溝通形式……當人進入一個較大的範疇關係時,並且他接收到更大量的建議以及對其所處環境的挑戰時,他們的意識自動變成更具轉移性,然而從素僕轉移到批判轉移的關鍵步驟是不會自動發生的,達到此種步驟將需求彼此主動與互相對話的教育課程,此種課程是關注社會與政治責任。」,總的來說,上述意識覺醒的發展途徑,並非是未經獨立思考便盲目接受他人的觀點,而是個體應作為知識與價值的主體,也是主體的反思途徑,來發覺個人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也看見現存社會現象的特質與目的。
囤積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與提問式(problem-posing)教學
弗雷勒在《受壓迫者教育學》探討傳統囤積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所帶來的壓迫,並提出具有解放性質的提問式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所謂囤積式教育,系指師生關係包含一個講述的主體—教師,與一群耐心聆聽的客體—學生,囤積式教育近似傳統填鴨式教育,知識不斷的囤積,學生只是一個容器,或者機械式的接受器,這種教學法,其實就是一種壓制的工具。
而提問式教育,系指師生間一起合作,在一個對話的情境下,追求人性化,尋求解放。師生間的關係會改變,並呼應意識的本質-意向性(intentionality)-具體展現溝通,一起去探究這個世界,人類知識是一個共用的財產,而非教師所獨有私占,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也同時幫助了學生和教師,一起克服傳統囤積式教育裏疏離的師生關係-教師單向度的自導自演,學生在上課時完全沒有互動討論的對話機會。
可惜的是,有許多運用囤積式教學的教師們,並不自覺他們正進行非人性化的工作,也不明白所囤積之物包含許多與現實不符合的矛盾現象,但學生遲早會察覺,現實是一個過程,會不斷改變,如果人存在的志業是追求人性化,那麼人們遲早會發現囤積式教育存在著許多矛盾,並因此致力於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
接續以弗雷勒理論概念來分析中國新高考制度的問題
(一)意識的覺醒(conscientization)分析新高考制度的問題
由於欠缺逐增的批判意識,人是無法統整調合於自身於一個具有密集改變與矛盾的變遷社會……如同人們擴大他們的言論接受度,以感受並回應於在自身的問題情境而產生的建議與問題,並且提升他們的能力,這不僅能與他人進入對話,並且也與世界作對話,他們變成可改變性……意識改變使人們成為可意識覺醒(的主體),並且此種意識使人以完全投入的方式,取代原本對既存人事物的高疏離感。
從上可知,以弗雷勒理論概念來分析新高考制度的問題,最能發揮的功能向度,就是介入解放這一段因應試文化中考試主義綑綁中國新高考制度的問題,而造成壓迫者(因應試文化中考試主義所綑綁的中國新高考制度)-受壓迫者(學生、老師與其他相關教育人員)關係現象,這樣因制度而造成的受壓迫關係,目前在中國新高考制度的改革中,高中學校仍習慣以追求升學率的考試評價觀來衡量、理解新高考改革的目的、宗旨及價值追求,使得改革的價值追求受傳統考試評價觀的阻礙。如新高考改革要求教師要調整教學組織方式,轉變教育觀念,有調研發現,有的教師的教學方式仍是知識傳授,甚至有教師對改革宣導的教學方式持否定態度。
承上言之,而可能連帶所有參與中國新高考制度改革活動的人、事、物等,轉眼因應試文化中考試主義綑綁新高考制度的問題而變成“受壓迫者”。由於學校、學生、家長等長期受應試文化的影響,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套穩定的教學、學習、評價模式供自己在教育改革場域中使用;面對新高考,他們依舊沿襲傳統的教學、備考方式阻礙改革,例如有些學校依然按照原有的工作思路(根據高考科目與時間安排)安排教學計畫,出現教學碎片化現象。
而受壓迫者(學生、老師、家長與其他相關教育人員)又是如何長期屈服於壓迫者(因應試文化中考試主義所綑綁的中國新高考制度),在受壓迫者的文化潛意識上有另一種詮釋,為何在中國社會大眾的偏好仍是以客觀分數為準繩,考試成績以卷面成績為依據,其來有自,因在中國的社會大眾相信分數面前人人平等,而且這種分數是以不易產生“貓膩”(金錢、人情、關係、權力)的客觀、卷面試題為主的分數,這樣在應試時也就有依據可以遵循。但上述的分數主義所帶來的公平卻不是真正的公平,而是一種“異化的公平觀”,因為這樣的考試選才雖然有強烈的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但卻不能實踐真正的「平等」(equality)。
承上,為何就算分數主義不能帶來真正的平等,社會大眾仍是堅持選擇這樣的考試選才制度,除了應試與分數這樣的選才制度,能排除主觀家庭背景、權力財富、關係主義等不當的影響外,在這背後社會大眾有更深層、更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擋在高考制度改革前,便是社會大眾對於中國社會的信任危機,對現代高考新制度的不信任,及深知關係主義影響了中國社會傳統道德的發展,而這樣的關係主義也相對主宰了中國教育制度與選才分配,社會大眾便意識到古往今來的關係主義帶來「階級再制」與「社會階級結晶化」,人民難以撼動,於是寧願選擇「有分無人」、不能帶來真正公平的應試主義,也不選擇雖能帶來新契機,卻可能被關係主義綑綁更深的素質教育導向中國新高考改革政策,而弗雷勒“意識的覺醒”的運用,正可從應試文化中考試主義所綑綁的新高考制度,究其最根源的意識型態做出檢視,並從中尋找改良之方。
顯而易見,在高考改革行動中,中央和省級政府是驅動高考制度改革的關鍵主體,高校始終屈居配合高考改革的從屬地位,如果決策權力失去應有的監督與制約,就會導致權力腐敗從而損害公共價值,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大學內部都存在這種風險。高校自主招生領域的腐敗問題就是權力不受制約的結果。2018年底浙江省高考成績違規加權賦分的案件也是權力失範導致的,而上述能改進新高考制度改革最大的關鍵,便在於建構更具公開、開放辯證對話的制度決策情境,應讓在新高考制度改革下的政策制定者,老師、學生、家長、社會大眾和相關的教育人員彼此共同對話,盡可能跳脫本位主義的溝通障礙,讓所有人都可以運用弗雷勒“意識的覺醒”,去看到應試文化中考試主義所綑綁的新高考制度,及其最根源的意識型態,如此才能避免已投入大量金錢人力、與各種政策資源的新高考制度改革走向“形式化”的問題,總之,透過運用弗雷勒“意識的覺醒”,才能讓受壓迫者們(學生、老師、家長與其他相關教育人員)意識到自己的問題處境,進而能開始進行現實問題的解決。
(二)囤積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分析中國新高考制度問題
囤積式教育不僅違背民主的概念,也漠視每位學生的獨特文化背景以及生活經驗。因而弗雷勒堅信個體兼具「社會、歷史、思想、交流、轉化與創造性的人」,而隨著知識經濟和資訊社會的快速出現,隨著大規模擴招帶來的高錄取率、高等教育大眾化,統一高考的品質效益受到質疑,統一高考在創新思維培養上的缺陷越來越突出,單一統一筆試考核形式強於培養求同思維能力,弱於求異思維和創新思維能力培養 ,久而久之將對民族素質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從而在溢出制度效益上出大問題。中國歷史的應試文化,就是目前新高考制度所面臨的獨特文化背景,而應試文化身受科舉考試制度直接影響,科舉考試制度不僅對中國社會和知識份子的生活有重大影響,而且還形成了中國的學者氣質和中國尊重人才的風氣,而中國尊重由應試文化所選拔的讀書人,在考試的觀念和制度是中國科舉對世界文明最大的貢獻,對照西方對於科舉考試的態度,雖然西方也推崇科舉對考試公正性做出貢獻,但無中國這樣因科舉制度所延生的應試文化,卻出現一種極化的現象,把社會上極大的財富分配給極小的一群有功名的讀書人,而當科舉制度所延生的應試文化和社會財富分配掛勾時,便開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及許多弊端,包括只注重筆試而不重視辯論的科舉傳統,及過度重視排名順序、強調同質性優秀(培育出特質很像的人),卻忽視異質性傑出的應試文化,而中國這樣的獨特文化帶來筆試能力強、獲取排名順序前三(狀元、榜眼、探花)功名,就能有效得財富、權位的「書中自有黃金屋」途徑,但只重筆試能力忽略辯論能力的應試文化,會弱化重視辯論所培育的批判思考能力,及連帶失去批判思考能力引發創造思考能力的可能性,這都是中國現代高考改革所遇到的歷史難題,與嘗試要完善的教育現代化目標,然後新高考制度背後的獨特文化如同大山一樣,阻隔著原先要透過高考改革讓孩子全面發展的目的地。
承上言之,漠視中國新高考制度背後的獨特文化背景,以及過往歷史中應試文化的考試主義,對社會大眾產生根深蒂固影響,如未周全關注其會產生降低推動新高考制度成效的事實,只有立意良好的新高考改革理念,但在政策行動上卻產生了不一致的現象,例如:面對改革,有些考生卻認為,“我們這屆就是被坑的小白鼠,什麼時候能停止這種瞎折騰!”,有家長認為“改革意圖是好的,但落實中有偏差。比如我主張孩子全面發展,新高考方案也是這個精神,規定10門都得考。但實際上,卻要求學生剛上高一就得把計分的選考科目和發展方向定下來。可上大學還有轉專業呢,過早確定計分科目,實際上更令考生緊張和迷茫”。根據上述真實狀況,可用弗雷勒的理論術語來描述政策目標和行動不一致的現象,這是另一種形構壓迫性的灌輸,是一種囤積式教育的概念的展現,在新高考政策出現目標和結果的不一致,關鍵在於新高考政策未經批判性的提問檢視與修正執行,壓迫的是教育決策與推動過程,灌輸的是未經開放對話,獨立辯證,周全轉化的決策,這是一種“灌輸的過程”,與最後形成“囤積式教育的概念”的結果,這已明顯違背民主教育的概念,也漠視新高考制度背後的獨特教學實務與文化背景,灌輸的是政策決策者,同時也是社會大眾,但最後得到的政策效果,往往是事與願違。
(三)提問式(problem-posing)教學分析中國新高考制度的問題
如同一種人性與解放實踐,提問式教育處於如同是根本地位,受支配的人們必須為他們的解放作奮戰。朝向此種結果,此種教育使教師與學生克服威權主義以及異化知識份子主義,並成為教育過程的主體,此種教育亦能使人們克服他們對於真實的錯覺。
將提問式教學的對話精神與原則,放置在新高考制度的決策與行動,讓每個參與者仍能進行真正使用批判意識來做自由對話,這樣的對話讓每個參與者獲得自由的同時,也能真正地對於問題情境做最適合的回應,例如《教育部關於加強和改進普通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意見》要求建立公示制度、檢查制度、誠信責任追究制度、申訴與復議制度等;然而因上述制度有許多正在探索完善,使得在改革過程中,高中綜合素質評價被高校抱怨其“沒法用”,高中吐槽其“沒有用”,進而能將弗雷勒提問式教學原則與精神正嚮導入新高考制度的決策,當新高考制度出現了壓迫的現象,受壓迫者本身必須對於解放行動有著反省性參與,惟一有效的解放工具是一種人性化的教育學,實現一種共同意向的教育(co-intentional education),正為弗雷勒當年對於囤積式教學批判的原則精神,轉化用於批判反思新高考制度形成的過程與結果,因批判教育的實踐涉及行動(doing),以及對行動的反思(reflecting)之間的一個動態以及辯證運動……甚至理論論述本身也必須具體足夠,藉由行動以成為具清晰性可證明性。
然而,在現今中國社會,教育幾乎依然是中國社會底層上升的唯一通道,高考 緊扣住學生在社會上升的狹隘通道,而通過高考得到高教育地位,對於學生個人與家長家族的命運關係極大 ,導致現今高考依然如科舉考試那樣是高利害考試。庇護式流動下,整個社會對於教育價值的認同具有趨同性,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成為文化潛意識,中國家庭投入到孩子教育之中的時間和資本是西方社會達不到的。
承上論之,而這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成為文化潛意識,至今仍被中國特有傳統文化的標籤保護與包裝著,如果運用弗雷勒提問式教學原則與精神,對此問題做反身性思考,就會發現面對被此特定文化與傳統社會現實綑綁助的高考制度問題,我們走向的是重複解謎的路線,可能為眾人都知道怎麼做高考制度的教育改革,但是卻被中國特定文化和傳統社會現實擋在前面,顧明遠先生便指出高考改革的問題核心:「現在的考試制度還是以分數為標準,將來以能力和綜合素質為標準就好了。但這樣的改革相當困難,因為能力和綜合素質很難具體衡量。中國人講公平,不患貧只患不均,這是中國人的文化,跟國外不一樣。」。在上面論述很明顯指出高考改革的困難點,在於以中國特色文化與傳統社會現實包裝的應試文化難以撼動,而在此,能以弗雷勒提問式教學的原則來做一提問檢視:「是否以特定文化與傳統社會現實來合理化此論述口號,就是助長中國高考制度改革成功的困難度的其中環節呢?」,而目前此教育現象是值得做一深度探究。
(四)人性化(humanize)教育分析中國新高考制度的問題
弗雷勒致力於「人的解放」(human liberation)以及社會轉化(social transformation),旨在喚醒受壓迫者在爭取自由解放過程中產生「意識覺醒」(awakening consciousness),所重視的是人性化社會(humanized society)的建構以及「人性化」(humanize)的教育行動,主張人類存有的使命是成為主體,藉由對話教學論喚醒受壓迫者為解放自己而投入行動,以實踐社會正義和進行社會轉化,並作為其奮鬥的目標,最後並完成人性化的志業(humanizing vocation),而弗雷勒的人性觀,他認為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有基本的存有志業,去成為一個能行動及進行改造的主體。使自己具備更多的可能性,並使生命更加富足。另外,不論是處於何種狀態的人,都應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他的世界,透過與他人的對話,追求個人有意識的人性化,在此弗雷勒強調教育不僅需要不受已失去人性的統治階級的宰制,更要啟迪被統治階級的自主意識,才有可能發展自主化及人性化的文化,一再強調把人當人,而非把人當物看,同理,新高考制度表面上是教育政策制度決策的問題,但內在層面上,我們應該去思考,這樣的教育政策制度是被「人」所制定的,也反映出制度中部分不當的缺陷問題,制度常會出現把人當物看的錯誤,導致教師、學生、家長和相關教育人員產生了壓迫與痛苦,已有了非人性化的問題,也例如會因為人性問題產生其他「非人性化」的負向效應,而學人王中男在〈學習評價價值觀為何會「以分為本」——基於社會.個體維度的雙重審視〉便明確指出:「從社會維度來看,在等級社會中向上浮動,分數是基本途徑;從個體維度來看,實現功利主義價值觀,分數是基本途徑。而無論是「在等級社會中向上浮動」還是「追求功利主義」,皆為人性使然。對於追求以分數為代表的考試結果而言,人性都是深層的動力。」,人性便是形成「以分為本」現象的根本原因,再例如中國高校專項計畫的實施過程中,個別地方官員利用自身影響力將子女戶口改回農村,或把子女送到貧困地區上學爭奪政策優惠的移民現象,諸如上述人性中的自利,會帶來高考改革中非人性化的連鎖教育問題。承上論之,而弗雷勒理論思想,最主要是去除這樣非人性化制度與環境,故其思想必然可應用,只要針對問題採取最「人性化」的問題解決策略,行筆至此,研究者認為弗雷勒在創造理論之前,就因為自己生命處境曾經貧窮過、挨餓過,曾親身遭遇到人性的考驗時刻,因為這樣的生命體驗,所以在做任何的教育決策上,會先考量人性,跳脫不人性化的、打高空的教育政策規劃與配套措施,做出最「人性化」的決定。
行文最後,我認為中國新高考制度所造成的連鎖問題,就是未運用弗雷勒理論思想中的對話精神與原則所出現的結果,而弗雷勒主張必須穿越就有既定價值觀框限,透過批判性思維,來發展出另一種文化的批判性思考,這樣的新思考才有機會突破既有文化傳統與輿論的不利限制,運用思想工具解開既有決策者被舊我的工具理性所捆綁的困局。
中國目前教育方式已經出了問題,卻自己騙自己繼續合理化錯誤制度。故我特別以Paulo Freire批判教育學檢視中國高考制度。而我在下一篇文章會論述說明,台灣這個國家為什麼可能做到培育下一個Steve Jobs。
文.張天泰(教育博士、政治工作者)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