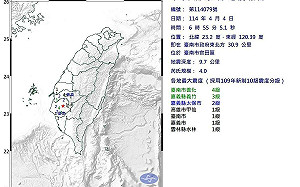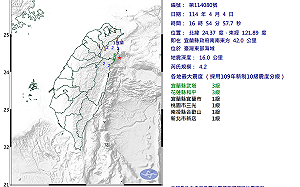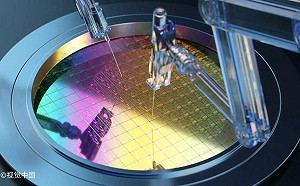台灣大罷免,現正熱映中,大罷免是民主國家公民的權利,也是台灣政治改革領導者出現的時刻。而我認為台灣政治改革領導者應由「博學者」(polymath)擔任,萬事通先生係指通曉各式各樣事物的人,為一般人所討厭,認為其打腫臉充胖子吹牛,特別是烏合之眾會拿此作文章。
事實上,的確無萬事通先生,但有透過不自我設限學習,成就跨領域的「博學者」(polymath)。在這裡所指的博學者或通才,係指「精通多個不同範疇而且表現超群的人」,早在文藝復興時代便有所謂的博學者,當時有另一個別稱「文藝復興人」(英文:Renaissance man,拉丁語:Homo universalis,義大利語:Uomo Universale),特別是在藝術和科學方面的通才。因為在文藝復興時出現了不少這類的博學者,其中Leone Battista Alberti和Leonardo da Vinci就是當中的佼佼者,西方被公認為博學者除上述的兩位,還有Athanasius Kircher、Simon Stevin、Blaise Pascal、Gottfried Leibniz、Mikhail Vasilevich Lomonosov、Immanuel Kant、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Thomas Young、Alexander Porphyrievitch Borodin、John von Neumann,而東方世界也有博學者的出現,例如中國的孔子、鬼谷子、東方朔、諸葛孔明、蘇頌與王國維。
台灣大罷免政治改革領導者應由「博學者」(polymath)擔任。
近代評論者Kumar認為More《烏托邦》中兼具了理性論(rationalism)和實在論(realism)的特色,是一種開啟新視野的作品,是來自於其生命對於政治現實的深刻體驗(profound sense of political realities)。對於教育與政治的關係,More看中的是透過教育能為政治帶來正向的效益, 而More的烏托邦思想具有行動性,他是行動的思考者,除因工作的緣故主動的介入政治、也同時肩負知識份子所應擔負的社會責任,「入世淑世」四字可說是More的一生的速寫,所以有了More《烏托邦》中對政治制度與社會革新的種種理想,這都是值得對台灣教育改革啟示大書特書的地方。例如More主張是希望以適當的教育來培養政治領導人才,由「博學者」來治理城市,因他本身就是具體參與政治事務的公務員,正是如此,More思考的是除了舊有重視「沈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e)的人文主義思想路線,也因More關懷現實的個人特質,以及關心社會的入世問學精神,故特別強化人文主中「入世生活」(vita active)的實踐,將自己繼承的人文主義的傳統理想透過行動,轉化為真實,如何讓理念與對政府的服務行動中取得一致性。
博學者治國的傳統其來有自,在Plato透過與Socrates與別人的對話來提倡一烏托邦式的教育系統《理想國》(Republic)便可看見博學者治國的傳統,Plato已明示哲人王作為一個國家的政策立法者和決策者,所以在理想國中政治權力與哲學須交由同一人的手中,上述的同一人便是哲人王,而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的知識教育與技能訓練,便是博學者(polymatch)的訓練,博學者對於生活中的各項事務,需要有異於常人的好奇心,而這樣的好奇心是可以造就博學者可以精通多個不同領域、不同範疇且表現超群,在Plato《理想國》在其理想的哲人王需具有的六種特性便可看到博學者的特質,Plato認為哲學王需有六項特質能力,一為必須能對目的作抽象的推理、二為能夠知道達到目的的有效手段、三為能夠自制以面對誘惑時堅守理性、四為能夠避免錯誤的推理、五為關愛真理和學習、六為仁慈和真誠的傾向,而在這六種能力特質上仍需要建立在多方涉獵不同樣態的善的知識與善的形式,從Plato強調哲人王在廣博知識、手段與目的、邏輯推理、理性紀律、關愛真理、熱愛學習、仁慈與真誠的能力特質上,其實便是博學者特質的符應與延伸,顯而易見Plato希望具備博學者特質的哲人王,能夠克制非理性與慾望的混亂,對於Plato而言,具備博學者特質的哲人王就是「理性」(Reason)的代言人,理性是哲學人追求的最重要目標之一,我觀察到Plato所提出的培訓具博學者特質的「哲人王」教育,其實是一直想要彰顯「國家理性」與愛國主義的使命感,從其Plato教育系統的設計跟強調鐵血的斯巴達城邦的教育有明顯的雷同之處,斯巴達城邦教育就是「以國家為主體」而設計教育制度,哲人王所受到的愛國訓練,便是要提升「國家理性」,故Plato在《理想國》的基本觀點是,具有博學者特質、愛國主義的使命感的「哲人王」,他有一個很重大的任務去運用所謂的理性來抗制整個社會中的非理性與混亂的個體,而上述的理性很明顯有很大一部分是「國家理性」,而就Plato的思考來說,其所認為真正的哲人王是能理解那些知道柏拉圖式的「形式」(Forms)或「理念」(Ideas)的人們,而Plato的「哲人王」雖然明顯的是菁英主義思想下的產物,但要考量Plato所處的希臘城邦的歷史時空之限制,我認為應該放大Plato強調具有博學者特質的哲人王的領導守則,包括堅持「真理」、守護「正義」、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以及能夠不被貪婪所控制身心與行為的「自我控制」,並將Plato這樣古老的「哲人王」概念進行現代性的應用,但不是重複部分菁英團體在教育上錯用Plato強調把人分金銀銅等階級複製的化約分類 、過度重視菁英主義所造成的困境。
在歷史上,博學者從政成功有其案例,在歷史中博學者從政,帶領政治革新獲得全面的成功例子是有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便是博學者(polymatch)從政,並帶領美國進行政治革新成功的最佳實踐示範,富蘭克林的博學使其能跨領域發明避雷針、雙目眼鏡、富蘭克林壁爐,甚至其電學發現和理論成為美國啟蒙時代和物理學史上重要人物,更重要的是富蘭克林以一個博學者在美國政治革新上的影響力,他曾擔任過賓州州長、駐法國和瑞典大使,第一任美國郵政總長,也是美國政治上堅決反對畜養蓄奴的先鋒者,在政治上的貢獻是為美國簽署三大法案文件《獨立宣言》、《1783年巴黎條約》、1787年《美國憲法》,被後世評論者認為富蘭克林後來未擔任美國總統,不是因為他的能力或聲望不足,而是因當時富蘭克林的年齡太大,年事已高等健康問題,曾有歷史學家認為博學者富蘭克林對帶領美國政治革新的貢獻程度與重要性,只在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之下,而富蘭克林在美國政治革新的行動中,包括出身寒門所以重視勞工、在生活與工作上追求簡樸勤奮的努力、強調民主對於國家的價值,也形塑其代表美國中產階級在美德與價值觀為基礎的國族認同意識,這也是美國愛國主義的來源之一,也是富蘭克林運用「國家理性」的過程,幫美國創造出一個由平民老百姓所組成的中產階級統治階級,博學者富蘭克林經由其從政的過程,展現了美國的政治精神—多元包容、同時重視個人主義與團隊合作、政治外交兼顧理想主義、國家實力至上。
台灣這個國家是有「博學者」(polymath)的,需要用心找出來!
文.張天泰(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