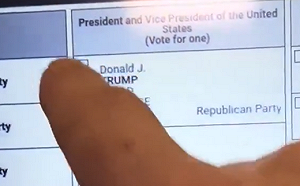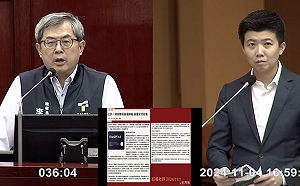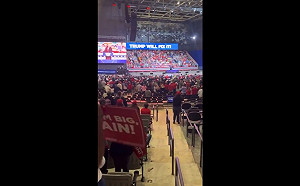當精神鑑定凌駕於司法之上
108年7月間的鐵路殺警案,鄭男因拒絕補票遭列車長要求於嘉義站下車卻於車廂內大聲咆哮,24歲的李承翰員警獲報上車處理,遭鄭男以尖刀刺傷腹部,失血過多不治。一審因台中榮總嘉義分院精神鑑定,認為鄭男殺害行為時處於急性發病狀態而不具行為辨識能力,達刑法第19條第1項因精神障礙而不能辨識行為違法的程度,行為不罰,判決無罪。判決結果一出,引發社會譁然,眾目睽睽之下的殺人,居然獲判無罪!
案經上訴,二審另囑託成大醫院精神鑑定,綜合各項證據資料,參酌榮總嘉義分院、成大醫院報告,認定鄭男行為時,因思覺失調症發作,辨識行為違法的能力與行為控制能力均顯著減低,但未達完成喪失,只能減輕其刑,不能判無罪。二審依殺人罪判處鄭男有期徒刑17年。
此案兩審截然不同的判決結果,凸顯出精神鑑定在審判中的地位,竟凌駕於司法判斷之上!
到底是誰在判決?精神鑑定VS法官
法律講究證據,但「證據」一定客觀公正嗎?
在審理過程中經常會出現各種型態的證據,像是物證、書證、證人證詞、被害人證詞、鑑定意見、數位證據等,究竟哪些可列為本案證據?是否具有證據力?若有,證明力範圍到哪裡?最終判決要不要採用這個證據?這些都取決於法律賦予法官獨特的「心證」裁決權。除非,有目擊者親眼目擊案發經過,監視器錄下關鍵畫面,現場又留有血跡斑斑的兇刀、DNA等鐵一般的事證,但絕大多數的案件都沒有這麼幸運,往往都是事後抽絲剝繭,才能勉強拼湊出一塊拼圖。
因此,在沒有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對犯案人或被害人案發後的精神鑑定,卻成為救贖法官判決的一根稻草,製造出看似公正,卻始終不是科學鑑定的證據,因為精神鑑定的核心,乃是與行為人之對談、聆聽陳述後做出意見,而經聆聽後所作出的鑑定意見是否就因為有專業背書而可以認定罪行有無的唯一證據?
國內就曾發生一起駭人聽聞的醃頭案,差點被殺人犯利用精神鑑定佯裝精神疾病成功脫罪。殺人犯陳佳富為詐領保險金,竟事先於民國100年蓄謀至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向精神科段永章醫師謊稱病情及誇大喝農藥、上吊、自殺等情事,並隱瞞正常職業工作的能力,使其開立精神分裂症之診斷而獲取中度精神障礙之身心障礙手冊,遂後於101年殺害胞妹詐領保險金,並意圖佯裝罹患精神疾病脫罪。然而,法院囑託嘉義長庚周士雍醫師鑑定,該醫師卻讓陳佳富自填量表並透過「直接觀察」之方式推論出「解離多重人格」之鑑定意見,此等草率的鑑定方式險些讓殺人犯免於刑責,若非事後經台大醫院吳建昌醫師重新鑑定,綜觀身體及腦波檢查、心理測驗、精神狀態檢查、長期住院觀察、詐病檢測、解離量表等詳細檢查,差點就讓陳佳富佯裝精神病成功詐騙司法脫罪。
法院將判決寄託於精神科醫師良莠不齊的鑑定品質,不免令人擔憂,畢竟不是每位精神科醫師都像台大吳建昌醫師這般細微謹慎。據了解,醃頭案這位差點成為幫兇的周士雍醫師還曾涉犯詐欺貪污罪一審被判刑,不免令人質疑,像這類素行不良的鑑定醫師是否堪任法院囑託鑑定之責?其所採之鑑定方法如此草率,僅憑直接觀察,在毫無實證基礎下率行而論之假設,竟可直接成為法庭上斷人生死的金口?就連法官歷經多次審理都無法判斷之事,如何能冀望精神科醫師僅憑一面之緣的判斷?
當精神鑑定凌駕於司法判決之上,無疑是助長犯罪風氣。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