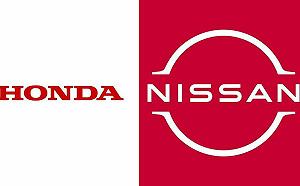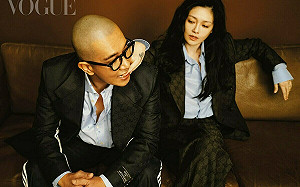文/林瑞霖
外交部北美司在聯合報11月30日”劉姍姍案/認罪協議與豁免主張不衝突” 一文的論點, 從國際法豁免權的規定, 與美國外交部所公布處理豁免權的原則來分析, 對台灣外交部處理劉案的 ”策略運用,” 可以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1. 豁免權的範圍 – 國際法將豁免權分為大使的豁免權 (diplomatic immunity) 與領事的豁免權 (consular immunity)二種, 前者的規定以1964年聯合國通過的 ”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為準則 (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1961) (http://untreaty.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nventions/9_1_1961.pdf), 後者則以1967年聯合國通過的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為準則 (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1963) (http://untreaty.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nventions/9_2_1963.pdf).
基本上說, 大使館官員享有一般所謂的 ”全部/絕對的豁免權” (full/absolute diplomatic immunity); 相對的, 領事館官員僅有所謂的 ”一般/職務操作上的豁免權” (general/functional immunity). 美國政府對外國駐美外交官員豁免權的問題, 原則上接受上述聯合國豁免權的規定(http://www.usdiplomacy.org/diplomacytoday/law/immunity.php).
”全部/絕對的豁免權,”依照 ”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第二條的規定, “外交官員的人身不得侵犯(inviolable), 他不能受任何形式的拘捕或拘留.” 第31條, “外交人員享有駐在國刑事管轄的豁免權.” 相對地, ”一般/職務操作上的豁免權”, 依照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第41條, “領事官員的人身不得侵犯” 第一項的規定, ”領事舘官員不能被拘捕或拘留待審, 除非在一件嚴重的犯罪案件, 同時依據一位能勝任法官的決定.” (Consular officers shall not be liable to arrest or detention pending trial, except in the case of a grave crime and pursuant to a decision by a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y). 也就是說, 依此規定當領事館官員犯重罪時, 經法院確定, 駐在國有權拘捕或拘留待審.
美國外交部發言人答覆中央社記者詢問時表示, 駐美台灣代表享有的豁免權是根據1980年台美簽署的特權免稅暨豁免協定. 在此協定下, 劉姍姍享有與領事官員相同的地位, 她的豁免權僅限於執行許可的職務範圍內.
現在在臺灣與美國對1980年的 ”台美協定” 豁免權有不同解釋的情形下. 國際慣例與國際法規就成為主要的參考資料.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第五條, ”領事官員職務”內容與台灣”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領務服務介紹的網頁 (http://www.roc-taiwan.org/us/ct.asp?xItem=14055&CtNode=3136&mp=11&xp1=), 其服務內容與上述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的領事職務大同小異. 由此看, 外交部堅持對劉姍姍在本案在美該有豁免權的主張, 實有認知上商榷的必要.
2. 針對美國外交部解說劉姍姍在美豁免權局限於 ”職務行為.” 駐美代表袁健生說: ”女傭是政府雇用的,不屬個人問題. ” 外交部次長侯平福認為 ”算不算公務由我方判定.” 北美司11月30日在聯合報解說, ”畢竟如果每項行為屬不屬於豁免範圍, 無論派遣國主張為何, 均可任由駐地國執法機關逕將其派駐人員逮捕後由法院裁判界定, 此種豁免恐已難稱豁免."
決定一個行為是否符合豁免權所允許的 ”職務行為,” 是國際外交上嚴重的難題. 但這也並不能因此就認為 ”職務行為” 的認定是恣意的 (arbitrary), 毫無原則可循. 互惠原則(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是豁免權重要地履行要件,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