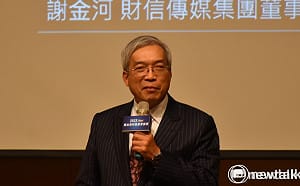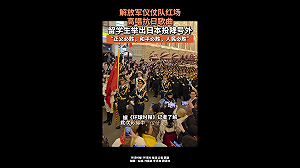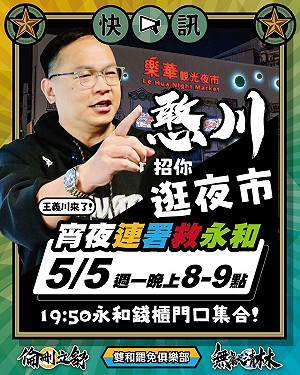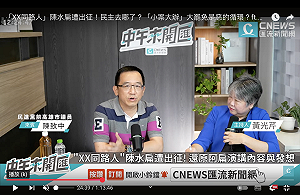剛落幕的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囊獲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等5項大獎的《破.地獄》,不是只有藝術上的突破,從票房數據來看,在香港已創下超過一億六千萬港幣的紀錄,成為目前香港華語電影的票房之最。這是對電影本身的肯定,也代表一種社會現象。它證明港人其實渴望著與死亡對話,渴望與自己過去的情緒和解,只是一直以來都缺少了一面鏡子。而這部電影,恰恰讓他們看見了自己的倒影。
在一個以效率跟現實為信仰的城市裡,「死亡」像個禁忌詞,不宜高聲談論,更別說凝視其真實面貌。《破.地獄》卻選擇在最嘈雜的時代,靜靜地撕開這層沉默的帷幕。它沒有大聲疾呼,卻讓我們重新學會傾聽,聽見死亡的靜默,聽見活著的吶喊。
這部講述殯葬禮儀行業的電影,猶如一道縫隙,讓我們偷窺那原本不敢直視的黑暗,透視逝者未完的愛,生者未說的歉,以及活著卻身陷地獄的我們。
現正最夯:冬奧中國突破零金牌 謝金河批台灣部分人「愛別人國家、阻礙自己」
導演陳茂賢營造的鏡頭冷靜、克制,卻讓人痛得透徹。他不靠催淚配樂與誇張情節,而是用一場場寫實的死亡儀式,掘出人性最深層對於「釋懷」的渴望。每一幕殯儀館的細節,都是對生命尊嚴的最後守護,也是生者心中不願放下的執念。
兩位男主,黃子華與許冠文的轉型,恍如城市記憶的化身。他們不再是笑匠,而是悲劇的容器。黃子華冷靜無語的每一個動作,安撫的不單是亡者的遺容,更是整個城市早已麻木的神經。許冠文飾演的父親,一句「我唔係一個會講『我愛你』嘅老竇,但我從來都冇覺得你丟我架」(我不是一個會把「我愛你」掛在嘴邊的爸爸,但我從來不覺得你讓我丟臉),深信會讓無數觀眾潸然淚下,不是因為感動,而是一種似曾相識的熟悉。
死亡,是生者無法掌控的無常。女主救護員文玥常在搶救病患無效之後,與急診室同袍醫生發生性行為,那一刻的慾望,不是脫序,而是一種求生本能的變形,是向死亡宣戰的軀體反應。性愛與死亡如同硬幣兩面,一體而生,那種頃刻的失控與衰竭,不正喻示了人性在極限之中仍然渴望的一絲連結。
全站首選:川普權衡對伊朗軍事行動 白宮稱達成協議「非常明智」
影片深度觸碰的議題,便由這裡慢慢浮現,死亡不是單一終點,而是生與社會、性別、身分、宗教、制度交錯的節點。片中無數對傳統儀式的挑戰,都是對整體社會結構的質疑,為何只許男性執香?為何同性伴侶只能在法外談情?為何說出「我愛你」要費盡一生?
片名「破」字,不只是破地獄,更在破那些無形的枷鎖。這點完全呼應了沙特「他人就是地獄」的哲理名言,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活在由他人眼光構成的地獄裡。「破」字的真正意義,就該從這層涵義作解脫,絕不是躍過火陣的儀式,而是一次與靈魂的自我對話。
喃嘸師傅嗨佬文中風後寫給子女的信,不僅是告別,也是悔悟。他明白自己被傳統吞噬了一生,更希望下一代不要再被延續。這種形式的和解,不是甜美的團圓,而是一種破鏡後的重生。正如禮儀師道生,替他宣布「兄妹共同主理喪禮」的當下,那個瞬間,是顛覆,是掙扎,也是跨出未來的門檻。
結局鏡頭拉遠,俯瞰香港維多利亞港的兩岸,像極了生死的兩端,我們無法閃躲,必須跟著居中審視,我們究竟要如何走過這一生?又是否準備好,迎接那場終將到來的離別?末了,畫面映出白居易〈自覺二首〉詩作,節錄詩中「幾許平生歡,無限骨肉恩。抖擻垢穢衣,度脫生死輪」四句,詩句很貼切地為電影做了總結。死亡終究不會等人,但我們可以在尚存之時,學會放下。不是放下逝者,而是放下那些不敢愛、不敢說的自我。
在甫落幕的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這部囊獲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等5項大獎的《破.地獄》,不光只有藝術上的突破,從票房數據來看,在香港已創下超過一億六千萬港幣的紀錄,成為目前香港華語影片的票房之最。這是對電影本身的肯定,也代表一種社會現象。它證明港人其實渴望與死亡對話,渴望與自己過往的情緒和解,只是過去缺少了一面鏡子。這部電影,讓他們看見了自己的倒影。
也許,讓看過電影的觀眾真正有所啟發的,不是它拍了死亡,而是它透過死亡,讓人們重新思索如何活著。願我們都能有勇氣打那通該打的電話、說那句「我愛你」、做一次不為傳統而活的自己,並超脫我們身處這個名為「人生」的地獄。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