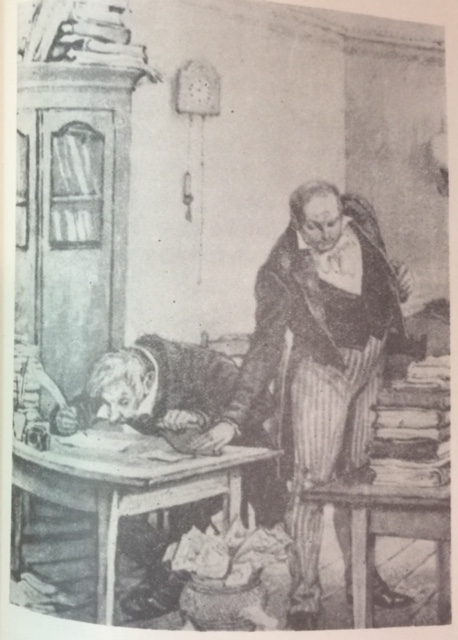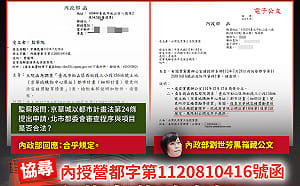對聰明睿智的人,也不知其深度,對勤奮用功的人,也不知其真諦,我的思想在世上找不到接受者,如同海水只能在自己體內老去。----法稱(古印度詩人)
6.
一走進書房,我立刻被滿牆的書籍給吸引住了,更具體地說,我被一種龐大的書卷氣息壓倒了。這簡直是一座小型圖書館。剛才,他提到捐書一萬五千冊,我還停留在抽象的數字概念。不過,現在,我對它的看法整個更新了,因為這麼多實體的書籍,堂堂正正地出現在我面前,我就能比非親歷者更能夠體會到數量的實相。這個巨大的感觸,使我忽然想起了印度的耆那教的哲學思惟來。耆那教認為,空間是一切存在和運動的場所,靈魂、物質、靜止的條件和運動的條件都是存在於空間裡。空間雖然不能被人們直接所感覺,但它的存在確是可以透過邏輯的推理而得知。耆那教將空間劃分為有人、靈魂和占有的「充實的空間」,以及靈魂擺脫肉體以後定居的「虛空的空間」,前者是有限的、相對的,後者則是無限的、絕對的。時間為「一切存在的連續性、變化、運動、更新提供了可能性。由此看來,我現在立在捐書者的書房、他日以繼夜寫稿的工作室,我真的切身感受到「充實的空間」與「虛空的空間」充滿熱情地向我走來了。
現正最夯:荷姆茲海峽GPS/AIS遭大規模干擾 船舶「登陸」、油輪飆時速190公里、異常軌跡
「嚴先生,就是坐在那張桌子寫稿的?」我指著臨窗的桌子,很有自信地對他說道。
那時候,窗外的陽光灑了進來,照得整個房間甚為明亮;與此同時,它彷彿也在呼籲藏於角落的陰影暫時撤退,因為今天的日子有點特別,來了一位出版商,他正以虔誠的心情參觀它們主人的神聖之所。
「嗯,不去做義工的時候,我就來這房間裡工作。如果寫得不順利,我就東摸西找的,好比,抽出鐵書架裡的舊書,把它翻動一下,或者抽出來,讀個片刻都好。總而言之,心情就會變得快活起來。」他的語氣有著某種自豪的回響。
全站首選:美對伊戰爭耗損嚴重! 8百愛國者導彈、11架MQ-9、3架F-15戰機損失
「不過,上午的陽光那麼熾烈,哪怕經過玻璃窗的阻擋,那還是很熱的吧。」我最怕燠熱的煎熬了,自然以自己的感受為先,「而且,房間裡沒裝冷氣,只開著電風扇旋轉,您受得住啊?」
「嗯,」他微微一笑,「不過,與其說我不怕炎熱,不如說我已經習慣了,日子一久,就順其自然地接受它了,不然又能怎樣呢?」
這句話說的真好!順其自然地接受事實,看似悲觀色彩的宿命論,仔細想來,並沒那麼糟糕,沒那麼孤立無援,否則在冷氣機尚未大量生產,尚未走進家庭之前,人們又是怎麼度過日日夜夜的?
「對了,熟門熟路的歐凱里飛進來,有特別喜愛的位置嗎?」我重啟了話題,「例如,書桌旁的鐵製書架上,或者其他的位置?」
「社長,不愧是養鴿的過來人。」他很滿意我的提問,轉過身來,指著書桌右後方的書架說,「您看,鐵製的書架自下而上都塞滿了書籍,我在最上層特別留出了空位,作為歐凱里的棲息處。那裡也是牠的家,牠隨時都能自由進出的。而且,我認為,那個位置極好,可以看著我埋頭寫稿,又不會讓我分心。因為牠知道,如果飛到我的身旁,我就會停筆下來,與牠一起逗樂,無止盡地說話……」
「如您所說,歐凱里真是個懂事的孩子。」
我由衷地稱許他,人與鳥類之間,能夠建立起這般深刻的情感交流,實在很不容易。進一步地說,這之間發生的故事,絕不是嫉妒者所說的妄想和幻影,而是根植於親情與愛情的土壤,否則不可能有如此雋永如新的萌發。對嚴向冬而言,其實,他的後背也藏著一對眼睛。雖然他背對著歐凱里的位置,卻能感知到歐凱里的神態,在最幽微的時刻,彼此進行沉默的關懷。
「哎呀,聽您這麼一說,我真羨慕那些傑出的小說家……」我加強語氣地說,「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一進入他們的筆下,立刻變成煥然一新的生命圖景。」
「小說家比得上歷史學家嗎?」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啦。或許,可以這麼說,一個卓越的小說家,其作品的影響力,絕不輸給平庸的歷史研究者。您看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他們為什麼推崇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小說就知道了。」
「社長想當小說家嗎?」他直白地問道。
「哈,坦白說,我有過這個夢想,」我坦白從寬地說,「不過,我知道自己的毛病,耐不住寂寞和誘惑,更慘的是,缺乏滴水穿石的毅力……。如果我有嚴先生一半的耐性,也許,我還能當個半吊子的小說家呢。」
「哎呀,不要這麼說,我都覺得難為情了。」說到這裡,他喜憂參半似地說,「這次,我的書稿多虧社長的幫忙啊……」
「您客氣了。我說過,您是自費出版,所有的費用已包括打字、編輯、校對、排版、印製和裝訂費。一千本印製出來之後,我幫您代銷三百本,其餘七百本由您處理,可以自行售販,盡快掙回付出的費用……。」
「謝謝您!」
「不客氣。……話說回來,我倒比較擔心歷史學界對這部書稿的反應。」
「咦?」他沉吟了一下,略顯不安似地說,「……因為我不是大學裡的歷史系教授,不是正統權威的歷史研究者嗎?」
「在我看來,這不成問題的。專業的歷史學家出版著作,在史料考證以及寫作技藝上,一定是毫無破綻可言,否則就與歷史學家的名銜不相符合了。我較為擔心的是,您對於日本戰敗以後是否向蔣介石政府交出『受降書』提出了質疑,這個引證是否站得住腳?」
「社長,我鄭重地向您說明,經過我多方的查證,『受降書』的說法,似乎並不可靠。持肯定論的學者和作家,最終依然沒提出『受降書』的原本,多半為引述前行者的說法。」
「我願意相信您,嚴先生。不過,在此,容我開個玩笑。您主張沒有『受降書』的存在,等於向那些肯定論者開砲和挑戰啊,直白地說,其中就有我認識的作家朋友呢,儘管你的參考書目多達五百本之多……」
「我沒考慮到這些,」他露出尷尬的笑容,但最後仍然直陳自己的想法,「也不是刻意要挑戰他們,我只在乎歷史的真相,更多人知道歷史的真相,不是很好的事情嗎?」
「這麼說,您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我追問道。
「……社長的意思是,專家和歷史學者對我提出嚴厲的批評嗎?」
「嗯。」
「我只是個平凡的作者,如果能得到他們的批評,也是一種無上的光榮。」
「是啊,嚴先生,一本新書出版了,如果沒能得到某種程度的關注,等於被打入了冷宮,除非出現什麼奇蹟,否則就很難翻身了。稍為誇張地說,到時候,有學者對它提出尖銳的批評,作者和出版商都應樂觀看待這個危機的,因為許多事例表明,危機逼降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轉機。」
話畢,我向他補充,該書出版以後,我將為他辦個新書發表會,吸引更多人關注,雖然書市向來冷清,但是該做的宣傳就要徹底執行。這與出版商的規模大小無關。一部書的誕生,如同一個生命體來到世間,無論它來自闊氣的豪門或者簡樸的小木屋,任何人都沒有資格限制它。
「感恩,譚社長!一切就拜託您了。」
「別客氣,這是我應盡的責任。無論如何,我不能收錢不辦事啊。」我如耿直的他一樣,也坦誠說出自己的感受。「嚴先生,我認為,您採取自費出版的方式,不失為一個明智之舉。事實上,出版有時候蠻複雜的。」
「咦?」他似乎沒聽懂我的弦外之音,只能等待我進一步的說明。
「一般來說,作者有這樣的心理:出版社為作者出版新書,作者有版稅收入,又能享受作者的頭銜,強化自己的社會地位,自然是高興無比的。不過,這種美事只發生在大作家的身上,不會降落在平凡的作家的餐桌上。」
「真是這樣嗎?」顯然的,他被我的說法所吸引了。
「如果,那個作者剛好流年不順,遇上了居心不良的出版商,那麼後續的情況就很慘了。他們抓住作者極欲出書、渴望受到社會肯定的心理弱點,就在文字合約裡做陷阱。例如,一般的版權年限為五年,他們把它調高到十年,這時經驗尚淺的、或者不諳出版管道的作者,就會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做出妥協。再則就是版稅的支付了,對出版商而言,這可是一門絕妙的經營學。」
「……可是,合約上明白寫著,他們不支付版稅嗎?」
「這個倒不會,不過,他們依然有辦法對付你。譬如,他們先支付一半的版稅,在那之後,就沒有下文了,你們變成了陌生人。」
「為什麼?」
「按照行規,出版商每半年必須向作者寄發版稅結算書,裡面寫得非常清楚,銷售冊數、破損、退書、庫存等等。作者確認無誤後,簽字寄回就可,這是正派出版的做法。相反的,居心不良的出版商,偏偏就不給作者年度版稅結算書,讓作者處於黑暗不明的狀態中。」(待續)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文化隨筆三部曲《日輪帶我去旅行》、《我的枯山水》、《燃燒的愛情樹》(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