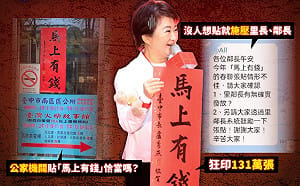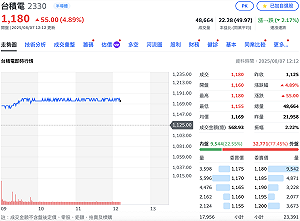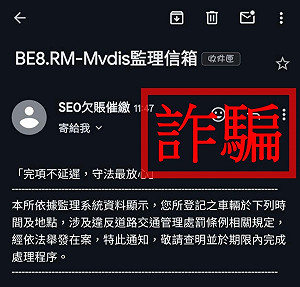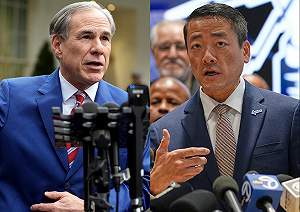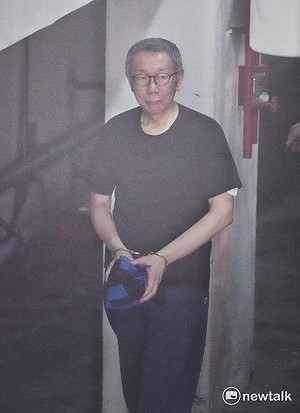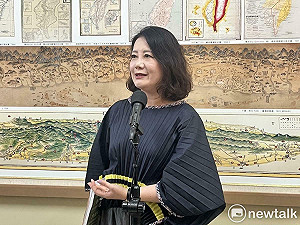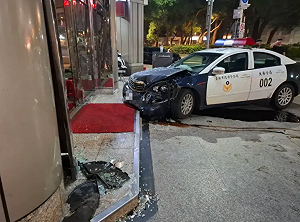我國憲法第78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按此規定,解釋憲法與統一解釋法律命令,均屬司法院,更精確地說,憲法法庭之權限。惟在近來憲政實務與學界討論中,因「國會擴權修法」所引發的憲法法庭與立法權權限關係,與司法院釋憲裁判的拘束範圍,再次變得高度受矚。
釋憲是否拘束立法權?
現正最夯:曾霸氣護女!前主播吳中純淋巴癌逝享年56歲 老公悲痛發文:淚乾心碎
現行法制下,憲法法庭或過去大法官解釋,究竟在多大範圍內對於立法院具有「規範重複禁止(Das Normwiederholungsverbot)」原則」的效力,素屬憲法學理與實務裡的爭議焦點。肯定說主張,在憲法為最高法規之地位下,國會應受憲法法庭判決拘束,不得以立法「繞道」繼續做出違憲行為,否則形同否定憲法審查之意義與護憲功能。否定說則認為,基於權力分立的動態平衡,立法院作為民意代表機關,其立法權僅受憲法明文拘束;至於憲法法庭判決,雖有指導意義,但未必能直接限制未來的立法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否定說近年來因動態權力分立理論而受到一定程度重視,主張法院須尊重多數立法決定,勿妨礙政治過程運作。惟立法院官方報告(如本次的立法院法制局報告)直接採否定說,仍相當罕見,顯示憲政結構的不穩與立法、司法兩權的潛在緊張。
立法院法制局報告之政治企圖心
2024年立法院法制局發布以局長郭明政為首的報告〈重複立法作為憲政對話──論國會立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的界限〉,主張憲法法庭判決僅屬「非憲法位階」,立法機關僅「需尊重」而無須絕對遵從,即便大法官宣告法律違憲,國會仍可再行立法,甚至再次通過內容幾近相同的法律。報告明確界定司法權不得干涉立法權,主張立法院通過的法案僅能接受最低密度的審查,不得進一步介入「政治問題」。
此種觀點,無疑對長期認為釋憲有「規範重複禁止」拘束力的多數學說構成挑戰。特別是在憲法法庭2024年(113憲判9號)就「國會擴權法案」部分違憲之後,法制局報告的核心命題,等於為藍白陣營的「國會擴權2.0」預作理論鋪墊,試圖讓立法院可再度推動類似法案,迴避司法審查之「拘束」。
「國會擴權2.0」與三權失衡
立法院法制局如此論述,不僅具高度政治意圖,更伴隨嚴重的憲政風險。近年我國三權制衡的實質機制已遭多重挑戰:大法官憲法法庭自113年初即因人事與政治拖延近七個月無法正常運作,實質癱瘓。面對違憲法案在國會反復表決,憲法法庭不僅未及時裁判,更淪為「似有若無」的護憲制度。
另一方面,社會自2023年以降對國會擴權修法的激烈抗議,並沒有因公投及罷免潮而消耗殆盡,民間聲音持續不滿。現有8位大法官多數選擇不積極作為,坐視憲法法庭長期停擺,分權制衡機能近乎喪失。在這個節骨眼,法制局報告反而進一步「學理化」立法權不受司法審查拘束,等於為未來國會多數連續推動舊案開綠燈,形成持續違憲、憲政倒退的惡性循環。
比較法與護憲機制的重建
值得追問的是,法制局報告所舉「立法權不受釋憲拘束」之法律系統根據,究竟來自何處?若以德國、美國等成熟法治國家的憲法實務觀之,雖承認立法者基於民意代表性有一定裁量空間,惟釋憲機關一經確認立法違憲,即具裁判拘束力,立法者不得以繞道手法持續違憲。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即具有法律拘束力,美國最高法院對違憲法律之宣告雖不直接修改條文,然政府部門實際上均會執行判決。是故,立法院法制局主張台灣「釋憲不拘束國會」乃為藍白狡辯之特色,既無比較法基礎,更與我國憲法明文立法精神背道而馳。
當前憲政危機的癥結,在於三權分立原則失靈及憲法審查制度的空洞化。本文認為恢復正常運作的憲法法庭,端正對國會立法權濫用的即時糾正,是解決憲政危機的唯一正道。大法官應發揮其定紛止爭、維護憲法最高性的使命,對於明顯違憲的國會法案主動審查、明確禁止重複立法,並做出具實效的違憲宣告。行政部門與立法機關亦應尊重釋憲決定,共同維護法治國基礎。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民意遭政黨鬥爭綁架,確保人民基本權利與憲法秩序。
然而,國會擴權2.0法案的可能推動,讓不少支持分權、護憲的民意紛紛呼籲執政黨必須強力阻擋。然而,大規模罷免運動失利後,社會反對力量明顯消耗殆盡,不少人感受到藍白無敵星星的威力,深刻的無力與挫敗。
眾所周知,「釋憲不拘束立法權」之說,若為立法院之多數立場,實質上等於廢止釋憲制度、削弱護憲機制,使三權分立流於形式,並為政黨專斷留下漏洞。當公民正義、憲法守護機制不再有效時,不只是民主品質的破壞,實為民主倒退的前兆。台灣今日的憲政危機,正是警覺此一趨勢的最佳證明。護憲之路不能退縮,仍須重拾憲法第78條原意,確立憲法法庭判決的效力,方能使共和基礎穩固不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