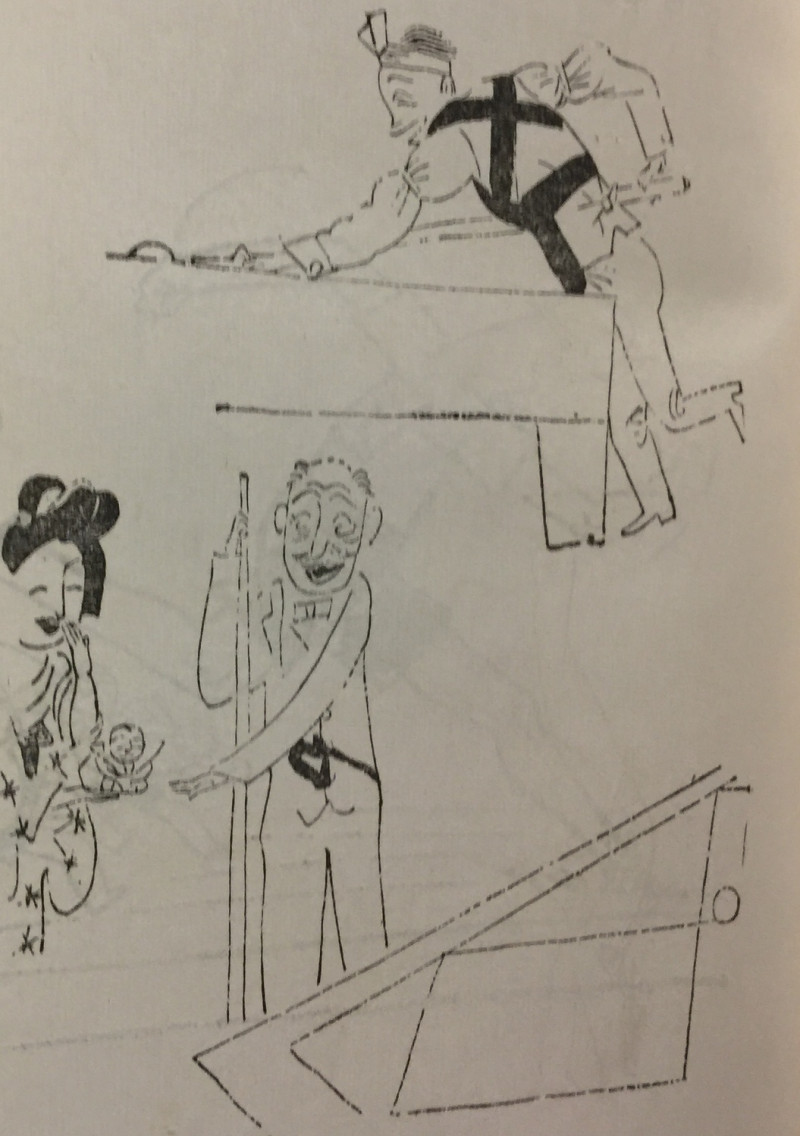引言:在這個價值錯亂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講述自己的故事,以獲得嶄新的身份,找回有意義與價值的位置。這部小說藉由一個徬徨的青年作家,為了解封性愛的苦悶和對生命的探求,得到一個老政治犯的思想啟迪,從此走出思想的困境,進而了解底層人物的心聲,揭示存在於臺灣社會內部的禁忌和荒誕面相。同時,這也是由壓抑的性愛通往政治思想解放的現代喜劇。
第三章 無神論者的視界
一個陌生女子的親吻
現正最夯:張又俠落馬「剩下習近平撐場」胡采蘋:相當於解放軍將領全軍覆沒
一個陌生女子的親吻那日午後,突然下起了大雨,把「新樂園世界旅館」頂樓加蓋的鐵皮屋頂,像打鼓似的擊得咚咚作響。在注重四季變化的日本人看來,這就是季節的風景詩。不過,也因為這場感性的驟雨,將連日來燠熱纏綿的暑氣驅散不少,增添了些許涼意。那些苦悶壓抑的人群,一看見這種及時雨,自然是高興不已。
賀蒙特依照塞林傑的說明,沿著旅館內暗淡的階梯,一步一步地拾階而上,朝著佩琪所在的房間走去。這時候,賀蒙特突然覺得有點格格不入,因為「新樂園世界旅館」是他常來的地方,與老闆塞林傑聊天的場所,並非初來乍到的陌生處所,邁出的腳步不應該這樣遲疑的。
賀蒙特來到房門前,深深地吸了口氣,輕輕往門板敲了兩下,貼著木質紋路的門敞開了。他心想,可能是她早已做好準備,也可能是這間套房原本不大,與走道的距離很近,所以幾乎不到三秒鐘的時間,那扇門就輕盈地拉開了。他終於走進甜蜜的房間了。
「賀先生,您好!」女人招呼道。
「你好!塞林傑說,你遇到困難的事情,叫我來這裡看看。」賀蒙特確認地問道,「你是佩琪嗎?」
話音剛落,女人噗哧地笑了出來。她解釋道,塞林傑的聽力有誤,她已經訂正過好多次了,她的名字叫做貝綺娜,而不是女性常用名字佩琪,雖然這兩個發音很相似,比較容易記住,但是她很在乎發音的準確性,因為名字代表那個人的內在特質,承載著父母親的期盼,所以由不得有一絲絲的馬虎。好比,取名為聰明的男孩子,父母在取名的時候,必定希望這孩子將來聰明過人,在險惡的人生中躲過各種無情的暗算;相反的,如果取名為美麗的女孩子,當然希冀這女孩子長得漂亮,用良善的美貌為自己帶來好運。
「來,您這邊坐。」貝綺娜拉著賀蒙特的手,來到床舖旁坐下來,隨手把檯燈的光線調得更暗淡了。賀蒙特原本想看清楚些房間內的格局和擺設,燈光卻陡然變弱了,暗淡的漸層加深了。他眼前的視界因此變得模糊了起來。如果說,在這時候,他看得什麼具體的東西,那就是檯燈的餘光托映出床舖前那台電視機了。於是,他不由得浪漫想像著,他們同在暗淡的房間裡,正要進行奇妙而冒險的情事,儘管那台舊式的電視機沒有被啟動,它都要抓緊住什麼的,吸取最大的光線來證明自身的存在,哪怕在別人看來,它只是微不足道的物體,一個用來消磨時間的裝置而已。
外面的雨聲很大。他們倆坐在床邊上,以這種形式開對話的序幕。賀蒙特旋即發現,這房間的濕氣很重,從浴室裡傳來的、由各種雜物散發出來的,包括像是衣櫥裡彌漫著的霉味。而長期租這裡的貝綺娜,必然比任何人都更早察覺到,所以在賀蒙特來此之前,她已經把冷氣調到最冷,用最強的冷氣把這些惱人的雜味,一寸不留似地全部驅趕出去。不過,牆上那台半舊的窗型冷氣機,似乎不怎麼爭氣,馬達聲隆隆震響著,送出的冷氣一下子強勁,一下子冷弱,使得這精心設計的情愛空間扣了分數。
在那以後,貝綺娜自己先脫了衣服,僅剩一件胸罩和內褲。接著,她脫掉賀蒙特的衣服和褲子,動作輕柔絲毫不做作,宛如正為鍾情的男友獻身一樣。從男人的視點來,這種風情萬種挑逗的動作,輕而易舉就能擊潰男人的戰壕防線。剛開始,賀蒙特仍然帶有謹慎的防衛性,還沒摸清楚對方的來歷,貿然接受無償性愛的輸送,終究充滿不確定的危險。問題是,經由她慢條斯理為其解除武裝,他似乎慢慢地接受她手指所傳達的愛撫的召喚。
貝綺娜主動送上了一個親吻,然後移動膝蓋繞到賀蒙特的背後,伸出柔情的雙手環抱住詩人,用自己的臉頰貼在詩人的耳邊,輕聲說道:
「說來您可能不相信,我是一個不幸的女人。」
賀蒙特只「噢」了一聲,沒有正式應答,因為他若口頭上回答相信,顯然是言不由衷,等同於自己在說謊話,可是他又不能說不相信,這樣未免會傷及對方的感受。
「我丈夫是個台商,他在開放兩岸探親的時期,變賣台灣所有的財產,到大陸做生意了。原本我也跟著過去協助,待了好多年,後來我娘家出了點問題,需要我回來處理。情非得已之下,我只好先回來暫住……」
「你丈夫的生意做得如何?」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他經常來電話,說他的生意做得很好,以後有機會的話,要我多拉幾個股東入伙。」
「不好意思,我不懂生意經,單純憑普通的常識來說,既然生意做得好,就不需金主加入,這樣獲利分紅豈不是變少了?」賀蒙特問道。
貝綺娜苦笑了一下,似乎欲言又止。她呼出輕盈的鼻息觸動著賀蒙特的耳毛,有兩三秒的時間,使得賀蒙特差點發痒起來,但為了他們對話的順利,他極力壓抑著這個黑色喜劇般的意外。
「是呀,按照常識來說,做生意賺了大錢,自己數鈔票都來不及了,哪會容許別人來分好處呢?不過,這個道理不適用在我的丈夫身上。」貝綺娜揭開誠懇的面紗說。
「怎麼說?」
「我說不上來。他們那些自視左派的菁英,能言善辯很會講話,反正最後說不過他們。」
賀蒙特聽到「左派」二字極為敏感,有段期間他非常著迷左派的理論思想,不管是否讀懂它們,有借書機會的話,他就全部借來複印,作為思想讀物資料庫。所以,就這層關係來說,他認識些臺灣的左派人士,即使彼此沒見過面,也聽過他們的名字。在這瞬間,他突然很想知道貝綺娜的丈夫是誰?
忠誠報效祖國的途徑
「你剛才提到左派菁英,我心裡有點好奇。其實,我認識過幾個左派的朋友,聽說他們也到大陸做生意,可是後來失去了聯絡,僅能從共同的朋友那裡,知道他們的近況。實際的情形怎樣,我並不清楚。」賀蒙特停頓了一下,說道,「不好意思,方便告知你先生的大名嗎?」
貝綺娜沒有迴避這個提問,反而超出賀蒙特的預想那樣,把他摟得更緊密了,豐滿的乳房像柔情的肉彈,甜蜜地伏貼在他的後背,這個挑逗的動作,立刻引起了賀蒙特強烈的生理反應,進而往他厚實的胸膛撫摸著,「我的丈夫叫做向欣榮。您認識他嗎?」
「向欣榮?噢,我不認識,」賀蒙特說道,「我那個左派朋友是個詩人,叫做徐紅行,原本開了一家小出版社,專門出版批評日本帝國主義的書籍,但更多的是,批判車輪黨的反共政策的出版品。不過,你大概不知道,車輪黨並不是省油的燈,他們掌握住龐大的國家機器,隨時都能把反對者的聲音給壓下去。結果,聽說車輪黨還沒正式發動查禁的攻擊,他的出版社就倒閉了,讓警備總部和調查局的人員,失去展現鐵腕精神的機會。」
「後來,你這位朋友就這樣消失了嗎?」貝綺娜好奇地問,「他該不會也去大陸吧?」
「對,你猜的沒錯。臨去之前,徐紅行還向前輩詩人哥達拉斯辭行,說他一直待在臺灣沒有出路,甚至惹來不必要的麻煩,不如到偉大的祖國闖蕩一下。」
「他是做出版的人,沒有從商貿易的經驗,能做什麼生意嗎?除非他身上有大筆的資金。可是,你說他的出版社倒閉了,經濟狀況應該不好吧?」
「徐紅行到大陸打天下,詳細情形我並不清楚,只是從哥達拉斯那裡轉述來的。哥達拉斯說,他向幾個左派朋友借錢,說打算在廣州開餐廳,再造人生的高峰。」
貝綺娜輕聲地哈了一聲,吹向了賀蒙特的耳裡,又把他搔得酥癢了起來。「開一家小餐館,就能夠再造人生的高峰嗎?」
「說得也是。不過,這畢竟是他的自我期許。對一個失敗的人來說,要把自己從沮喪的泥淖中拯救出來,首先就必須給自己建造一個神話。就像我的朋友童衛國一樣,他把自己在臺灣的所有生活,視為一種真空狀態,將來時機成成熟的話,他就要回到祖國的懷抱。」
「您跟童衛國很有交情嗎?」貝綺娜問道。
「不好意思,是我岔題了,不應該提到不相干的人。」賀蒙特歉然說道,「哥達拉斯說,徐紅行帶著一個草綠色的大軍用袋,裡面裝著數十個鐵板,以及二十萬元人民幣,隻身就前往廣州了。」
貝綺娜似乎越聽越感到興味盎然,很想知道徐紅行的下文,與此同時,她深切感受到,現在與賀蒙特的肌膚之親應該是穩定狀態,接下來雨雲交融更會邁向新的境地。想到這裡,她輕柔地把賀蒙特按倒下來,轉而把整個臉頰貼伏在他健壯的胸膛,然後用大拇指和食指淘氣般搓弄著他的乳頭,催促著他繼續把徐紅行的故事說完。(未完待續)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我的書鄉神保町》1-10卷(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