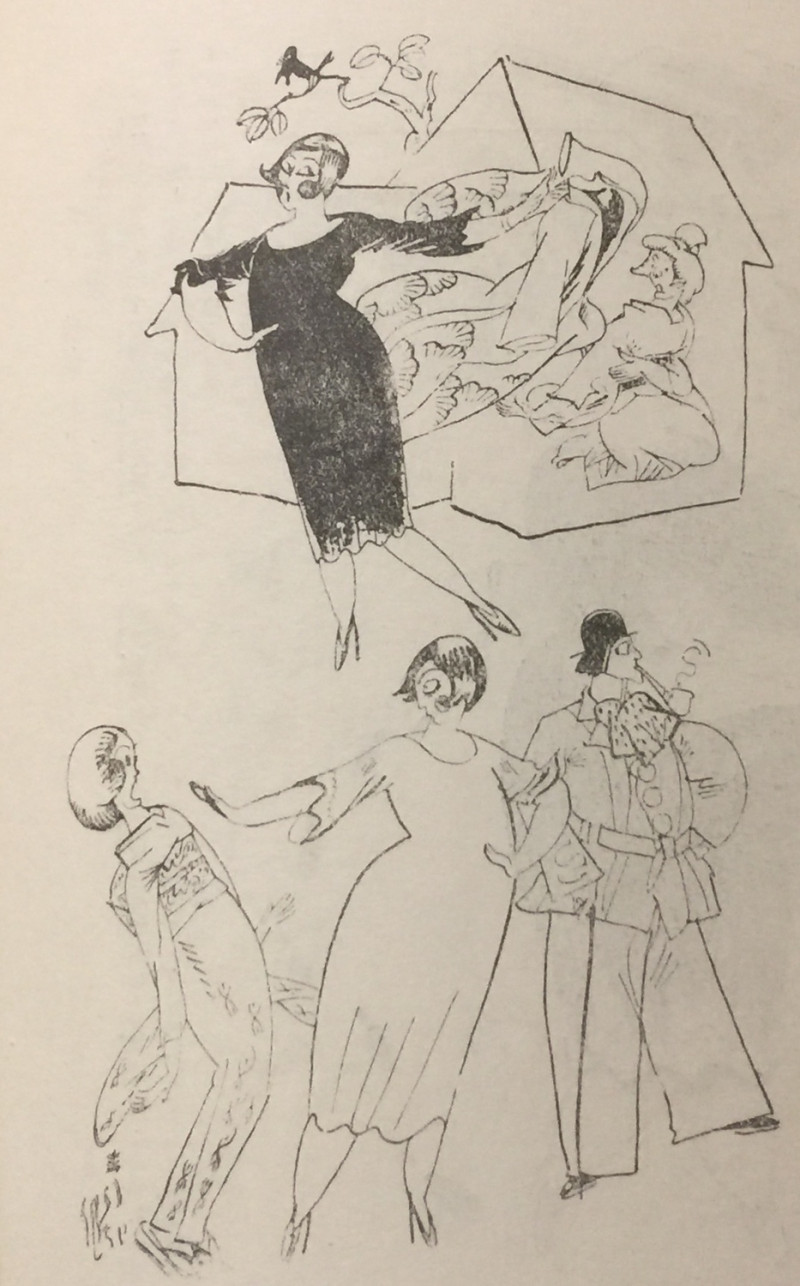在這個價值錯亂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講述自己的故事,以獲得嶄新的身份,找回有意義與價值的位置。這部小說藉由一個徬徨的青年作家,為了解封性愛的苦悶和對生命的探求,得到一個老政治犯的思想啟迪,從此走出思想的困境,進而了解底層人物的心聲,揭示存在於臺灣社會內部的禁忌和荒誕面相。同時,這也是由壓抑的性愛通往政治思想解放的現代喜劇。
第三章 無神論者的視界
戴上一頂惡之花的花冠
全站首選:張又俠落馬「剩下習近平撐場」胡采蘋:相當於解放軍將領全軍覆沒
在塞林傑再三的催促之下,賀蒙特很快就抵達「新樂園世界旅館」了。老闆看到詩人朋友來了,立刻站了起來,微微一笑朝他揮了揮手,表示他等了好久,屁股快要燃燒起來似的。不過,他仍然沒有忘記待客的禮數,看見賀蒙特走來,遞上一小杯淡褐色的茶水。賀蒙特接過小茶杯,一口氣飲下了,旋即說道,「塞林傑,我看你大概不專心沏茶,這隻烏龍茶浸泡太久了,茶湯的顏色不對,茶湯都變得苦澀了。」
「哇,賀哥,真是厲害,喝下一小口,就知道這茶湯走味了,難怪上次韓德爾光臨本店的時候,只喝了一口茶,就挖苦地說:老弟啊,你是在搞謀殺嗎?這種釅口的天公茶,我嬌貴的胃腸哪招架得住,再說,請人喝茶要有誠意,至少泡點福壽山農場的高山茶嘛。」
「慢著,我打個岔,韓德爾是誰?」
「他是……」說著,塞林傑打量了周遭,看見沒有可疑人士的目光,壓低聲音說道,「我們這選區的議員,他的酒量極好,所謂千杯不醉的能人。通常,樂於杯中物的人,不大喜歡品茗,或者根本與品茗絕緣,因為這兩種味道相差太懸殊了。不過,他畢竟是勢力堅強的地方議員,三教九流都有來往,有人贈予頂級的高山茶,自是理所當然的事。我想,他是個例外,既是酒國的英雄,也是品茗的高手,否則不可能只喝一小杯,就知道這是廉價的烏龍茶。撇開這個不說,他可是我們的功德主之一。」
「怎麼說?」
「因為他三不五時就帶小姐來這裡鍛煉身體。就此來說,他為我們的營收貢獻不少。」
「好吧,我知道了。韓德爾的事情,我們以後再聊。」說著,賀蒙特也跟塞林傑剛才的動作一樣,環視周遭有無可疑人士,確定排除潛在的危險以後,他才探問道,「那個女人在嗎?」
「噢,佩琪嗎?二十分鐘前,她剛剛外出買東西了,說晚點才會回來。」
「塞林傑,這事情太唐突離奇了。我覺得,其中好像藏著什麼陰謀……」
「不會吧。」
「……也許,你被蒙在鼓裡而不知。有人說,施展陰謀就是在證明其害人的智能和高度。」
「我聽不懂,你說的太高深了。」說著,塞林傑湊近賀蒙特的耳邊說,「你試試再說嘛,先不急著推辭。我因為是條件不符,不是佩琪要的人,否則我早就撲上去了。」
「虧你說得眉飛色舞的,看來你拿了不少好處?」
「別疑神疑鬼,有好事上門,就痛快地接受它吧。」
「你剛才說,韓德爾那麼熱衷於帶女人開房間,他不就是最佳人選嗎?可以把他介紹給那個叫佩琪的女人,這樣豈不是兩全其美嗎?」
「哈,賀哥想到的,小弟我也想過。」旅館老闆說,「可是,這有兩個難題。首先,韓德爾雖然性好漁色,不過他終究是地方議員,他會顧忌來路不明的佩琪免費找他上床,是不是搞仙人跳,趁此機會狠狠地敲他一筆?而且,政治人物最怕惹上桃色糾紛了,一旦自掘這個窟窿,等於給他的政敵製造倒土的機會。所以,我想就算他發了酒瘋,大概不會這麼做。」
「韓德爾的勢力龐大,還害怕這個嗎?」
「我想,不止韓德爾有這種顧忌,每個在政壇上走跳的人,總比一般的炮客考慮得多吧。說的也是,一個政治人物向某金主借來大筆的資金,撒上大把鈔票,用它來綁樁腳搞選舉,如果能選上當然最好,因為確定當選才有還債的基礎。相反的,萬一落敗的話,債權人和仇家們立刻就會找上門來。哎呀,這是多麼慘烈的場面,簡直使人不敢想像。可想而知,最後他必定落得走投無路,只好像熱氣似地從人間自行蒸發了。幸好,韓德爾還是挺住了。有段期間,我去附近小學的運動場跑步,還看過韓德爾卑躬哈腰地站在那裡,對著每個來運動的學生家長握手呢。試想,所有與他親近握過手的學生家長,進入選舉熱季的時候,能不投他一票嗎?」
「嗯,的確不簡單!從常人的角度來看,他能做到酒醉而心不醉,不愧是百年來臺灣政壇的奇葩。」
塞林傑說到這裡,冷不妨笑了一聲,並露出詭異的神色,賀蒙特好奇地問道,「你在笑什麼?」
「剛才,我是從政治人物的角度來考量,為什麼他不接受美女奉獻肉體的邀請。嚴格講,這是一廂情願的說法。實際上,事情恰巧相反。」
「咦?」
「上次,韓德爾帶著小姐開房間,剛好毗鄰著佩琪的房間,那時候她待在房間裡,全程聽著他們打炮時發出的聲音。佩琪說,他們辦完事情以後,那女人先走了,隨後十分鐘左右,韓德爾才推門走出去。佩琪出於好奇算好時間,推開門縫偷看那個男客,結果,那個情景卻讓她感到吃驚……」塞林傑似乎說得越發興奮了,連續吞了兩次口水,彷彿這是他親臨現場的採訪報導。「她說,在暗淡的通道上,她看到一個光頭,後腦勺呈現如V字型的光頭,就這麼闖進了她的視線中。她原以為是自己眼花,要不就是光線或角度的緣故,結果不是,這是鐵錚錚的事實。」
「女人會嫌棄禿頭的男人嗎?」賀蒙特問道。
「……我不是女人,不清楚她們的愛好。以我個人來說,禿頭是一種不可對抗的災難,因為你付出再多的心血照料和滋潤,它們未必如你所願,在光禿的頭皮上長出髮絲來。佩琪明白向我表示,不喜歡禿頭的男人,但比禿頭更讓她在意的是,韓德爾的身板太單薄了。他猶如一隻流浪的瘦皮猴!根據佩琪的形容,他走路時搖擺不定,似乎無法直線行走,以致於步下樓梯的時候,看來都像是會失足摔斷腿骨的酒客。而正是這個踉踉蹌蹌的背影,讓佩琪堅決地把韓德爾剔出名單之外。」
自由的性生活總處於邊界
「所以,經過一番淘汰賽,我就成為你推薦的人選嗎?」賀蒙特笑得無可奈何。
「沒錯。我們做旅館業的人,不僅要招呼過夜的房客、上門尋歡的男人,更要照料那些可憐的女人。」
「賣淫的女人嗎?」
「嗯。我剛從老爸接手的時候,我還沒弄懂這個道理,想法方面很單純,後來遇到許多事情,才慢慢體會出來。有一次,一個應召女結束接客,先行下了樓,待男客離去以後,又折返回來與我講話。直到那一刻,我才重新看待我們的行業。」
「說說看,也許我可以把這段故事,分享給我的小說家朋友。」賀蒙特興趣盎然地說,「因為別人的故事,不管悲慘的或歡樂的,經過合情合理的編織,它都能成為小說的最佳題材,雖然我不會寫小說。」
塞林傑帶著感傷的口吻說,乍看去,那個妓女芳汀的臉上布滿滄桑,像是永遠有解決不完的煩惱,所幸她的身材保持得很好,否則情況會更糟糕的。她不加掩飾地說,以前,她在一處停業待拆重建的飯店裡租個套房,以接客賣淫來維持生計,生活勉強還過得去。後來,那棟頹廢的飯店要進行拆除,她就此失去了營業場所,於是,四處流轉找不到生活的定點。那一陣子,她把自己的處境,形容成像一隻流浪狗,在白天和黑夜之間穿梭,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或許,上帝聽到了她的呼求,終於向她伸出了救援之手,將她指引到「新樂園世界旅館」來。他聽完芳汀的講述,心裡非常感動,尤其她噙著眼淚,用誠懇的眼神所說的那句話:塞先生,謝謝您的收留。對我來說,「新樂園世界旅館」就是我的自由聖地,因為我生活的全部全來自於它,包括我的生命和青春。說到這裡,塞林傑輕輕地嘆了一聲,「賀哥,你是個傑出的詩人,我這樣講述芳汀的故事,你應該可以想像那樣的情景吧?也許,由你寫出來更合適。」
「不,我寫不出這樣的小說,」賀蒙特說道。
「芳汀說,沒有客人上門的時候,她只能坐在房門走道上,目光呆滯地看著電梯,幻想著每個走出電梯的男人,都是來為她捧場和光顧的。當然,她仍然有振奮精神的時候。例如,用半電動式的白鐵壺燒水,待熱水噗噗地沸騰以後,沖泡一杯濃濃的烏龍茶,給自己提神醒腦。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與其說我不經意地喝著濃茶,其實並不是因為茶葉浸泡太久,而是我的下意識在起作用,我試圖要還原芳汀枯坐客人上門的心情。」
「噢,你的說法很有意思,如果把它寫成小說的話,不輸給那些無病呻吟的小說。」
「別取笑我了。這是我真實的感想,也許虛假的編造,就沒這麼感人了。所以,賀哥啊,你說我能不照料這些人嗎?地方議員帶女人來小店惠顧,我陪著笑臉都來不及了,哪有膽子和本錢得罪他們呢?」
「你若不配合聽話,像韓德爾那樣的人,隨時會通知轄區的警察來抄店?」
「哎,這事情不需要明講,放在心裡知道就好。」
「對了,我再問一遍,佩琪那個女人真的沒問題嗎?我們是老朋友了,不可在我的背後搞鬼。」
賀蒙特最後一句話,明顯帶著沉重的尾音,聽在塞林傑的耳裡,他表情和聲音出現了變化,由剛才輕鬆應對的明快語調,變成複雜和暗淡的神色。(未完待續)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我的書鄉神保町》1-10卷(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