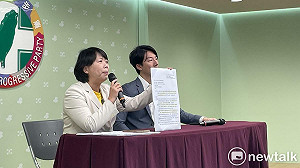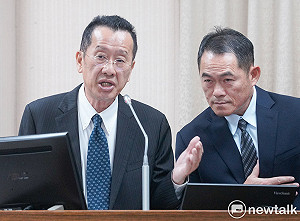中共四中全會落幕,北京隨即展開一場鋪天蓋地的宣講行動。從李強到王滬寧,再到蔡奇,領導人接力「投書」,輪番詮釋剛出爐的《十五五規劃》。其中最具風向球意義的,莫過於蔡奇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治國必先治黨,黨興才能國強〉。這篇看似是對黨務工作的常規重申,實則釋放出中共治理邏輯發生重大轉變的制度訊號。
文章揭示了中共五年規劃的深層轉向:從「經濟導向」滑向「政治導向」,從「成長敘事」走向「穩定敘事」。這不只是政策語言的微調,而是治國策略的根本逆轉。
《十五五》不談經濟,體制正式進入「習近平停滯」
自1953年以來,中共的五年規劃始終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產能布局、成長目標、改革節奏構成其正當性的主幹。然而在《十五五建議》中,這一傳統被刻意放棄。蔡奇的詮釋通篇避談GDP、投資、創新、產業升級這些過去的高頻詞彙,取而代之的,是「從嚴治黨」、「自我革命」、「紀律監督」。
這種徹底去經濟化的語言工程,標誌著中國治理邏輯的一次結構性轉變——「習近平停滯」的制度化正式登場。
這一局面令人聯想到布里茲涅夫時期的蘇聯:進入一段表面穩定、實則僵化的「停滯時代」(Era of Stagnation)。今日中國亦步亦趨:政策不再尋求突破,而是繞著忠誠與控制自我強化;不再追求發展,而是以「不出事」為最高目標。這不是「改革放緩」,而是國家治理全面轉向保守主義與自我設限。
全站首選:近6萬警受惠!政院核定調高警勤加給 刑事加成提高至8成、勤務繁重加成最多加1.3倍
「全面從嚴治黨」:從副詞變主詞的統治語法
「全面從嚴治黨」原是黨內紀律建設的修辭,如今卻被正式寫入《十五五》的指導思想,地位從副詞性修飾語搖身一變成為治國主軸。
當「治黨」成為「治國」的全部起點與落點,五年規劃這種本應聚焦發展藍圖的政策文本,徹底變質為一套政權防禦工程設計圖。
蔡奇文章中不斷重複的「嚴的基調、嚴的氛圍、嚴的措施」,體現的是當前中共治理心態的真實寫照:不是追求鬆動與彈性,而是收縮與管控;不是制度完善,而是權力強化。
所謂「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此語境下早已不再是清廉訴求,而是權力穩定機制。反腐不再針對貪污,而是針對異己。
去經濟化背後的核心邏輯:權力防禦主義
對照《十三五》與《十四五》仍高頻出現「創新驅動」、「製造升級」等經濟術語,《十五五》則幾乎將這類語言大幅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判斷力」、「風險預警」、「紀律巡查」、「防範未然」等政治穩定語彙。
這顯示中共的治理焦點,已從發展焦慮徹底轉為政權防禦。當社會壓力上升、地方債務爆表、青年失業高漲,北京已不再寄望於經濟成績換取統治正當性,而是轉向政治忠誠與紀律整肅。
《十五五》不是一份政策規劃書,而是一份避震結構設計圖。它的核心不在發展未來,而在防守當下;不在鼓勵冒險,而在規避變數。
從「發展型政黨」走向「防禦型政黨」
中共曾自我定位為「發展型政黨」,透過經濟增長來支撐其統治合法性。然而《十五五》無疑宣告這一模式的終結。
蔡奇的文章不是純粹的理論闡述,而是一紙制度化的轉向公告,昭示著中共已完成從「發展型」向「防禦型」政黨的質變。在這個新治理架構下:經濟規劃淪為維穩工具、反腐成為統治資源、忠誠取代能力、政治紀律取代市場邏輯。
GDP不再是官員升遷的KPI,創新也不再是政績核心指標。搞經濟不如跟對人,表現不如表忠。
結語:從語言治理到體制自鎖,「習近平停滯」的時代來臨
從布里茲涅夫的「表面繁榮」到習近平的「語言治理」,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大國邁向現代化的進程,而是一個封閉政體為延命所採取的體制自鎖。
《十五五規劃》是「習近平停滯」時代的官方註腳:它象徵著中國共產黨放棄經濟驅動的改革路線,選擇以高度集權、政治篩選與語言工程,建構一個封閉而防禦的統治架構。
在這份規劃中,無解的經濟、無聲的改革、無限的忠誠與無處不在的黨,交織成一場統治焦慮的制度化迴圈。而這一切,不是錯誤,而是刻意設計;不是應變,而是預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