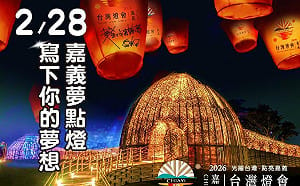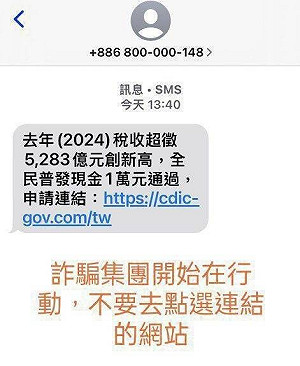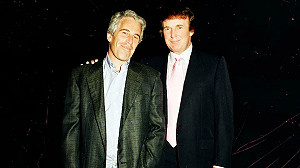《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5日刊登專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秘書長呂特(Mark Rutte)文章。呂特在訪談中提出一個引人注目的地緣政治情境:若中國決定攻打台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會聯繫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要求俄羅斯在歐洲對北約國家發動攻擊,以分散北約的注意力。此論點凸顯中俄之間潛在的戰略協同,也將2027年視為一個關鍵時間點,並點出美國在全球安全架構中面臨的挑戰。
中俄聯手威脅:戰略協同的可能性與現實

呂特在專訪中提到,若中國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習近平可能會要求普丁在歐洲發動攻擊,以牽制北約力量,特別是美國在歐洲的軍事資源。這種假設基於中俄近年來日益緊密的戰略合作關係。2022年2月,中俄宣佈建立「無上限夥伴關係」,隨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國雖未直接提供軍事援助,但被指控通過提供微電子、原料和規避制裁的雙重用途產品,間接支持俄羅斯的戰爭努力。呂特指出,中國、北韓和伊朗與俄羅斯的合作,顯示出一個反西方軸心的形成,這使得歐洲和印太地區的安全挑戰更為緊密相連。
當前熱搜:大翻車!中國官員用ChatGPT寫日記 OpenAI不忍了:跨國鎮壓駭人內幕全公開
從現實角度看,中俄聯手威脅北約的可能性存在,但受到若干限制。首先,俄羅斯目前深陷烏克蘭戰爭,軍事資源和經濟實力受到嚴重消耗。根據呂特的說法,俄羅斯在三個月內的彈藥生產量是北約全年產量的三倍,但這也反映出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的高消耗率。俄羅斯是否有能力在2027年前恢復軍力,並在歐洲開闢新戰線,是一個疑問。其次,中國對俄羅斯的影響力雖強,但俄羅斯作為一個具有核武能力的獨立大國,未必完全聽命於中國。普丁可能會衡量自身利益,避免在歐洲挑起與北約的直接衝突,因為這可能引發毀滅性的後果。
此外,呂特的論點可能有一定的「威脅放大」意圖,旨在促使北約成員國加快軍事現代化並增加國防預算。他提到俄羅斯正在以「現代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建軍力,並警告北約必須提升至5%的GDP國防支出目標,這表明其言論部分是為了推動內部團結和資源整合。然而,中俄之間的協同行動確實不可忽視,特別是在情報分享、軍事技術合作和經濟互補性方面,這可能在未來構成對北約的間接威脅。
2027年時間點的戰略意義

呂特提及的2027年作為中國可能對台灣採取行動的時間點,與美國情報界的評估相呼應。美國官員曾表示,習近平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在2027年前具備入侵台灣的能力。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一定會在該年發動戰爭,但顯示出其軍事準備的時間表。2027年作為一個關鍵節點,與中國國內政治和經濟目標有關,例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長期願景,以及在全球影響力上超越美國的企圖。
當前熱搜:很想犯台?紐時:川普透露談台灣時習近平「呼吸沉重」令他不高興
從軍事角度看,中國近年來大幅增強軍事能力,特別是在海軍和核武方面。根據呂特的說法,中國海軍艦艇數量已與美國相當,並預計到2030年將增至450艘,核彈頭數量也將達到1000枚。這種軍力增長使得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投射能力顯著提升,對台灣構成直接威脅。同時,俄羅斯的軍事復甦也為2027年的假設增添了複雜性。呂特警告,俄羅斯可能在5至7年內對北約構成直接軍事威脅,這與中國的時間表不謀而合。若中俄在2027年左右形成某種協同行動,例如中國攻台同時俄羅斯在歐洲挑起衝突,北約和美國將面臨兩線作戰的巨大壓力。
然而,2027年的時間點也需謹慎解讀。中國是否會在該年採取軍事行動,取決於多重因素,包括國內經濟穩定性、國際環境,以及美國及其盟友的應對能力。台灣問題對中國而言不僅是軍事挑戰,還涉及政治、經濟和外交層面。中國可能更傾向於通過經濟壓力、外交孤立或灰色地帶行動(如軍事演習)來實現對台目標,而非直接發動全面戰爭。因此,呂特的警告更多是基於最壞情境的假設,旨在提醒北約和美國提前做好準備。
美國面臨的挑戰:戰略重心轉移與盟友分擔

呂特的論點中,美國在全球安全中的角色至關重要。他提到,美國期望歐洲承擔更多防務責任,以便美國能將戰略重心轉向印太地區,對抗中國的崛起。這反映了美國長期以來的政策轉向,即從歐洲為中心的「大西洋優先」轉向「印太優先」。然而,這種轉向帶來了若干挑戰。
首先,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仍是北約的核心支柱。呂特否認美國正在從歐洲撤軍,並強調美國的承諾是「鐵一般的」。然而,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第二任期內的立場可能影響這一承諾。川普長期批評北約盟友在防務支出上的「搭便車」行為,並推動北約成員國將國防支出提高至GDP的2%,甚至5%。呂特在專訪中高度讚揚川普的領導力,稱其為北約達成5%支出目標的關鍵推手,這顯示出他試圖通過外交手段確保美國對北約的持續支持。然而,若美國進一步減少在歐洲的軍事投入,北約的集體防禦能力可能受到影響,特別是在應對俄羅斯潛在威脅時。
其次,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挑戰日益加劇。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對南海的領土主張,以及與北韓、伊朗等國的合作,都要求美國投入更多資源。呂特提到,若中國攻台,美國可能需要將軍事力量集中在印太地區,這將削弱其在歐洲的應對能力。若俄羅斯同時在歐洲挑起衝突,美國將面臨兩線作戰的困境,這對其軍事資源和戰略決策構成重大考驗。
此外,美國的內政問題也可能影響其全球領導力。國內政治分裂、經濟壓力以及對外援助的爭議(如對烏克蘭的軍援)可能限制美國在多個戰場同時行動的能力。呂特強調,歐洲盟友已增加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2025年達350億美元),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美國的負擔,但也顯示出美國在全球安全中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義。
呂特論點是誇大?還是警訊?

呂特的論點揭示了當前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和緊迫性。中俄之間的潛在聯手威脅,特別是在2027年這一時間節點,可能對北約和美國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雖然中俄協同作戰的可能性受限於各自的戰略利益和能力,但其合作已在烏克蘭戰爭中顯現,對北約的防禦能力構成間接壓力。2027年作為一個軍事準備的時間點,凸顯了中國和俄羅斯軍力增長的緊迫性,促使北約加快現代化進程。對美國而言,平衡歐洲和印太地區的戰略需求、應對國內外挑戰,以及維持與盟友的團結,是未來幾年的核心任務。呂特的言論不僅是對潛在危機的警告,也是對北約內部凝聚力和資源分配的呼籲,目的在確保聯盟能在未來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中保持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