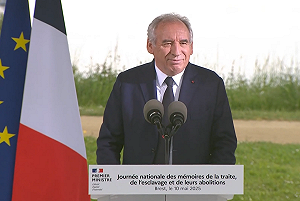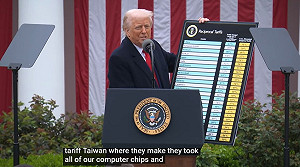【合法閃兵的我,無法心安】
近來多位藝人因兵役問題引發社會爭議,「閃兵」這個詞再次浮上檯面,引發民眾對公平、責任與制度正義的深層討論。事實上,這不只是名人現象,更是整個制度設計與社會價值觀長年累積的問題。而我,也曾是其中一員。今天,我願意誠實地說出自己的經歷,並公開反思。
當前熱搜:逼江啟臣吞下?黃士修揭楊瓊瓔洩民調期程盤算:就問黨中央管不管
我在1989年隨父母移民加拿大,取得當地國籍,之後依法登記為中華民國的僑居國民。1999年返台後,我長年在台生活與工作,每年超過300天待在國內,與一般國民無異:工作、納稅、享健保、參與投票。但為了避免服兵役,我選擇依規定每四個月出境一次,以維持形式上的「僑民」身份。只要不在國內停留超過規定時限,兵役機關就無法將我認定為常住國民,我也因此「合法」地迴避了兵役。現在雖然法令有更嚴格的修正,但要當閃兵,有資源的人依然做得到。
那時的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畢竟「合法」就是「合理」吧?但隨著年歲漸長,社會歷練與國際局勢的變化,我逐漸意識到:這不只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價值觀的問題。我享有這個國家的一切權利,卻在最基本的公民義務上選擇逃避。這樣的我,還配說自己是台灣人嗎?
【閃兵不是特例,而是制度漏洞的結果】
當前熱搜:「藍白立委會一直擋國防特別預算到美國出面」吳嘉隆:在等下台階
我知道,我不是唯一這麼做的人。許多在國外長大的雙重國籍者,也多半以相同方式閃避兵役。更不用說那些透過醫療免役的知名人士:演藝圈與政界圈中,不乏身體健壯卻獲判「不適服役」的案例。他們在舞台上奔跑跳躍、政治活動上用超高分貝的音量激情演說,似乎與所謂「免役體位」明顯不符。社會自然會質疑:這真的是一套公平的制度嗎?還是某些人憑藉資源與關係取得了「特權通行證」?
這樣的現象,正是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家 Michael Sandel 在其著作《What Money Can’t Buy》中所批判的核心問題。他指出,當公共責任變成可以用金錢或社會資源「買斷」的選項,社會便會出現階級斷裂。當富人可以逃避義務,風險與責任就會落在弱勢者身上。
【國際典範:為何民主國家仍堅持義務兵役】
在許多民主國家,這樣的價值觀早已被制度化為全民共同承擔的義務。瑞士所有成年男性皆須服役,無論身份地位;挪威不僅實施義務役,還擴大到女性,視其為平權的一環;芬蘭面對強鄰壓力,更堅守全民役制度,將其視為國民團結與國防精神的象徵。
不僅如此,歐洲皇室與美國政治菁英更以親身服役為榮。英國查爾斯三世、威廉王子與哈利王子皆有軍旅經歷,哈利王子更曾兩度派駐阿富汗;瑞典王室成員也接受軍事訓練;美國歷任總統如艾森豪、甘迺迪、老布希、小布希與曾經參選總統的已故參議員麥凱恩等,皆有服役背景。在他們看來,兵役不是階級的負擔,而是領袖的資格證明。
【台灣也有典範:他們可以閃兵卻選擇承擔】
台灣社會中,也有值得敬佩的例子。像吳怡農與何志偉兩位政治人物,皆出生於美國、擁有美國國籍,依法完全可以申請僑民身份,像我當年一樣合法閃兵。但他們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自願返台服役,親身進入國軍,履行國民責任。他們沒有因為背景或資源而選擇豁免,而是用實際行動表達對國家的承諾與對公平的堅持。
他們的選擇,是對我最強烈的提醒。我當年有空間選擇,也選擇了逃避;他們卻在可以逃避的情況下選擇了承擔。這份勇氣與愛國情操,值得我誠懇地說一聲:敬佩。
【全民皆兵,不只是口號,也應包括女性】
更進一步地,我認為台灣是時候推動「全民皆兵」的真正精神,實現性別平等服役。現代戰爭早已不再是泥濘戰壕裡的肉搏戰。今天的軍隊需要的是資訊安全、無人機操控、後勤管理、醫療支援與通訊作戰等多元能力。軍隊不是只有前線步兵,也有大量需要女性參與的專業崗位。
如果我們真正相信男女平權,那麼服兵役這件事,也不該只交給男性。挪威與瑞典都已證明,女性也能有效參與國防,不僅提升軍隊整體戰力,也讓國民認同更為均衡。台灣的女性早已在科技、教育、醫療等領域展現領先實力,在國防體系中自然也能扮演重要角色。
【把一年的時間捐給國家,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作為一個國民,把一年的時間捐給國家,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榮譽。 國防不是別人的事,不是志願役的事,不是窮人的事,更不是男生的事,而是你我的事。國家不是政府的抽象名詞,而是我們每天生活的這片土地,而這片土地的安全,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守護的。
《經濟學人》在2021年曾以封面指出:「台灣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我們面對的不是假想敵,而是真實威脅。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我們還以逃避為榮,以規避為聰明,我們將失去的,不只是國防戰力,而是國民的凝聚力與社會的信任感。
【結語:從懺悔到行動,讓兵役重新被尊重】
我願意承認,過去我是閃兵的一員;如今,我願意誠實面對,也希望社會能正視兵役制度中的不平等,重新賦予服兵役以尊嚴、正義與價值。
如果未來的台灣,能讓所有人無分貴賤、性別、背景,都以服兵役為榮,並以保衛國家為天職,那麼我們就不再只是「生活在最危險的地方」,而是「擁有最堅強人民的國家」。
作者:陳柏同/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