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聰明睿智的人,也不知其深度,對勤奮用功的人,也不知其真諦,我的思想在世上找不到接受者,如同海水只能在自己體內老去。----法稱(古印度詩人)
8.
抵達天龍國站以後,我抬手看了看手錶,時間還很充裕,便信步到附近的書店,我想藉著這個機會,考察同業的出版品,以作為日後精進的基礎。因為接下來,我就得著手處理嚴向冬的書稿了,現下,凡是有參考價值的圖書範例,都是我刻不容緩效法的對象。坦白說,我不希望嚴向冬的勞苦力作,由於我的因循苟且而毀了。而且,我期待這部編著問世,能夠引起歷史迷的關注,儘管它最終會被擺在書店內冷僻的位置,依然有讀者陸續前來購買,但我不願像卑劣的同行一樣,背著櫃檯人員的視線,將已被束之高架的自家圖書,若無其事似地把它擠在平擺書台上。
全站首選:中國網軍4千帳戶攻擊高市早苗 矢板明夫:台日兩國正面對相同挑戰
逛完書店,我來到馬僮任職公司的附近,給他打了電話,他若是得空的話,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彼此的近況。
「您好,請問馬僮先生在嗎?」
「噢,馬主編正在開會耶,」接電話的是一位年輕小姐,她的聲音很甜美,洋溢青春與活力,「先生,您要不要留個電話,開會結束以後,請他給您回電。」
「這樣子啊。我是馬先生的朋友,我叫譚定,天方夜譚的『譚』,安定的『定』。我沒什麼要緊的事,剛好路過這裡,很想請他喝杯咖啡敘敘舊而已。待會兒,麻煩請他回電。謝謝您。」我向那位小姐報上自己手機號碼。
說到我與馬僮的重逢,還真是充滿戲劇性的曲折。
兩年前的夏天,我在萬年春麵館吃水餃,店內的電視機正在播報午間新聞,女播報員嘰嘰喳喳地說著,隨後又插入了長長的廣告,賣痔瘡藥、保健食品、感冒藥、勞動階層專用的威而鋼飲料、治療坐骨神經痛的診所等等,種類之多不及備載;彷彿所有臺灣人都是潛在的病患,不認識這些廣告的效用,隨時都會被疾病和不安所吞沒似的。對於這樣的商業廣告,我自然是不感興趣,除非播報重大的社會事件。說來正巧,當我在心裡犯嘀咕之際,虛張聲勢的商業廣告突然中斷了,插入了一則衝突流血事件的畫面。一群高舉著赤魷黨旗幟的激進派人士,極盡招搖地經過紅龍魚站,不僅如此,他們將擴音器的聲量放到最大,完全鄙視《噪音管制法》的存在,一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態勢,其囂張的氣焰猶如要把整個天空撕裂一樣。在這當中,有路人看不慣出言制止,他們馬上露出流氓的本色,作勢追打跟他們說不的市民。有幾次,他們不只是口頭恐嚇,最後因爭論不過對方,索性以旗桿往異議者的身上死打,驀然間,悶重的聲音,一記又一記的響起;其中,一個高頭馬大的女人,出手更毒辣了,竟然把其手中的旗桿都打斷了,無疑要讓路過的市民見識其恐怖份子的殘暴性格,並藉此大肆宣傳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統治術。
接著,畫面轉到了一個中年男子的臉上。他的個子不高,長相很清秀,但他的左眼角淌著血痕,身上的白色短襯衫也沾著血跡。一個女記者將麥克風伸在他的面前,問他對這起暴力攻擊事件的看法。中年男子大概過於悲憤了,神情十分嚴肅,一下子,沒能找到恰當的言詞來表達心中的忿怒。後來,他的面前又多了三支麥克風,這形成了一種壓力,要他立刻停止沉默,譴責這樣的暴力事件。
「對,我們應該譴責這種暴力事件,」他的嘴唇微微顫抖著,「臺灣是個自由民主體制的國家,每個人都享有表達思想的自由,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是,絕不能使用凶殘的暴力攻擊對立的異見者。你不同意對方的政治觀點,可以透過辯論一較勝負,就是不能以大欺小,欺凌弱小的一方。」
「你怎麼看待那個拿旗棍打你的趙大媽呢?」
「趙大媽?」他雙眉深鎖似地說,「哎,這個外國媳婦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她大老遠從獨裁體制的赤魷國嫁到臺灣來,而且,在自由的土地上,生活了十幾年了,取得了本國居民身份證,充份體會到自由社會的美好。但諷刺的是,她卻背道而馳,強迫我們接受獨裁的體制,灌輸我們暴政的思想。這不是很荒謬嗎?」
「不過,據赤魷黨的支持者說,你們的排外意識太強烈了,打從心底鄙視赤魷國來的人。關於這點,你能否認嗎?」一個自稱「烽火連天電視台」的女記者,以挑釁性的口氣問道。
乍看去,原本中年男子有點消氣了,一聽到女記者這般詰問,頓時,又怒火中燒了起來。他似乎在心裡臭罵了幾句。不過,他知道這時候要冷靜下來,否則說錯了話,詞不達意的話,將會掀起另一場風波來。
「這是赤魷黨人的慣用手法,先給對方潑了髒水,再說他們回潑髒水,是反射性的動作,更是正當防衛。你相信他們的說法嗎?」
「先生,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女記者咄咄逼人說道。
「我沒回答你的問題?」他臉上掠過不屑的冷笑,「我覺得,你用這種口氣採訪受害者,已經失去記者的客觀立場了。」
「……」女記者一時語塞,但隨即不甘示弱地問道,「至少,你要承認赤魷國是強大的國家吧?」
「強大的國家?這跟我有什麼關係?現在,我要表明的是,自由的世界與獨裁的世界,是對立而不可相容的。難道你反對這個說法嗎?」
「先生,我覺得你有點強詞奪理,」女記者怒不可遏地說,「趙大媽說,你先是以言詞激怒她,用不屑的眼神踐踏她,讓她陷入了混亂的思緒裡。而那時候,你已克制不住憤怒之火了,整個頭顱頂了過來,她基於正當防衛的心理機制,不自覺得地揚起手中的旗桿擋著,自然的結果就是,你的左眼角掛彩了。」
「哈,你的意思是,我的左眼角流血自己造成的?責任在我身上?與趙大媽一點關係都沒有,要怪就怪那支旗桿是嗎?」
他連珠炮似地說著,或許反諷的修辭發揮了作用,惹得在場的市民哄然大笑,倏地,劍拔弩張的氣氛,多了些歡笑的波紋。
「是啊,赤魷黨的棍子是不長眼睛的,都是這位先生的錯啦,搞不好,那個趙大媽要他向旗桿賠不是呢。」一個六十出頭的男性市民打趣地說。
這個笑話,又引來了一片笑聲。
然而,原本被勸擋在一旁的趙大媽,一聽見對她的呼名,旋即推開身旁的市民,一個箭步撲了過來,準備給他補上一記拳頭。不過,在他面前因電視台女記者擋著,加上六七支麥克風,形成了特殊的防護網,趙大媽的拳頭才沒擊中目標,否則他的左眼角又要開裂了。
在那之後,轄區的警察終於趕來了。趙大媽及其赤魷黨人悻悻地離去,臨走之前,他們還惡狠狠地瞪著掛彩的中年男子。一場因政治意識型態對立的衝突流血事件,總算降下了帷幕。
接下來,換我被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喚醒了。剛開始,我只注視著中年男子血痕猶在的左眼角,而忽略了他嘴巴右下方有一顆黑痣。噢,他應該就是我的國中同學馬僮!因為他的嘴角也有一顆黑痣,而且,不管從身材年齡和面貌來看,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一旦認出了他面相的特徵,我就有更大的自信認為,那名左眼角被惡意的旗桿打傷的中年男子,即是闊別了三十餘年,未曾見面的同學馬僮了。
為此,我立刻打了電話給克拉克博士,因為他的人脈很廣,消息非常靈通,有文化界地下情報局局長的美稱。我相信,只要委託他,要找某個失聯的朋友,描述那個人的各種特徵的話,很短的時間內,他即能回報好消息。
翌日上午,克拉克博士果真捎來了電話。
「譚定啊,你的尋人啟事,有著落了。」
克拉克不改平日的幽默,將我要確認一個失聯的同學的身份,比擬成因人生各種困難而導致的「尋人啟事」。這個引喻與日本二戰後的處竟很相似。那時候,整個日本社會尚未從混亂中恢復過來,廣播電台有「尋人時間」的節目,在公共澡堂裡,經常可以聽到播音員以緩慢而清晰的口吻,說出通報者的姓名與地址和失散者的名字,他們用這種方式尋回離散未歸的親朋好友。
「謝謝!那個被打傷的人,真的是馬僮嗎?」
「沒錯,就是他。」
「念國中的時候,他體格瘦小,經常被大個子的同學欺負,想不到他比變得勇敢了。」
「這樣子啊,這段小歷史我不清楚……。不過,一個時常挨打的人,若能變得敢於面對棍棒的威脅,這終究是一件好事。至少,他已經做好心理準備,恐怖的效力就會減少許多。」
「對了,那個大骨架的女子,下手為什麼如此狠重,將矮個子的馬僮打得頭破血流了。她是不是針對馬僮而來的?」
「是啊,你也看出來了。」克拉克博士清了清嗓子說,「現在,馬僮是《海馬斯論壇報》的主編,三天兩頭就在自家的刊物上,用最激烈的措詞批判赤魷黨的反社會行為。不用說,他這番言論馬上成了赤魷黨的眼中釘,而信奉暴力流血的黨徒們,早就想修理他了,現在於半路上認出了他,必然要對他揮棍制裁。」
「趙大媽是該黨的核心人物嗎?所以,採取如此激烈的手段?」
「嗯,」克拉克博士解釋道,「我們從受害者的受害程度(包括屍體毀損),可以反映出那個施暴者的殘暴心理。馬僮被打得頭破血流,表示他們並非致他於死地,而是要展現暴力的恐怖,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使強大的暴力,來制裁所有與他們針鋒相對的反對者。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僮只是流血掛彩,他們還沒對他進行海豹部隊摸哨時的勒頸鎖喉呢。」
「這只是小菜是嗎?」我說。
「是啊,」克拉克博士笑了笑,「話說回來,馬僮還是有兩把刷子。他身材矮小很吃虧,但他卻善用文字的力量來扭轉頹勢。簡單講,赤魷黨的成員多半是暴力分子,識字程度不高,談不上論述的能力。在智力上,馬僮顯然是占了上風,可是在體格上,他永遠處於不利的下風。」
克拉克博士談笑風生地說起馬僮的現狀,以及他與赤魷黨人的政治對立所掀起的風浪,不由得使我與馬僮同窗讀書的往事連結了起來。(待續)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文化隨筆三部曲《日輪帶我去旅行》、《我的枯山水》、《燃燒的愛情樹》(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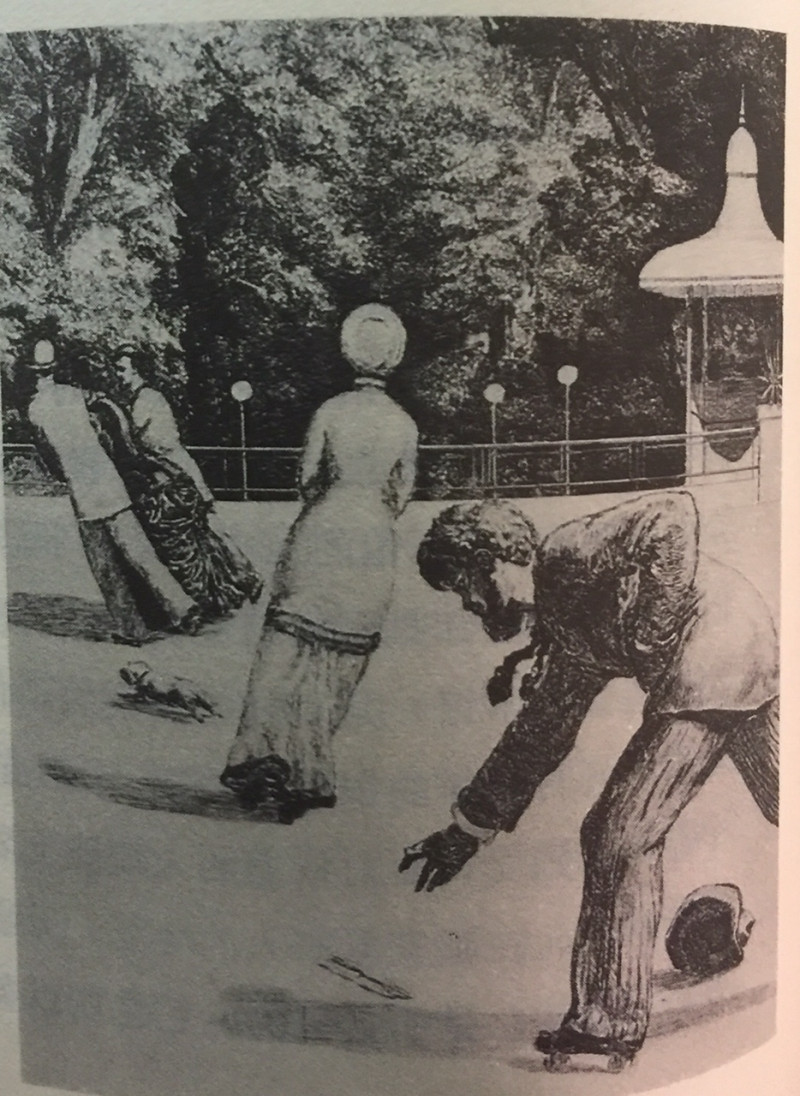





![[影]年假尾聲曬萌犬片!賴清德分享蔡英文帶「樂樂、鳳梨妹」作客官邸](https://images.newtalk.tw/resize_action2/300/album/news/1021/699b1786a6f50.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