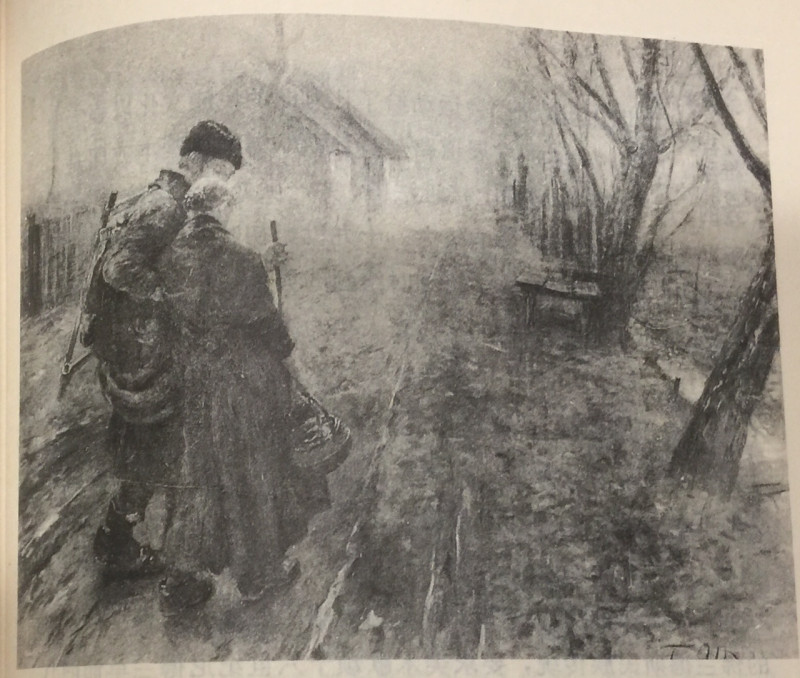對聰明睿智的人,也不知其深度,對勤奮用功的人,也不知其真諦,我的思想在世上找不到接受者,如同海水只能在自己體內老去。----法稱(古印度詩人)
7.
「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有,當然有。首先,他們料定老實的作者不計較,不會向他們提起版稅的事,所以,證明他們的做法值得鞏固下去。其次,讓作者置於晦暗的狀態,他們更容易上下其手?」
「上下其手?」
「例如,作者的書銷路不錯,自然有增刷的必要,但這時候他們卻不通知作者,而是悄悄地一批批加印,偷賣了幾十刷,悶聲發大財了,作者還以為自己的作品,未能得到讀者的青睞而沮喪不已。換句話說,他們對待國內的作者況且如此了,長年旅居國外又甚少回國的作者,哪會知道他們的地下活動呢?」
當前熱搜:朱蒲青觀點》東京巨蛋的一場加油 為何在台灣變成政治戰場?
「哇,真是令人不敢置信啊。」他驚訝的程度比剛才更強烈了。
「還有一種很不幸的畸形的情況,」我稍為整理思緒地說,「如果出版社的總編輯恰巧是個作家,儘管沒什麼真材實料,但其最後也不會有好結果。」
「這話我就聽不懂了。」
「好吧,簡單講,拿薪水的總編輯同意出版同輩的作品,其實是作者受難的開始。新書出版以後,總編輯刻意不推廣,消極地把新書擺在倉庫裡,目的就是讓新書變成舊書,讓它們與厚重的灰塵為伍,以這種方式來折磨作者的才氣。而且,作者簽了十年合約,即使後來發現有異狀,他什麼也做不了。所以,有一本幽默小說形容這種怪異的現象,作家遇到不良的出版商,如同給自己判了十年徒刑。為了從這種狀態中脫困出來,作家就必須具備兩個身體。」
「作家怎能有兩個身體呢?」他睜大眼睛問道。
「哈,意思是說,作家的一個身體被關在合約的監牢裡,十年之後才能出獄。在這種情況下,作家必須擁有另一個身體,去找其他的差事賺取生活費。也就是,作家若沒能練得分身大法,他的日子就難過了。諷刺的是,這卻是那樣的總編輯樂見的結果。」
看得出來,嚴向冬的表情逐漸在變化,從原先詫異的和旁觀的立場,明顯變成了不予苟同。他心想,作者辛勞地完成了一部作品,找上出版社洽詢,這時候代表公司的總編輯,經過一番評估,並得到老闆同意出版,就應當盡力推廣才是,怎能反其道而行呢?如譚社長所說,他不但不積極宣傳,還要批評作者的作品,寫得多麼糟糕……,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眾所周知,出版社即使生意慘淡,照樣得持續出版才行,否則很容易淪為無書可賣的出版社。說來悲哀,在我們業界裡就有掛羊頭賣狗肉的業者,而且,他們對外還以文化人自居呢。」
「可是,就我的理解,成立出版社不就是要出版新書嗎?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用途嗎?」
「哈,用途可多呢。譬如,遇到國內發生重大災情、書市大蕭條的時候,他們可以向文化部門申請紓困補助,而政府為了拯救藝文出版活動,只要申請者符合相關的條件,很快就會撥用紓困金的。諷刺的是,對不專心經營的出版人,領取政府的紓困補助金,比他們劣質的出版品的銷售來得多。」
「如果沒有新的出版物,他們拿什麼申請呢?」
「那還不簡單,就以舊的出版品重新改裝,或者動得手腳,調換舊書的排版,這招借屍還魂的手法,輕鬆就能騙過文化部門的眼睛。」
「哎,」他不禁又嘆了一口氣,「聽您這麼一說,我原先對出版社很有好感的,這下子全崩塌了。我知道社長是個正派的人,不會誇大其詞,但我真的不敢置信,有人以此辜負政府的美意。」
「嚴先生,那不叫做辜負,而是惡意和濫用。我的朋友克拉克博士很幽默,他說,這種人就是稅金小偷,廚房裡的偷油婆(蟑螂)。」
「……一個人被說成是蟑螂,實在很不值得。」
「是啊,人與蟑螂,終究是不同的。我再補充一下,偽善的總編輯為何要暗算競爭對手作者的心理。這一開始,他就有針對性的。倘若換成了別人,就會往對他有利的方向發展。好比,總編輯一心想奉承哪個作家,他就會施展借花獻佛的手法。」
「……這樣做,對他有什麼好處?」
「有的。從人性的角度來看,這可是八面玲瓏的高招。首先,他利用出版社的資金,拉抬該名作家的作品,而受惠於此的對方,就欠下他的人情,以後,就得以某種方式回報。」
「要怎樣回報?」
「立竿見影的回報是,作家將透過各種人際關係,介紹他給媒體雜誌寫專欄啦,主持廣播節目啦、不定期到大學演講啦、當個短期的大學講師等等。」
「原來如此。」他恍然大悟似地說,「還有更超前的佈局嗎?」
我點了點頭,對著他說,他們擔心哪天被炒魷魚了,一時找不到工作,也是會焦慮的。所以,他在位的時候,就得想法設方廣結善緣,其實是公器私用,真到了他下台的一天,那些曾經受惠於他的作家,自然會以最快的速度,幫他找到下個工作。您說,這不是未雨綢繆,什麼才是未雨綢繆呢?
「我是個直來直往的人,沒辦法弄得這麼複雜。不過,也真為難那樣的總編輯了,為了一份差事,為了私人的打算……」他的語氣中充滿著同情,沒有半點反諷的意味。
「無論如何,這只能說是性格決定人的命運吧。事實上,還有比這更惡劣的不幸事件呢。」
「社長,我覺得剛才您提的內幕,已經使我感到沮喪的了,為什麼還有更不幸的事件?」
「我知道談起這種遺憾的事件,一定會令人掃興的,雖然它只是罕見的突發事例,但反過來說,今天我們之所以談它,是因為要避免悲劇再度重演。一個年輕女子不能白白地死亡……」
「枉然而死嗎?」
說到這裡,老先生告訴我,他那個兒子「不在」了,幸好,老天垂憐他,還有一個孝順的女兒,經常回家探望他們兩個老人。然而,當我提及一個年輕女子不能平白死去的時候,他作為子女的父親依然為這年輕女子的離世感到惋惜。在我看來,這就是偉大慈愛的體現,它勝過任何的巧言善辯。
「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我沒等他從淡淡的感傷的情緒中恢復過來,就逕自說道,「有一位遭受身心重創的年輕女作家,花了三年的時間,完成了一部自傳式的小說。照理說,她可以運用老師的關係代為推薦的,正如那位長袖善舞的總編輯一樣。可是,這年輕人很了不起,她不想攀關係或走後門,而是要以自己的力量取得出版的機會。之後,她捧著列印的小說稿,拜訪了好幾家出版社,可惜都被打了回票。不過,這些挫折並不能打敗她,她繼續往希望的方向前進。有一天,她造訪了某出版社的總編輯,以為對方同為女性,應該比任何人更理解她那幽微的心靈世界。在那場會晤中,她們總共談了四個小時,氣氛十分融洽。一般來說,與初次見面的人交談,心裡多半有所保留,但她是個天真率直的女孩。即使總編輯問起私密的問題,她都坦誠回答,毫不留下退路,諷刺的是,這種和盤托出的坦誠,竟然成了她的索命符。」
「有那麼可怕嗎?」
「總編輯快速看過她的小說稿,又與她做了四個小時的深談,同意出版這部小說。只是,它必須有附帶條件。」
「既然答應出版了,為什麼提出附帶條件?」
「乍聽下,這個附帶條件對女作家是有利的,但細究起來,它如同一條柔軟的鎖鍊,要牢牢地套在她的脖子上。」
「這話我就聽不懂了。社長,您能夠說的更詳細些嗎?」
「抱歉,我這樣轉述的時候,心情依然是激盪的,雖然我不認識這位女作家。」我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總編輯要求女作家出具接受過精神治療的病歷,而女作家本人同意了,答應下次造訪的時候帶來。如果事情到此,還不致於推向悲觀的終點,出版方這個附帶條件,那倒不算是苛刻的。偏偏問題不是這麼單純。總編輯說,除此之外,女作家必須配合出版方所有的行銷活動。例如,他們會安排她出席電視台的綜藝節目,在受訪當中,配合主持人既定的提問,逐一地坦承自己的創傷史,以博取觀眾的憐憫與同情。因為這將有效突顯這部新人小說的話題性,有助於提升銷售量,倘若反應熱烈的話,就順勢操作把它打造成超級暢銷書。這與出版社花錢買排行榜相比來得划算。」
「後來,女作家答應了嗎?」
「沒有。對女作家來說,她只希望自己的小說出版,證明她對文學的熱愛,不想被當成廉價的消費品,更別說成為總編輯操縱的木偶了。後來,她經歷了內心的掙扎,不過最後仍然鼓起了勇氣,拒絕了總編輯的附帶條件,並要求退還小說列印稿。這時候,心高氣傲的總編輯有點惱羞成怒了,但又不想放掉差點到手的天鵝,只好以退為進地說:我承認,你是個很有才華的新銳作家,可是你沒有任何知名度呀,所以,我才用這種方式來行銷你的小說。對你而言,這可是利大於弊的機會,有什麼好猶豫的呢?……我知道,你有自己的堅持和理想,而再美好的理想,小說出版沒能暢銷的話,它只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幻影罷了。這樣好了,你的小說我暫為保管,你回家沉澱一下,一定可以體會我良苦的用心,到時候,我們再簽合約……」
「我覺得,這位總編輯真會說話,兩三句話就能把人捆綁了起來。社長,每個出版社的總編輯都這麼厲害嗎?」
「不,就我所知,大部份的總編輯都是正直努力的人,否則老闆不會將這個重責大任交給他們。也許,我剛才提到的兩個總編輯比較特殊吧,他們對於人總是有著深不可測的算計。令人惋惜的是,那位女作家自殺了。」
「傻孩子!為什麼要自殺呢?他們不出版的話,再找其他家洽詢,不必用這麼決絕的手段啊。……發生了這種悲劇,那個總編輯沒有半點罪惡感?」
「那總編輯是否因為這起事情而自責,我無從得知也無法證實,只知道,後來引起了社會的嘩然,批評的聲浪撲向了她,指責她違背了出版人的良知,只為了追求利益,而罔顧人性的尊嚴。然而,總編輯並不認為必須對此負有責任,她只對自殺事件表示遺憾和惋惜。過了幾天,她看到批判的聲浪仍然沒有消退,便打電話給消防勤務中心,說她壓力太大要跳樓自殺……」
「真的?」
「哈,怎可能真的跳樓啊。」
「為什麼?」
「任何一起事先張揚的案件,往往是一種表演前的廣告,預告有自殺的動作,但不會真的跳樓身亡啦。這種戲碼最常出現在政治閙劇的表演上。我只能說,那總編輯善用這個手法,真是不簡單的人物。」
「結果,如何收場?」
「總而言之,這可苦了消防隊員,他們緊急趕到她住家的樓下,快速地鋪置大型的氣墊,還派出了有伸縮功能的照明車,一邊以希望的燈光照向她立在公共階梯的身影,一邊以擴音器施予勸說。這時候,酷愛灑狗血的電視台和新聞記者女士先生,早已聞訊趕到樓下附近,用激揚的口氣報導這場世紀性的自殺表演。」
或許,我對這起事件的描述過於具體而詳細,讓他再次陷入了沉默的深淵,他向我投來淡然悲憫的眼神。我讀懂並感受到這眼神的意義。所以,我趕緊補充說道:
「嚴先生,一樣的米養百樣的人,您不要因為我對她的負面評述,而對人性感到失望。……我會盡最大的努力處理您的書稿,讓它早日問世,邀請更多的人關注臺灣的歷史。」
約莫一個鐘頭以後,我與他在附近的餐館共進午餐,又盡興地談了一會兒,我向他告辭,他堅持要送我到雷馬克站乘車,我領受了他的好意,邁著大步跨進了車站內。然而,我沒跟他說,待會兒,就要去找我的同學馬僮了,那個退他稿件的《海馬斯論壇報》主編----馬僮。(待續)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文化隨筆三部曲《日輪帶我去旅行》、《我的枯山水》、《燃燒的愛情樹》(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