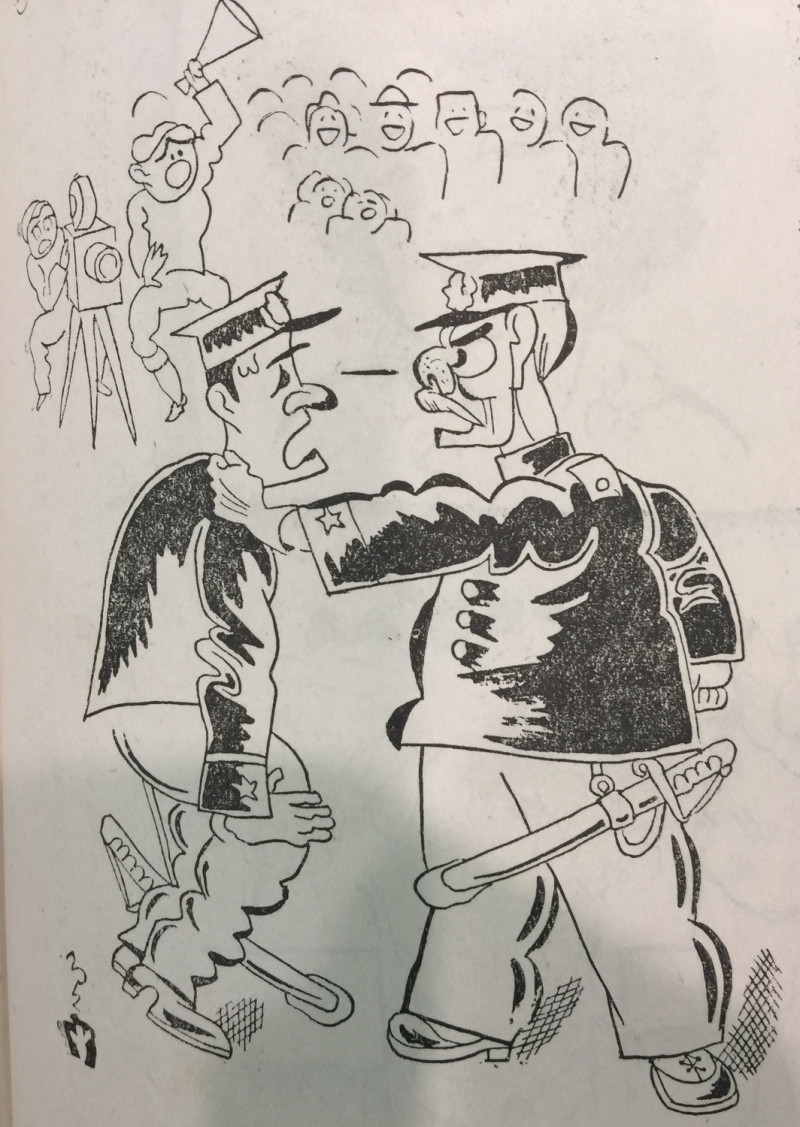在這個價值錯亂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講述自己的故事,以獲得嶄新的身份,找回有意義與價值的位置。這部小說藉由一個徬徨的青年作家,為了解封性愛的苦悶和對生命的探求,得到一個老政治犯的思想啟迪,從此走出思想的困境,進而了解底層人物的心聲,揭示存在於臺灣社會內部的禁忌和荒誕樣相。同時,這也是由壓抑的性愛通往政治思想解放的現代喜劇。
第一章、百樂門
通往對話的路徑
現正最夯:港媒披露劉世芳外甥涉中資爭議 內政部回應
查利提看見史高治對於悶熱的煎熬,似乎沒有太大的感受和回應,這等同於他提起的這個話題失敗了。因為沒有對象的說話,只能是喃喃自語,它永遠無法構成對話的事實。查利提是個見多識廣的人,並未因此用譏諷的語言,來捉弄這個年輕人,反而主動釋出長者的善意,拿起冷氣機的搖控器,對準牆上的室內機,用力按了兩下,由微風升到強風程度。果不其然,他這小小的動作改變了全局,整個辦公室裡頓時涼爽許多,這意味著他們之間的聊談,獲得新的開始。
「對了,高治老弟,我聽克拉克博士說,你在寫作上遇到瓶頸,找不到合適的題材,是嗎?」
「嗯……」史高治囁嚅了一下,像是在思索恰當的用詞,以保持體面和個人尊嚴。不過,他也知道不能讓董事長等候太久,應該給予恰如其分的回覆,在這時候,他不能出糗,要爭取好印象才行。「寫作是一件苦差事,很不容易啊。朋友說,我的頭髮掉得很厲害,跟我寫不出稿子,有很大的關聯。他們打趣地說,這就叫做『壓力山大』。我想了想,這話是有點道理。」史高治只說自己掉頭髮,其實是在暗示他沒取下貝雷帽的原因。嚴格講,這種說法極富修辭技巧,說因壓力過大導致掉頭髮的自嘲,總比坦承壓力讓頭皮毛細孔燒焦長不出頭髮來得有利。
全站首選:11億校產全捐國家 修平科大宣布停招 擬併國立暨南大學
「我是個生意人,不懂你們作家的實際狀況,雖然我也寫過兩冊書,但是我相信,這與文化和文學寫作是有所差距的。」
「噢,董事長,您忙碌之餘也在寫作嗎?」
「那是以前的事。現在,眼力和體能都不行了。你看,我這條手臂和手掌,」話畢,查利提抬起手臂伸到史高治的面前。意思是說,仔細看看他的手臂,就知道他的身體狀態。
史高治依照查利提的指示,朝他的手臂仔細打量著。或許,史高治有點緊張,前前後後看了幾遍,似乎沒能看出任何端倪來。他只覺得,查利提的皮膚粗糙,缺乏健康人應有的光澤。直到他再次端詳的時候,才發現了新的事證。查利提的手背上有許多小紅點,不細看的話,還真的不易分辨出。
「你看出來了嗎?」
「董事長,小紅點是什麼回事?」
「這個啊,扎針留下的痕跡。」
「您的意思是,中醫師為您扎針的嗎?」
「不是,我自己扎的。」
「這屬於侵入性的治療,自行扎針是很危險的,除非您之前學過針灸的技術。」
「不,這等小事情,不需要中醫師出馬,我自己來就行了。」
「這樣不好吧?」
史高治感到疑惑了。剛才,查利提董事長問他寫作方面的問題,怎麼扯到扎針的話題來了。這與向他求助出版贊助費有關嗎?
「老弟,你怎麼不問我,為什麼自行扎針呢?我覺得,這也是發掘寫作題材的機會。」
「噢,說的也是。」史高治順著這個開頭問道,「為什麼呢?現在,臺北市區,多的是有健保給付的中醫診所,給中醫師診治不是來得有保障嗎?」
「這就是問題所在,老弟!」
「咦?」
「我告訴你一個祕密,你參考看看。說不定將來對你有用。」
史高治默不作聲,等候查利提往下說,他不希望接錯話題,回答的不得體,到時候好不容易爭取的出版贊助費,就要煙消雲散了。
「大概我三十幾歲的時候,參加了兩次讀書會,認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直到現在,我仍然覺得在我的人生當中,那是我最感到自豪的事件。」說到這裡,查利提喉嚨有些發乾的樣子,於是拿起辦公桌上的保溫瓶,扭開黑色的蓋子,就著嘴裡仰頭喝了兩口。僅只數秒之間,他的嘴唇受到了潤澤,而露出舒服的表情。
「後來,這事情卻急轉直下,我們的讀書會被車輪黨的特務給滲透了!所有的成員全被抓了。我雖然不是核心成員,同樣在牢裡蹲了五年。你說,這經歷不恐怖嗎?」查利提見史高治緘默不答,吞嚥了一下,繼續說道:「打個比方,當年我們同樣都是這個年紀,不過,你卻比我幸運多了,克拉克博士介紹你來我這裡尋求出版贊助,而那時候,我卻被捲進了一場政治思想案,整個人生從此全變了調。同樣的年齡,你在找尋寫作的路子,而寫作卻與我完全無關,若說有什麼相關的話,那就是我對於封閉空間的回憶。」
題材在此筆在他處
不知道查利提是否刻意引到這話題來,或者要向史高治試探什麼,有著冬蟲夏草能耐的史高治,看見機會不可失,終於抓住這個話語的尾巴:
「董事長,您的經歷很精采,沒有把這故事寫下來嗎?」
「我不是文學青年,沒能力寫這種東西呢。再說,就算寫了,大概很難得到共鳴吧。」
「……」史高治又陷入了沉默,似乎在尋思恰當的說法。
「噢,我想起來了。如果你對這段經歷感興趣的話,可以看看《來信》這部小說。聽我的朋友說,小說裡提及的人物,與我的經歷很相似。」
「《來信》?我不知道這部小說耶。」
「不知道?」查利提的語氣突然轉強了,多少帶有責難的意味,身為文學青年的作家,為什麼不對臺灣的政治小說多點關注呢?看來,無病呻吟和不著邊際的文字遊戲,總是比質樸誠實的作品來得強大,用詩人伊謨尼斯基的說法,那些無意味的地下軍團的螞蟻們,輕易而舉就能咬掉有意義的樑柱,儘管沒能當場塌陷,也會讓它風來就倒的。
「好吧,《來信》作者是誰,並不重要。總歸一句話,經過那段日子以後,我的肺部變得很糟糕,碰到流感來襲的時候,一個不小心,我就要送急診室了。哎,這些令人驚聳的事情,我太太最清楚不過了。」
「……,後來,董事長怎麼處理呢?」
「怎麼處理?這還用說嗎,我太太就帶我到各大醫院報到,請西醫為我治病。她是個講求科學實證的人,堅持相信西醫的專業技術,不容許有任何懷疑,你若對西醫的治療方法說三道四,就會引來家庭戰爭,整個晚上,彼此都別想睡個好覺。她認為,中醫的治療時程太慢了,病人來不及康復,人早就死了。換句話說,她極力反對中醫的醫學傳統,而擁護西醫科學的現代性。」
「原來如此。不過,中西醫並行也是一種方法吧。」
「她才不理會這個說法。老弟,你好像沒完全聽懂我的話呢,我的意思是,在我太太的絕對觀念裡,我可以不喜歡西醫的治療方法,就是不准去找中醫師,不管他們是有執照的,公認的現代華陀,或者故弄玄虛的冒牌貨,統統不得越過她劃下的這條紅線。」
「問題是,您又不能替自己看病?」
「為什麼不行?誰規定不能自我診療?」
「可是……」
「事情遇到困難,就要想辦方解決,不是嗎?我問你,你既然是個作家,應該知道臺北的重慶南路書店街吧?」
「當然知道。」
說到書店的事情,這屬於史高治的管轄範圍,他跑過臺灣全國的書店,不在這方面展現,等於砸毀自己的招牌。他用充滿自信的語氣說:
「您是指哪家書店?說不定我還認識書店的老闆呢。」
查利提臉上浮現了笑容,為他創造的話題終於得到延續而感到欣慰。
「真的?這麼說,你應該知道『萬善堂書局』吧?」
「萬善堂書局?」史高治歡快的笑容,像受凍的鬱金香突然僵住了。他立刻在腦海裡搜尋,重慶南路附近有這一家書局嗎?他心想,不可能的,這家書店根本不存在,他對於那一帶的環境,比任何人都要熟悉,每條巷弄的樣子,他記得非常清楚。
「董事長,您會不會是記錯店名了?在我的印象中,應該沒有這家書店,而且還叫做萬善堂的。」
「怎麼了?叫做『萬善堂』有什麼不對嗎?俗話說,『百事善為先』,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怎麼經由你的轉述,『萬善堂』這三個字的形象,一下子變得俗氣了。老弟啊,你好像有語言歧視的傾向喔。」
「不,董事長,您誤會了。」史高治禁不住正面攻擊,尤其是來自贊助商高位的批評,這讓他更顯得焦灼起來,講話開始結結巴巴,失去他在各地演講時的那種從容態度。「我的意思是,在那條書街上,我記得有精英堂書店、萬保龍書局、香奈爾書坊、香蕉共和國、尼采之家,好像沒有叫做『萬善堂書局』的。您要不要拿出發票確認一下?」
「不需要。正如剛才我告訴你的,我的肺部因坐牢的關係,被搞得七葷八素,但是我的記憶力還行,不至於失智的地步。」說著,查利提向史高治招招手說:「來,你看一下,這是我在萬善堂買來的寶物。」
升起獨立的旗幟
史高治遵從查利提的指示,起身來到辦公桌前,態度像是刑事警察局鑑識小組的成員。他睜大眼睛察看眼前的光景:一本人體穴位圖書和一盒針炙針。這就是查利提所說的寶物。
「董事長,您該不會是一邊看這圖示,一邊替自己扎針吧?」
「嘿,這回你終於說對了。來,我馬上扎個十來針,讓你見識一下。」
「不要啦,這樣很危險吧?」
「不,哪有什麼危險。你沒來之前,我已經自行扎過五百多針了,這只是雕蟲小技,不必緊張。」
沒等史高治完全會意過來,查利提動作麻利打開針灸針盒,從盒內取出一支針,往自己左手的穴位上扎下去,然後一支接著一支,彷彿把一支尖針插在針線包上那樣簡單,一點也沒有顯示可怕的痛感。
「我告訴你,扎針很有功效。我靠它和適當運動總算挽住肺部疾患沒惡化下去。儘管如此,現在我仍然在探究行針的基本手法。而且我相信,經過不斷的摸索練習,將來一定會越加熟練。」
經由查利提的說明,史高治終於明白這一事實:董事長剛才向他展示手掌臂上的針痕、斑點是怎麼回事了。
「將來你有需要的話,可以到『萬善堂書局』看看,那裡什麼樣東西都有,五術、算命書、卜卦、風水陽宅、毛筆硯台、刮刮樂等等,可說一應俱全。不過,購買針灸針可得謹慎了。」
「為什麼?」
「你不知道嗎?現在,臺灣各大市場上到處充斥中國貨,簡體版書籍倒無所謂,反正那種東西不咬人,想看就買不讀也無所謂。針炙針就不同了,它是侵入性的東西,萬一它是重複使用的再製品,扎下去被壞東西感染的話,我這條老命就不保了。雖然我不怕死,活著不是為做偉大的事。但是對於別人的困難,我多少還能派上用場。再說,我太太堅決反對我去看中醫,的確使我不知所措,我始終相信她的真情,只是表達方式不同而已。」
「我相信,董事長夫婦的家庭生活,必定是相當美滿。」史高治停頓了一下,接著說道:「您是成功的企業家,家庭事業兩得意的背後,賢內助功不可沒,值得我們年輕作家效法。」
「哎呀,老弟過獎了。每個家庭都有各自的問題,解決得宜就是美滿,處理得不好,就被推向失敗的終點。話說回來,你單身沒結婚,還不了解夫婦到了老年,所謂感情『昇華』的事。這對於男人來說,也是一種重要的儀式。」
查利提說到這裡,故意賣個關子,不往下說了,因為有些事情沒有事實和經驗做支撐,任憑你運用美麗的詞語,依然無法把描寫得詳盡。在查利提看來,這個概念同樣適用於作家的創作。他回想起多年前與伊謨尼斯基的一次對談。伊謨尼斯基是個詩人,對於看待事物和思考,自然是與眾不同。那次,他來辦公室拜訪查利提,題贈他新近出版的詩集,以回報董事長的贊助情誼。伊謨尼斯基說,只談深奧的文學理論,沒有實際的文字操練,很容易掉入眼高手低的幻境,慢慢將自己變成孤芳自賞、悲憤成性的邊緣人。最明顯的症狀是,他們看到別人發表文章的時候,就會無原由地怒火攻心,強烈地否定別人的作品,批評別人只是在製造無用的文字。查利提說,他不懂得寫作這種行當的深奧功夫,但是他從企業經營者的角度來看,認同和欣賞詩人這種實證主義的說法,或許正因為這樣,他們每次總是相談甚歡,每次的話題都能引出嶄新的思想。就在查利提這樣稍做沉思的空檔,彷彿算準時間似的巧合,門外傳來了敲門聲:
「董事長,我送咖啡來了!」(未完待續)
作者邱振瑞簡介: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我的書鄉神保町》1-10卷(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