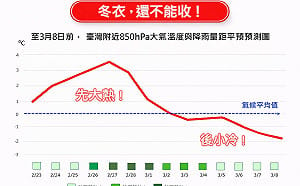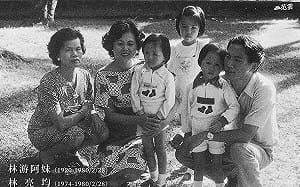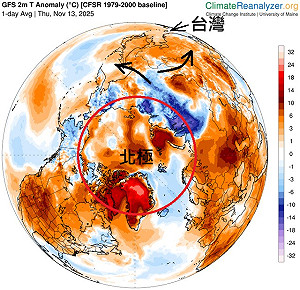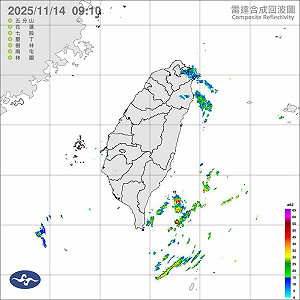當中國重慶公安局以「分裂國家罪」對沈伯洋立案時,他既未犯罪,未踏足重慶,甚至從未進入中國一步。這不是審判,而是一場充滿政治算計的荒謬戲碼——而這場戲,早在卡夫卡的小說《審判》中,便已有完整劇本。
《審判》的故事極其簡單:某個早晨,K.醒來,突然被告知「遭到逮捕」。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也從未見到法官,更永遠等不到判決。審判不再是可終結的程序,而是一種無盡的狀態;法庭不是建築,而是迷宮;法律不是制度,而是籠罩日常生活的陰影。
現正最夯:趙少康嗆「誰敢通過就告誰」汪浩轟:居心叵測!籲立院盡速通過台美關稅協議
如今,在21世紀的亞洲,一個威權政權正將這場文學寓言化為現實操作。卡夫卡式控訴,如今不再只是文學象徵,而是威權輸出司法控制的技術化工具;不再是小說,而是國家政策的一環。
一、不是你做了什麼,而是你是誰
在中國的政治邏輯裡,罪名不再根植於行為,而是繫於身分。你不需要違法,只要是台灣立法委員,只要在國際場域堅持台灣主體性,就足以構成「分裂」。
現正最夯:缺大咖!鄭麗文任主席首次新春團拜 前主席僅吳伯雄到場
沈伯洋的「罪行」不在於他做了什麼,而在於他代表了什麼。他的國會身分、在國際場合的發言、對民主制度的堅持,成為中共定義「犯罪」的依據。在這樣一個將政治意識形態凌駕法律標準的體制中,「分裂」不再是一項可具體說明的法律行為,而是一句可以任意套用的政治咒語。
只要不說北京想聽的話,你就是「分裂份子」;只要堅持不同的敘事,你就是「犯罪嫌疑人」。
二、法庭無所不在,重慶也好,泉州也罷
中共選擇重慶公安局作為對沈伯洋立案的單位,看似荒謬,實則用意明確。在這種體制下,「審判地點」不再與法律管轄有關,而是一種政治訊號的傳遞。重慶並非對台前線,也與沈毫無交集,卻成為主審機關——正因為如此,它更能表明:審判可以從天而降,無所不在。
訊息非常清楚: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的公安局,都可以成為你的法庭。
泉州公安局對台灣網紅八炯、閩南狼發出的懸賞同樣如此。他們不曾在泉州從事任何行為,但泉州需要一場審判——這就是重點。
在卡夫卡筆下,法庭無處不在;而在現實中,中共告訴你:只要我願意,哪裡都能審你。
三、程序不重要,聲明、影片與懸賞即可定罪
在卡夫卡的世界裡,法庭反覆召喚K.,卻從不給他辯護機會;而在中共的版本裡,連這層形式都可被省略——央視一段八分鐘的「專家解說」,就足以取代整場審判。
只要有主播念出台詞,只要有推播、懸賞、剪接畫面,司法就可宣告成立。
不需要證據、不需要審理、更不需要國際認同——只需一段能循環播放的敘事,一句聳動的話語,就能讓「分裂罪」成立;一張懸賞海報,就能壓過整本法律教科書。
這是一場「影像即判決」、「話語即權力」的新型審判。法官變成主播,證據變成剪輯,判決變成點閱。
四、目的不是抓人,而是抓住你的恐懼
中共非常清楚,它無法真正逮捕沈伯洋,也無法讓國際刑警為其效命。但重點從來不在「抓得到」,而在於能不能讓你「覺得自己會被抓」。
真正的目的是製造寒蟬效應——讓所有台灣政治人物、國際倡議者、青年官員,心中都浮現這樣的疑問:
「我會不會也成為下一個被立案、被懸賞的對象?」
「我出訪的國家會不會因為中共壓力對我設限?」
這不是軍機繞台那種可見的硬威脅,而是一種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心理滲透。它的目的,是讓人們在行動之前就先退縮,先懷疑,再自我審查。
它要讓外交變得更昂貴,讓民主發聲變得更困難。這就是用「司法恐懼」取代「軍事恐嚇」的灰色作戰,更精緻、更陰險。
卡夫卡的恐怖,在於「你不知道暴力何時會來」;而中共的跨境審判,在於「你知道它不會來,但你依然必須害怕」。
這,就是心理戰的最高境界。
五、審判的終點不是人,而是真相
《審判》的結局,是K.被帶往郊外處決。他不是因為犯罪而死,而是因為無法證明自己無罪。在一個荒謬體制裡,無罪本身就是罪。
今天,沈伯洋、八炯、閩南狼等人所面對的,不只是個人追殺,而是整體制度的崩解。被「處決」的,不是人,而是:主權的概念、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公法理性與程序正義、台灣政治人物的行動自由、以及最重要的:真相本身。
因為在中共體系中,真相不是經由證據而產生,而是由權力來宣布。
卡夫卡式的荒謬正全面回返,只不過,它不再是小說,而是政權的策略;不再是文學的警示,而是亞洲的現實。
結語:真正被審判的,是我們自己
卡夫卡令人戰慄之處,在於讓讀者明白:在荒謬體制裡,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告。
今天,中共對台灣政治人物的跨境起訴,不只是針對個人的迫害,而是對民主制度本身的壓力測試;不只是法律操作,而是話語控制;不只是審判沈伯洋,而是審判我們所有人對荒謬的反應能力。
面對荒謬,我們可以選擇像K.一樣沉默退場;也可以選擇,在審判劇場燈光亮起時,勇敢站上舞台,指出——「這不是審判,這是荒謬。」。
唯有識破荒謬,我們才不會成為下一個被推入迷宮的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