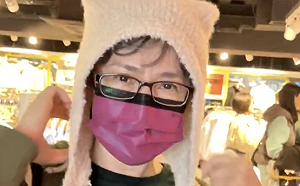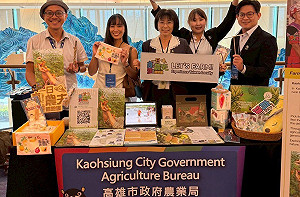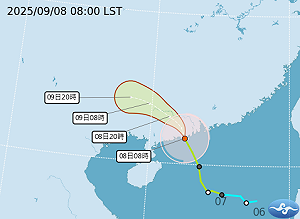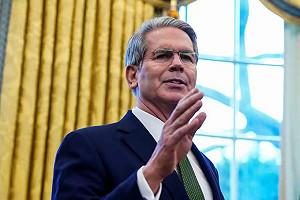中國「九三閱兵」的鎂光燈下,習近平再次向世界展示軍備與大國敘事。然而,舞台之外的言論衝上頭條消息引發廣泛討論:湖北襄陽一名網民因在微信發表對閱兵的「誣衊、詆毀性不當言論」被行政拘留;更有網傳案例稱,一名網民在群組質疑「啥年代了,還在搞這些XX玩意兒」後,短短三小時即被抓捕,最終遭十日拘留。官方未披露具體言詞,這種「有罪名、無細節」的禁評方式,讓人不得不追問:在重大政治事件期間,公民到底能說什麼?又有哪些話,說不得?
模糊的邊界:一種可擴展的沉默
現正最夯:2,000萬大獎已刮出兩張!2026金馬年刮刮樂攻略 拚頭獎選哪張? 賺錢率最高的是誰?
以「誣衊、詆毀」為名的處罰,若沒有清晰、可核查的判定標準,就很容易變成可自由伸縮的管理網。今天可以捕捉粗鄙罵語,明天也可能超收理性質疑;今天處理的是煽動性謠言,明天也可能涵蓋對政策象徵的價值辯論。當「界線」從法條走向「語感」,從程序走向「政治氣候」,中國人民對於「何為可言」的預期就會崩解,轉而以自我審查保身。久而久之,公共討論場域會被消音,留下的只剩掌聲與沉默,而沉默未必等於共識,等於民族自信心。
這種模糊性在本案中尤為突出,網警公告點名「不當言論」,卻不提供例句、情境或判準。輿論場上出現的不是針對內容的理性批駁,而是對程序的本能不安。一些網民的直覺反應是:「問題不是他說了什麼,而是這個時候什麼都不要說。」當公民學會對「時間點」比對「內容」更敏感,公共討論便迅速從「是非辨析」滑向「風險管理」,這樣的情境卻成為館長之流的崇拜。
「正能量」的悖論:鼓勵評論,但只要正面
當前熱搜:美揭露解放軍核試 華時:中國擔心「午夜之鎚」砸在自己頭上
任何社會都需避免仇恨言論與惡意造謠,但是中共官方長期倡議「建設性評論」與「正能量」的口是心非。然而,當「鼓勵評論」與「只要正面」被同時放在一段話裡,悖論便生成了。因為評論的價值,恰恰在於能指出缺陷、提出疑問、挑戰共識。去除負面,即等於剝奪評論的尖銳性與公共監督力。閱兵是中共的國家象徵,對其資源配置、政治意涵和時代意義的質疑,本應納入公共辯論的視野。
然而,舉報是紅衛兵的鬥爭傳統,公開「錯誤言論」可以擴散負面情緒。但另一個現實是:當細節被遮蔽,陰影便放大。一位網民的訴求直截了當:「把錯誤言論發出來,讓人民批批他不好嗎?」如果對自身叙事的自信建立在不讓公眾看到對立文本之上,這種信心其實相當脆弱。真理若能越辯越明,何妨讓民眾看見「不當」之所以不當?
程序正義與可預期性
任何限制性規範,都需要三樣東西:清楚的定義、穩定的程序、可達到的救濟,缺一不可。清楚的定義能降低執法的任意空間;穩定的程序能讓個案在不同時間、不同地區仍有一致的對待;可達到的救濟(申訴、復議、司法審查)則是保障權利的最後一道關口。當前問題不是是否可以管理言論,而是如何管理得「可被檢驗」。在本案中,如果官方能公開範例、提供裁量要素(如是否虛構事實、是否有明確指向的侮辱、是否造成實際危害),再附上處分依據與申訴途徑,公眾或不至於將想像填滿空白。
諷刺的是,當處置邏輯被包裹成「不可說的機密」,則短期或許能壓低噪音,長期卻會侵蝕公信力。公信力的喪失,一旦轉化為對制度的「預設不信任」,治理成本只會節節攀升。
風險與責任:從「如何說」到「不說」
對閱兵的質疑,完全可以討論其成本—效益、外交傳訊、對內凝聚與對外嚇阻的差異,以及在經濟壓力時期象徵政治的優先級,這些都屬「公共利益問題」,理應被允許也被鼓勵。換言之,治理者有義務提供表達的護欄與指南;公民則需在護欄內提升論述品質。當雙方都只強化單邊義務——政府只談秩序、個人只談自由——結果往往是對撞,而非共構。
中國語境中,若「敏感期治理」逐漸常態化,且標準滯留在「彈性模糊」而非「可驗明」,那麼外部對內部敘事的疑慮便容易累積,形成信任赤字。這些做法不會讓所有分歧消失,但能把分歧從陰影帶到光下,將「臆測的不安」轉化為「制度的可預期」。
眾所周知,閱兵展示的是硬實力,而一個社會最持久的軟實力,來自面對質疑的自信。當公共權力選擇以沉默回應「他到底說了什麼」的追問,便是在要求公民用信仰取代證據、用服從取代辯論。短期看,這或許收穫了整齊劃一的輿情;長期看,它削弱了制度的韌性。真正堅固的體制,不怕被提問,也不怕被看見程序如何運作。沉默的疊加讓閱兵壯觀,卻無法讓公民壯膽,壯的是以事實說理、以規範保護分歧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