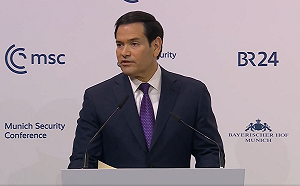依據我財政部初估決算,去(2024)年全國稅課收入3兆7,619億元,較預算數多出5,283億元,產生金額龐大的「稅收超徵」。若根據我國《預算法》第59條規定:「超收應一律解庫,不得逕行坐抵或挪移墊用。」也就是說「超收額」本質上應留於國庫。而根據《公共債務法》第12條第2項指出,若歲入超過原訂預算數,應優先用於償還公債,減少舉債需求。因此從法規層面的意義上來說,「稅收超徵」的運作首選並非是用在「還稅於民」。
另從在外環境來看,今年1月20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上台,短短三個多月,美國領導的世界已然呈現一團混亂。而我國不論是直接應對川普要求「臺灣製造業流向美國」或「被美國課予重關稅」,又或者要求我國「增加對美軍事採購」等,政府可能都會需要一筆臨時的應急資金,而去年的「稅收超徵」,剛好可以在不加稅、不額外發公債的前提下,提供紓困基金的來源,可以說是在變動最小的狀況下,得到因應外在環境劇變的準備金。
現正最夯:國民黨失美信任!劉寶傑轟「自業自得」蕭旭岑氣嗆:隨便你怎麼說
從國內民防體系來看,我國於1991年5月1日正式終止「動員戡亂時期」。雖然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對於台灣在1990年代後續的民主化進程,產生十分正向的助益,不過原《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搭配1950年代以來的《戒嚴令》,對中共產生一套嚴密的「防叛亂、防滲透」系統,也隨著「動員戡亂」的結束而走向衰弱。儘管臺灣仍遺留下《民防法》及其規範的民防架構,但在缺乏資源與演練下,漸成空殼,已難在臺灣發生特別危難時發揮作用。
隨著烏俄戰爭爆發「全社會防衛韌性」(Whole-of-Society Defense Resilience)的概念,再度興起,已於芬蘭、瑞典、烏克蘭等國獲得重視,尤其在面對現代「混合威脅」(hybrid threats)像是資訊戰、經濟戰、網路攻擊甚至全面軍事侵略時,顯得尤為重要。對臺灣來說,我們很難得有資源可以挹注於此,但這塊卻是臺灣廢弛已久的安全缺口,倘能將「稅收超徵」留於國庫,再透過立法機制,將其部分活用於「民防體系」建構,那麼除了能讓臺灣民防體系更加活絡外,在未來不論是應對中共的安全挑戰,或者隨著氣候變遷產生的非傳統威安全威脅,臺灣均有更強的本錢進行動員回應,也就增加了臺灣的安全係數。
總體來說,去年出現的「稅收超徵」,依法應優先留存國庫,而非直接「還稅於民」。在當前國際局勢動盪、美國要求台灣承擔更多經濟與軍事責任之下,「稅收超徵」可作為重要應急資金來源。面對台灣民防體系因資源不足而弱化問題,若能透過立法,將部分超徵稅收挹注民防建設,將有助於強化「全社會防衛韌性」,提升台灣因應傳統與非傳統威脅的整體防衛能力,長遠來說,對臺灣並非壞事。
全站首選:點名國民黨和民眾黨太親中!美智庫高層籲取消藍白政客及家屬美簽
作者: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馬準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