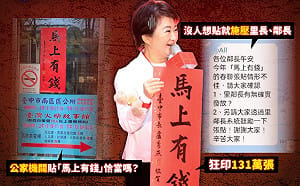《馮光遠(儘量)回憶錄》連載第一篇,七零年代的台北文青必服的藝術電影,以及只有巷仔內知道的「台映放映室」,以及在台映喀嚓聲中做的文青夢。
有回,與一位文藝青年聊天,一個不折不扣的文青,深諳藝文大小事,年紀也輕。聊著聊著,聊到電影,問他,「對費里尼可熟悉?」,他說「不熟!」但是立刻補上一句,回家會立刻上網做功課。
電影要站著看─國歌片頭
是的,上網,光是這個動作,現在的文青,就要比我們那個年代的文青幸運太多了,似乎一切問題,上網即可解決。以前憧憬當文青,除了興趣、天分、努力,其實機緣也挺重要,可是當年的環境,資源受限,以致於太多時候,任何一個立志當文青之人,都不是那麼容易圓其文青夢。
全站首選:台中超印14萬張春聯發不完 民進黨:盧秀燕把里長當行銷欺人太甚
上世紀七零年代,是我的文青養成年代,然而,光是看電影這檔事,其困難的程度,就絕非現在的文青所能體會,當然,我講的電影,指的是「藝術電影」。
至於商業片,那個年代,你想看三廳、武俠或軍教片,隨時走進一間戲院,看完國歌片頭(這一段要站著看),就著零嘴,我保證你看到飽。

文青電影的成色:催睡、傷腦、話題足
可是,如果想看的是藝術電影,那你就得耳聰目明,知道哪部片子的文青成色夠(意思是:夠催睡、夠傷腦、話題足),除此之外,更得搶在下片之前就將其解決,因為,文青追看的電影,通常也是下片最快的一種。
全站首選:曾霸氣護女!前主播吳中純淋巴癌逝享年56歲 老公悲痛發文:淚乾心碎
在這種大環境之下,當年要擠進文青行列,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得搭上各校「電影社」之類社團的列車,接受最新藝術電影的洗禮,結識來自各校的影癡,那是一種七零年代的「上網」。
一旦你被系統接納了,立刻,文青的日子宛如任督二脈打通:你將會被通知,何時可以去哪裏看法國新浪潮或義大利新寫實;你也會被轉告,在哪裡有新進口的日本電影將做地下放映,這是不容易的,因為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日本電影已成禁片;你更會被邀請,何時有電影討論、演講,老天鵝,這種機會根本就是文青大補丸,服下,整年受用。

神秘「台映試片室」
「台映試片室」,就是當時一個奇妙的產出,一個會讓今日文青嘖嘖稱奇的場域,因為那種「上網」,你可以感受體熱,你可以激動辯論,你竟然也可以索取到電話號碼。
當然,你更可以在按下記憶鍵之後,像我現在一樣,瞬間重新回當年的觀影時空。在放映室,保證隨時會有事件發生,這跟你坐在電腦或電視前面看 Netflix,是截然不同的觀影經驗。
─
那你可能好奇,「台映」,到底是怎麼樣子的一個單位。
是的,稱之為單位,好似它是一個秘密組織什麼的,不過,在當時,這個放映室,還真的挺神秘,因為它既不是電影院,也不是社團,可是,你就是可以在這裡,與同好齊聚一堂,看一部彼此都心馳神往的電影。
一般所謂試片室,打從我知道這種地方的存在開始,其功能、運作、形式,就八九不離十,都是一個樣:大約都座落在市中心某棟樓裡,容量則約莫四、五十個座位,或更少,銀幕雖小,但階梯式的座位安排,總也讓各個觀眾都看得舒服。
也許你會問,幹嘛去這種地方看電影,電影院不總是正常存在?再不濟事,也有二輪戲院啊!
頭皮到頭腦 那個國家什麼都要介入的年代
的確,七零年代,當然有一堆運作正常的電影院,也有一堆如今已愈發稀少的二輪電影院,可是,不要忘了,七零年代,警總還在,行政院新聞局還在,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神聖使命還在,每天在路上追著長髮男子立志要讓他們儀容端正的警察也還在。
我提這些,就是想告訴現在的年輕人,當年,看電影的選擇其實挺有限,不像今天想看什麼就看什麼。想想,連頭皮上面的頭髮長短,國家都要介入,那個年代,頭皮下面的腦波運作自由,如果國家機器不插一腳,豈不有虧職守?
這,就是台映試片室以及類似場域在那個年代崛起的背後脈絡。至於其運作的方式,也很簡單,試片室,其正常功能,以前、現在都一樣,就是放映還沒有在院線上演的電影給影評人或片商之類的觀眾看,所以幾乎都是一次性的放映。除了片商,去試片室觀影的人並不多,主要都是各媒體的電影線記者或者專業影評人。
後來,隨著各大專院校電影社團的成立,這些試片室,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竟然成為學校電影社團之外,另一股「校園在野觀影勢力」,也就是說,如果你對校園裡救國團式看電影活動沒有興趣(其實是不屑啦),去試片室看電影,就是另外一種選擇。
至於是哪些天才文青創出這種觀影模式,已不可考,不過,對影癡文青而言, 試片室文化的出現,絕對是八零年代台灣新電影人才輩出的一個濫觴,因為太多後來跟台灣電影有關的電影人,那個時候都是試片室的常客。

放映室運作:認識老闆、糾眾、決定看什麼、賣票
這裡,就先來解釋一下放映室的運作模式。
其流程約略如下:
一。先跟放映室老闆認識,我最先認識的,就是台映的老闆,林先生。認識林先生,意味著在台北這個放映室觀影系統裡,我已被列入「關係人名單」,此時,要認識其他放映室老闆,就容易多了;這道理,跟匪諜系統差不多,認識了匪諜甲,之後要認識匪諜乙或者丙、丁,就不難了。
二。詢問老闆現下他手裡有哪些片子能夠拿出來放,以便糾眾。這又要說明一下,當年,放映室不會大辣辣地放映正在院線上演、或者即將做商業映演的電影,放映室放的,多是一些可以從片商那裡調借的舊片拷貝(主要為藝術電影),而這些由舊片組成的片單,則是由不同的觀影社團,與放映室經由長時間互動之後而逐漸成型的。
三。一旦決定了放映的片子與時間,就要開始動員了,否則,九百元一場的場租、放映費,如有虧空,就得自己補貼。我大學打過很多種工,不過在放映室辦電影欣賞,則是最有趣的一個,不但看了想看的電影,還有錢賺,五十塊錢一張票,只要找到十八位觀眾,就至少不賠錢。
認識鄭在東 放自己想看的影片
七零年代中,大三的時候,我開始在台映辦起電影欣賞,與其說為何突然文青上身,不如說,我對賺零用錢更有興趣。
會辦電影欣賞,另一個原因是,我認識了鄭在東。
在東是我學弟葉光麟的舅舅,有一天,光麟與我在文友樓走廊聊天,他突然提了個主意,說,我應該要去認識他的舅舅鄭在東,至於理由,我現在哪裏記得起來?
總之,台映已有的放電影團隊,就因此又多了一個輔大/世新的奇怪搭檔,我所謂奇怪,因為其他幾個組合,多是同一學校或系所的同學,如淡江建築系的林洲民、吳永毅、李瑋珉,如台大視聽社的幾位同學。在東跟我的冒出,著實有點不搭,另外,還有一個不搭就是,我們的選片,比較不那麼藝術取向,我跟在東放電影,多放一些自己想看的片子。
其實,那時台映最受歡迎的,主要還是藝術電影,柏格曼、費里尼、安東尼奧尼、狄西嘉等導演的片子是為基本款,台北文青那麼多,就算每個週末透過不 同的觀影團隊放個幾部,文青還是喊餓。不過,我與在東對藝術電影就是不那麼買帳,我們比較喜歡看我們覺得「好看」的電影。
例如我對喜劇就很偏愛,所以我寧願選 Mel Brooks、Woody Allen,也勝過選柏格曼。另外,我更常洽談租一些日本電影來放(前面提過,當年日片為禁片),因為放日片,可以找日語系的同學看電影練日文,也可以問同學,家裡可有曾受日本教育的長輩,想看日片懷舊。用這些概念攬客,對我這種腦筋動得快的人而言,一塊蛋糕。

台映喀嚓聲中的白目文青夢
幾個月前,跟鄭在東約了在東區喝酒,在東從上世紀九零年代,就一直定居上海,這些年,台灣、中國兩頭跑,是個成功的藝術家。聊著聊著,他突然很感慨,「敬 1986 年一杯,那個美好的年代。」我們大口把酒灌下。
在東講的那一年,我拿到美國綠卡,也幸運地幫在東於紐約的格林威治村(東村)一畫廊,辦了他在國外的第一個展覽。可是前面提到的那晚,當威士忌下肚,我腦子裡翻轉的,卻是七零年代我們在台映辦電影欣賞的畫面,兩個對藝術懵懵懂懂的外省背景台灣年輕人,多年之後,分別從不同的文化關懷,逐漸完成了各自的文青夢。
台映對我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認識了鄭在東這位一輩子的朋友,其實後來許多出現在我人生裡的人物,他們在七零年代的某些日子裡,竟然也都曾經跟我於台映有過交集,各自受到台映觀影文化的影響、且回想起來感慨萬千。
凝視著多部台灣不易看到的外國藝術或社會批判電影,我們擠在小小的放映室,有時甚至聽得到背後放映室,電影放映機上賽璐璐片在片槽裡轉空、換另一部放映機接續投放時的咔嚓聲音;有時,冷氣不夠冷,也沒有人在意,大家就那麼專心地、飢渴地,各自吸收著設定要追求的養分,當然,我跟在東,大多數時候,也追求到我們設定的打工利潤。
好友與妻子都在台映認識
那種緣分是挺奇妙的,比方說,我在台映認識了我後來經過許多曲折而結婚的妻子,雖然最終,這婚姻還是一個文青之間無法終老的愛情故事,但是我收穫了一個跟我一樣、某種程度上可謂有點秀斗的女兒,我把這幸福,歸功於台映。
又如,我後來的幾位工作伙伴、以及幾位一輩子的朋友,如林洲民、李安、舒國治、韓良露、李幼新(即永遠有著一頭長髮的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劉森堯等,不論他們最後是不是走電影這一行,因為都曾經是台映的常客,甚至活動的主辦者,我們竟然就因著這看電影的緣分,各自在往後的日子裡,善用曾經在那個小小空間裡吸收到的養分,我們甚至因此合作,不論是電影,還是其他文化案子,大家都沒有枉費曾有的文青熱情。
因為台映,當初在放映室裡我們各自許下的卑微志願,多年之後,我們分頭在台灣不同的文化工程上,各自發揮自己的所學,且得以實踐那些卑微的志願。
你看費里尼?你也在現場?
進入二十一世紀,文青與觀影之間的鴻溝,早就沒有那麼多曲折可以敘述,文青當然依舊永遠忙碌,可是邁往文青之路,感謝科青(科技青年)的努力,也早已不再曲折,台映這種場所,早就成天方夜譚了。如今談台映的人,頭髮大多蒼白,視力早已老花,可是不要小看這些人,丟出台映話題,大家眼睛一亮,立即神彩飛揚。
幾年前,與新新聞、中國時報老長官王健壯聊天,談到台映,上面提到的精神狀態立刻出現,兩人不僅立刻進入時光隧道,且各自任意變換車道好不愜意(駕駛切勿學習)。
最好笑的一段話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在那裡看過費里尼的《羅馬風情畫》?」
「看過啊,除了台映,還有哪裏可以看到《羅馬風情畫》?」
「我也是在那裡看的,我記得,看到一半的時候,林先生突然把片子切斷,然後從放映室出來跟大家道歉,因為他把其中一盤膠捲搞錯了,次序顛倒,所以那一段要重放。」
「什麼,你也看了那一場?」
「怎麼了,難道那一場你也在?」
「對啊,我印象很深。」
「我也是,幾十個人面面相覷,因為沒有人知道電影放錯次序了。」
「還好是費里尼的電影,所以放顛倒了也沒有人在乎。」
「不是不在乎,是看不懂。」
「也是。」
「原來你也在現場。」
「這事我哪天一定要講出來。」
「七零年代台灣文青,看費里尼,厲害啊!」
好了,關於台映的回憶,我盡量了,就此打住。

關於【馮光遠(儘量)回憶錄】
「馮哥(我們都這麼叫馮光遠),你有講不完的故事,寫個回憶錄吧?!」
他半開玩笑又不失真實地說道:「寫回憶錄的人,多少有些自戀耶」
看來他拒絕。
「回憶應該是紀實,寫得開心,不小心就虛構起來了。」他繼續說道。
「沒關係,寫多少是多少,太…真實,大家壓力也大。」我們小心地應著。
「好,那我就儘量囉!」馮哥啜飲著泥煤威士忌,邊回答。
《馮光遠(儘量)回憶錄》企劃於焉形成。
這是兩年前的事。
不過,認識馮哥都知道,他已經很「儘量」了。
作者:馮光遠,曾任記者、作家、編劇、攝影、劇場工作者及政治人物,《中國時報》主筆、副總編輯。馮也是《給我報報》、憲政公民團創辦人,也曾受聘金石堂書店擔任行銷創意總監,主持電視評論節目及發表幽默與政治諷刺文章。作品《囍宴》獲金馬獎最佳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