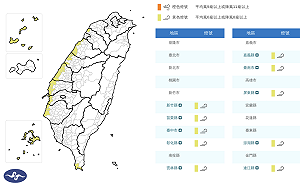因為疫情的關係,一位過去長期待在中國,原本是台商、後來變台幹、現在是台流的老同學,今年起既不能回中國,留在台灣也鬱悶,就約了本魯一人來聊聊。
他在學生時代就是個口才好、功課棒、有領導能力,對人也超熱情、常被老師選為班長的眷村子弟。本來在他每年農曆年回台時,都約老同學們聚在一起,但今年他留在台灣的時間長了,就改成一個一個約了聊。終究是多年同學,我們見面沒多久就聊開了,他帶著些微抱怨的語氣說:
當前熱搜:高階警官人事發布爭議 警政署:均依規辦理
「以前不覺得民進黨的去中國化很可怕,但最近我發現台灣人都變了。以前我從大陸回來,說現在大陸很進步,早就超過台灣,很快又會超過美國了,大家都沒意見。但現在還說沒兩句,立刻有人打斷我的話,連我說『我們中國人』怎樣怎樣,都有人當場頂撞說『我是台灣人』,可是我也是台灣人啊!『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我這樣說了一輩子都沒問題,為什麼今年有這麼多老同學,當場就給我難堪,台灣人怎麼都變了?」
本魯也是笑笑的回他:「綠皮藍骨的民進黨沒這麼厲害,否則政黨輪替2次了,蔡英文也都連任了,怎麼會現在才開始變?不是他們台灣人變了,是全世界都變了。現在到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你講『我們中國人』或『中國好棒棒』,人家對你的態度,可能比那些老同學更激烈。」
「但他們從前不會這樣啊?」
「唉!我們四、五年級生的本省人同學,大多來自農工商家庭,戒嚴時代父母長輩給他們的教導,就是『民不與官鬥』,他們從小就不會當面跟我們這些說『官話』的外省人『亂說話』,但不代表他們就認同我們所說的。我們到了這年紀,早該看清楚了才是啊!」
聊著聊著又聊到了龍應台的「反戰論」,他就很不解,《野火集》時,龍應台說「我們一千八百萬中國人為何不生氣?」也沒有看到什麼台灣人因為被稱為「中國人」而生氣。《大江大海》時,龍應台說「台灣這幾年的藍綠對立,其實跟看不見彼此的傷口有關。」這一點難道管大也認為她錯了嗎?本魯還是心平氣和的回他:
「從戒嚴時代迄今,外省人擁有政治及語言上的強勢,始終掌握著話語權,我們的聲音絕對是媒體上的主流聲音,台灣人不會不了解我們上一代離鄉背井與國破家亡的悲憤。因此外省人要說自己的眷村生活有多苦,童年遭遇有多辛酸,都不會有本省人反駁。可是龍應台大可不必把她完全不懂的本省籍女工同學拿來做對比,那就踩到了台灣人的集體傷痛。踩到一隻貓的尾巴,都可能被抓被咬,何況現在是一次踩一群貓的尾巴?」
兩起「以死明志」的自殺案
2007年4月14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龍應台的〈在仰德大道上〉上這樣寫著:
「於是YP和我都考上了不錯的大學,都申請到美國留學,雖然她和我都來自艱困的難民家庭,雖然她和我都是女孩。
本省的女孩……中學的同學們,很容易就被送到工廠去作女工了,賺到的錢,可以補貼家用,也可以買來黃金鐲子一圈一圈套在手臂上,累積將來的體面嫁妝。……
而一無所有的我們,因為被拋離了土地,拋離了附著於土地的傳統網絡,我們遂和男孩子們一樣讀書,一樣考試,一樣留學,甚至和男孩子一樣被期待去贏得美國的碩士或博士學位。……」
龍應台的這段話,赤裸裸的展現高級外省人以統治階級發言的傲慢。還好這句「本省的女孩」是出自龍應台原文,否則那些黨國餘孽與兩蔣鷹犬,為了鞏固既得利益,合理化自己世襲而來的特權,一定會痛罵早就認清真相又吃了誠實豆沙包的管大,總是在「製造仇恨與分裂族群」吧?
1975年8月,我在東園街的印刷廠當暑期摺紙童工,現在青年公園那裡的淡水河邊,浮起了一具國中女生的遺體,大家都騎腳踏車或跑步去現場。原來是住在中和鄉的洪X葉,前一天下午從中正橋跳水自殺,守橋的憲兵攔阻不及,隨後大批警消撈了一個晚上也無果,直到次日遺體才在台北市這一邊浮出。
洪X葉家境貧困,但她功課很好,老師替她交了報名費參加北聯(聯考),報上說她考上了北一女,但父母還是反對她升學,要送她去工廠當女工。洪X葉與老師向家長多次懇求,父母還是拒絕,於是洪X葉上午跳淡水河自殺,被岸邊的釣客跳入水中救起,送到派出所通知父母領回。但父母要送洪X葉去當女工的心意已決,洪X葉也死意甚堅,於是下午又到中正橋中央跳下,大批軍警消動員仍無法搶救。
不只是女工想升學,甚至以死明志,1964年9月發生在高雄市華國旅社的嘉義中學郭X良服毒案,讓人看了更鼻酸。嘉義市魚販郭X順夫婦,因婚後多年仍膝下無子,就收養了鄰居的男孩取名郭X良。之後郭X順的妻子雖然順利懷孕,但一連三胎都是弄瓦,因此郭X順夫婦仍將這養子視如己出。
郭X良從小就乖巧用功,但或許受限於資質,上了嘉義中學後,學業就跟不上同學,以致被留級,之後又休學一年,再重回高二就讀時已20歲了。她的大妹考上嘉義女中,重男輕女的父母,竟然不讓親生女兒註冊入學,堅持送她去洋裁店當學徒。
郭X良看到比他會讀書的妹妹,因為自己的魯鈍,被親生父母逼得失學,羞慚下竟跑去高雄市華國旅社,先服安眠藥自殺,不料劑量不夠,睡了一天一夜後又醒來。於是又寫了另一封遺書明志,再次喝下農藥,旅社服務生發現時,郭X良已無氣息。
飛歌電子廠的恐怖「怪病」
當年弱勢家庭裡的本省籍女工,渴望升學甚至以死明志的悲憤心情,在龍應台的筆下,卻成了「買來黃金鐲子一圈一圈套在手臂上,累積將來的體面嫁妝」,這完全是在踐踏台灣人的傷痛。
本魯在北投住了半世紀多,除了當兵那兩年以外,從未離開過這個小鎮。資深鄉民應該與我有同樣的印象,在淡水線鐵路的竹圍車站外,民族路上有家生產電視遊樂器和家用電器美商阿泰利(ATARI)集團的飛歌電子廠。
那年代公家機關與大眾交通工具都沒裝冷氣,大部分的電影院與餐廳也沒有,但飛歌的廠房裡,竟都裝設了冷氣。因此有些飛歌的女工很自豪,連放假都還穿著工廠制服,就像如今的空姐那樣。
但1972年7月起,飛歌電子廠忽然傳出「怪病」,女工一個又一個暴斃,門口就擺著一具一具的年輕女屍;因為覆蓋的白布不夠,有時甚至是兩具或三具女屍合用一塊。
當時還沒有《蘋果日報》,這種女體加屍體的聳動畫面,根本沒記者感興趣。但廠家附近的居民早已人心惶惶,平日熱鬧的廠區附近商家也都關門,瞬間變成了鬼域。
當時飛歌是台灣很重要的電子大廠,也是退出聯合國之後,美商還續留在台的重大投資,因此兩蔣鷹犬也在這裡很認真的「抓匪諜」。
後來女工暴斃的案例越來越多,連高雄那裡的日商三美與美以美也傳出同樣災情,最後政府工安部門不得不入廠追查,才發現根本就不是什麼匪諜在「下毒」,而是工廠為了節省成本所導致的悲劇。
戒嚴時代台灣什麼也沒有,就剩人命特多也特賤,因此工廠都用毒性甚高的有機溶劑三氯乙烯與四氯乙烯。但在冷氣房內工作的女工毫不知情,以致在廠房裡吸到了過量的乙烯中毒身亡。
「一圈一圈套在手臂上的黃金鐲子」在哪裡?
年輕鄉民或許不解,兩蔣既然要封鎖女工接連暴斃的新聞,為何廠方反而要這麼殘忍的曝屍?
原來那時雖已實行9年國教,但在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下,很多鄉下小女生,小學一畢業就必須上台北打工;但未滿14歲,工廠不能錄用,偏偏趕貨時又缺工,於是工廠要她們自己拿其他超過14歲在學女生的名字當人頭,用來領薪水與應付安檢。很多鄉下未成年少女為了進廠,於是冒用正在就讀高中女生的姓名個資來應徵。
資本家草菅人命,兩蔣鷹犬助陣,害得這些小女孩因工安意外暴斃,卻連微薄的勞保給付也拿不到。由於死者有些是廠方也不知真名,用假名在打工的小女生,偏偏一時間又無法通知家屬,只好曝屍以供家人指認。
消息傳開後,一方面有些家長聞訊趕來,急著連薪水也不要了,只想把確認還活著的女兒帶回家;但另一方面在廠方加薪再加薪之下,也有些貧困的少女,明知這裡已死了好多人,仍在真相未明之前趕著來應徵。
當年逃過一劫的飛歌倖存女工,後來下場也沒多好。1984年美商阿泰利將股權與廠房,移轉給另一家美商TTL公司,卻未發放資遺費。
吳念真也曾寫到,鄉下來的女工在工廠裡,被檢查出來有肺結核反應,廠方就通知家長領回。小女孩想到回家後沒辦法賺錢,反而還要浪費糧食,就在同事都去上工後,在宿舍裡上吊自殺。台灣經濟的起飛,靠的不就是兩蔣這種黨國資本體制剝削廉價女工嗎?
今天RCA罹癌的女工,聯福製衣、福昌紡織電子、耀元電子、興利紙業、東菱電子、太中工業等遭黑心老闆惡意關廠的工人,到底誰還戴著龍應台筆下那「一圈一圈套在手臂上的黃金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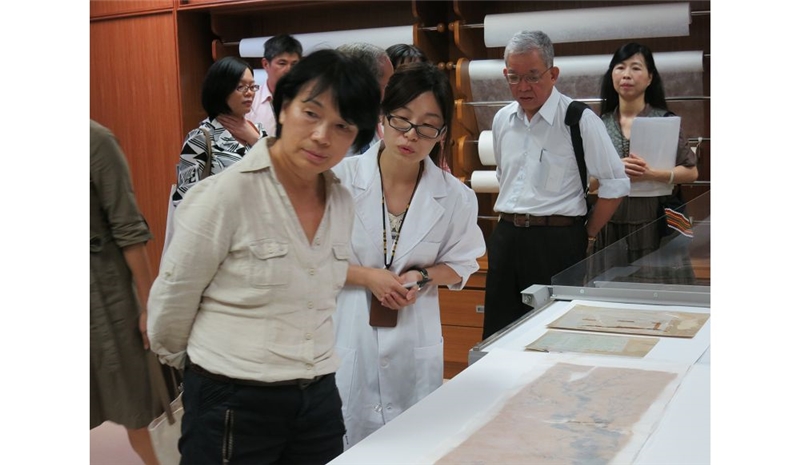
文化部前部長龍應台(前)曾撰文稱本省籍女工有錢買金手鐲,挨批是以高級外省人統治階級的傲慢發言。 圖:翻攝自文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