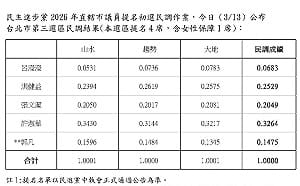當我們走到了人生的下半場,該如何看待自己呢?是緬懷過往的榮光,還是感傷流逝的青春,流氓阿德說,讓我們溫一壺青春來下酒吧,敬那些曾經擁有和未曾擁有過的。
聽第一首歌「虧欠」時,眼眶就已濕了。一直覺得阿德是「我輩」中人,雖然成長經驗和生活歷鍊大不同,但處在感情的「同溫層」裡,對於他歌裡的懊悔、羈絆、牽掛都有同感。繼「無路用咖小」的合作後,「虧欠」繼續找來擅長「後搖」的昆蟲白擔任編曲和製作人,阿德Vocal的主調在這首歌裡,其實退得較後面,讓樂器和合聲發聲,卻完整了整首歌的風格。「溫一壺青春下酒」由獨立樂團「守夜人」秦旭章製作,本該有些老派的情調,融入後搖基底後,讓這壺有些年歲的酒顯得青春。
說愛太過膚淺,阿德的歌裡借物來談情,「花帔」沿續他對母親和原鄉金門的思念,但有了製作人王榆鈞歌聲的加入,讓這牽絆多了份溫柔,跟專輯開場的「虧欠」,製作人昆蟲白硬生生、赤裸裸地展現心中的悔恨,兩者截然不同,聽「虧欠」心情是被撕裂後淌血,「花帔」則有更多的不捨。
不同於三年多前的「無路用的咖小」,是將自己流放於金門多年後,重新面對社會與流行樂壇之作,一個個合作的年輕樂團,像是一雙雙手,將阿德拉進現世的音樂潮流裡,「溫一壺青春下酒」則是這三年多,阿德回到台灣、樂壇後,生活中的一些感觸。專輯有一半如同上一張,找來不同的獨立樂團、音樂人合作,有一半是他與楊聲錚協力製作。年輕樂團替阿德的歌曲帶來不同的面貌,不同世代音樂人對於同樣的情感,有不一樣的詮釋手法,有時能平衡阿德歌裡的失落和無望,但不可諱言,有時也沖淡生命在音樂裡烙印下的痕跡。
曾是「刺客」樂團吉他手的楊聲錚,與阿德算是「同輩」,年齡、生活歷鍊相當,幾乎能無落差地擊中歌曲的核心,專輯裡兩人協力製作的歌曲,「最遙遠的距離」、「溫柔的暴動」、「生而為人,我很抱歉」、「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忠實保留了阿德歌聲的特質,雖不像其他年輕音樂人的作品,各有各的「起手式」,卻如同利刃般,不著痕跡地切入心中,如同漣漪般擴散。
全站首選:伊朗新最高領袖首度發聲!「不會放棄復仇」將繼續封鎖荷姆茲海峽
不再叫自己「流氓」阿德,他說自己現在是「搖滾詩人」,不受制於台語文的書寫方式,他用那嚴格來說不太正確的遣詞用字,寫下不管懂或不懂台語,都能閱讀理解的歌詞。抽掉音樂,每一首歌詞都如同一首詩,說的比唱還要多的「溫柔的暴動」,浪漫的詩意淹沒了一切,在阿德粗獷中感性的聲音裡,透過文字和音樂的描述,像是看了部無可救藥的愛情革命電影。「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透過密密麻麻的歌詞,阿德則唱出許多人藏在心裡,陰暗底層、不敢說出口的意念。
45歲回到台北,今年50歲的阿德寫下了「給五十歲自己的備忘錄」,本該是中年男子的懺情錄,年輕獨立樂團將歌曲編成了超級陽光正向,已過半百的阿德笑說,唱到間奏的啦啦啦啦時,真的有點啦不下去。「無論世事怎麼變化,絕對毋通變成討厭的大人」,這是阿德提醒自己的備忘錄,自己是別人眼中「討厭的大人」嗎?這是個殘酷的問題,得到的可能不是你想得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