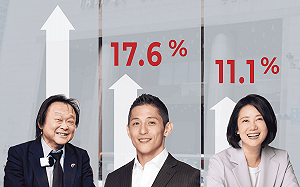22.6億元的吸金詐騙、四千多名投資人受害、跨境潛逃、還涉及中國統戰介入選舉案,這樣的人,法院竟然准以四千萬元交保?如今徐少東人間蒸發,檢調通緝在案。這不是個別法官的誤判,而是台灣司法制度對權錢犯罪長期失能的縮影。
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若犯罪重大、足認有逃亡或湮滅證據之虞,法院應裁定羈押,不得交保。徐少東不但涉犯銀行法、詐欺罪,且金額高達22億,刑期最輕5年以上,並已被限制出境,照理必須羈押禁見。結果法院以「有固定住所」「無逃亡之虞」為由准保,實質上等於給犯罪者自由出逃的門票。
檢方同樣難辭其咎。檢察官是否強力聲押?在法院准保後是否即刻抗告?在限制出境期滿前是否申請延長?若這些程序未盡,全屬怠忽職守。《公務員懲戒法》第6條明定,公務員怠忽職務致生重大損害者應予懲戒。如今22億資金去向不明,成千上萬被害人血本無歸,社會信任也隨之崩解。
更荒謬的是,法院設定的4000萬元保釋金,只占吸金金額的不到2%。這樣的比例在實務上等同「廉價的逃亡保險」。有錢人能輕鬆交保、繼續生活;沒錢的小嫌疑犯卻被長期羈押。司法制度在事實上形成階級分化——富者有自由,貧者被關,正義因此變成奢侈品。
這起案件也暴露出台灣司法對「重大經濟犯罪」與「國安案件」的監控漏洞。被告交保後並未被要求電子定位、未納入跨部會追蹤機制,導致潛逃如入無人之境。面對明顯涉統戰與境外勢力背景的被告,法官卻仍以「程序中立」為名縱放,這不叫依法審判,而是失職縱容。
制度改革刻不容緩。首先,應修法明定:涉及金額逾十億或受害人超過千人的經濟犯罪,一律不得交保。其次,涉中國滲透與選舉干預者應強制羈押禁見。第三,所有高額交保案件應強制電子監控,保釋金應納信託,逃亡即全額沒收補償受害人。最後,應公開裁定書與承辦檢察官姓名,接受社會監督。
司法不是逃生門。若連吸金22億都能交保,司法就已成詐騙共犯。真正的改革,必須從問責開始——查清那位准保的法官、那位未抗告的檢察官,才能恢復社會對法律的信任。
文: 蕭錫惠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