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5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雲南安寧出席瀾滄江—湄公河外長會後,宣稱依據《開羅宣言》《波茲坦公告》等二戰文件,日本戰後已將臺灣「歸還中國」。
隔日,我國外交部長林佳龍公開反駁,強調戰後的《舊金山和約》(1951)與《中日和約》(1952)從未將臺灣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各自存在。
王毅的說法延續北京一貫敘事,但與戰後正式條約文本不符。《舊金山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對臺灣、澎湖的一切權利、權原與要求,未指定受讓方。《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1971)處理的是「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問題,並未處理臺灣主權歸屬。美國長期政策亦未就臺灣主權採取立場,核心關切在於臺海和平與現狀維持。上述史實與法理構成駁斥北京敘事的基礎。
惡意曲解史實與國際法
支持北京主張者常引用《開羅宣言》《波茲坦公告》與日本受降事實,認為臺灣「戰後即已回歸中國」,並將聯大2758號決議視為國際社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主權的背書;在此框架下,任何主張臺灣主權或國際參與的論述,都被定性為「分裂中國」。
不過,實際上《開羅宣言》屬政治宣示而非法律拘束之條約,《舊金山和約》亦未指定臺灣受讓方;《中日和約》承接前述安排,等同確認「日本已放棄、但未移轉予中共」。2758號決議僅處理「中國代表權」,不涉及臺灣主權;美國公開文件與學術研究長年記載美方「不對主權採取立場/視臺灣地位為未定」的政策。北京將上述文件延伸解讀為對其統一主張之授權,屬惡意曲解史實與國際法。
宣言不是條約:從《開羅/波茲坦》到《舊金山/中日和約》
首先須分清「宣言」與「條約」在國際法上的位階。《開羅宣言》(1943)是政治性戰時宣示,《波茲坦公告》(1945)重申其原則,但兩者並非戰後安排主權歸屬的正式條約。真正具有約束力的是《舊金山和約》(1951):第二條(b)僅規定日本「放棄對福爾摩沙與澎湖的一切權利、權原與要求」,並未指明移轉給任何特定國家。
其後,《中日和約》(又稱《臺北和約》,1952)在第二條重申日本依《舊金山和約》放棄臺澎權利之事實,同樣沒有將主權移轉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亦即,並不存在北京口中的「已歸還」。
因此,北京若以《開羅/波茲坦》推導「主權完成移轉」,忽略了戰後真正生效的條約文本與國際法程序,屬以宣言凌駕條約的錯置。
被濫用的2758號決議:代表權≠主權
再者,北京經常以《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主張「國際社會已承認臺灣屬中國」,但決議的文本與會議記錄顯示,2758處理的是「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即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席位。決議並未提及「臺灣」二字,更未授權北京代表或治理臺灣。
近年各路研究與政策文件亦反覆澄清此點,美國國會推進之《臺灣國際團結法》(Taiw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更在條文中明確闡述:2758僅涉及中國代表權問題,不涉及臺灣主權與在聯合國體系的代表權。將2758延伸為對「臺灣屬中」的國際背書,是對文本與決議範圍的扭曲。
現實與原則:未由中共統治的事實、自決與美方政策
自1949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在任何一天統治或行政管轄臺灣,這一政治現實與戰後條約安排相互印證。
美國對臺政策長期重點在於維護臺海和平與現狀,並未對臺灣最終主權歸屬採取立場;國會研究處(CRS)文獻明確寫道:華府「不承認北京對臺主權、亦不承認臺灣為主權國家」,將臺灣地位視為「未定」,主張在尊重臺灣民意的前提下以和平方式決定。
此外,國際社會評估「臺灣是否一國」,亦並非由北京片面敘事決定,而是綜合條約文本、實際有效治理、人民自決意志與各國利益權衡的結果。當北京以軍事與認知戰壓迫臺灣,並以法律戰擴張敘事邊界時,澄清「條約與現實」之區別,正是反制錯誤敘事的關鍵。
臺灣的主權敘事:以法理與民主實踐對接國際社會
面對北京新版「史實話術」,我方對外敘事宜牢牢錨定兩個支點:其一是「條約文本—宣言之區分」,其二是「民主自決—有效統治」之現實。
外交部近日明確指出,中華民國是臺灣唯一合法政府,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此一主張建立在《舊金山和約》《中日和約》與聯大2758號決議的正確解讀上,亦反映了臺灣長期穩定的民主治理與對國際責任的承擔。
對外,臺灣應持續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在多邊場合駁斥北京對2758的誤用;對內,則需加強史實教育與國際法素養,避免被「三個八十年」等口號牽引。唯有把條約與事實說清楚,臺灣的主權敘事才不致被惡意話術帶風向。
結語
北京試圖以「開羅—波茲坦—受降—2758」的線性敘事,導出「臺灣已交中國」的結論;但一旦回到具有法律效力的戰後正式條約與決議文本,這套敘事即告失效。
《舊金山和約》明確只有「日本放棄」,沒有「移轉予中共」;《中日和約》承接其上位安排,亦未將主權交給北京;2758號決議更僅處理「中國代表權」,未涉臺灣主權。歷史與法律都不支持「臺灣屬中」的命題。
作為民主社會,我們不僅要在論證上嚴謹,更要在對外話語上堅定:臺灣的未來由臺灣人民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決定。當國內共識與國際連結同步強化,臺灣的主權地位就不會因話術而動搖,而能在理性與法理上持續站穩。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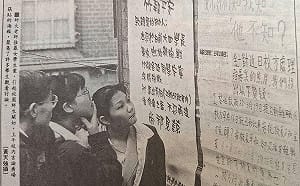





![[影]年假尾聲曬萌犬片!賴清德分享蔡英文帶「樂樂、鳳梨妹」作客官邸](https://images.newtalk.tw/resize_action2/300/album/news/1021/699b1786a6f50.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