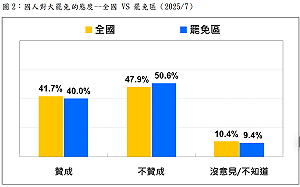在台灣,罷免行動已成為一種另類的直接民主形式,與傳統的間接匿名投票形成鮮明對比。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的民意代表,都有可能面臨民眾發起的罷免連署。這種連署要求公民團體逐一接觸民眾,當面徵求支持並簽名,每位參與者必須公開表達立場,這種面對面的參與方式讓罷免成為直接民主的生動展現。
罷免權作為直接民主的重要形式,考察其歷史發展的過程,可以上溯到中華民國建國之初,從孫中山的遠見傳承至今。孫中山受到在台灣的民主實踐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當前台灣民眾積極發動的罷免行動,更展現了一種另類的直接民主形式,與傳統間接投票截然不同,成為人民參與政治、監督政府的有力工具。這種直接民主的現代實踐不僅延續了百年理想,更為台灣的民主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其價值與意義。
孫中山早在百年前便提出罷免權的概念,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若公職人員失職,民眾有權將其撤換。他受到瑞士直接民主傳統與美國民主制度的啟發,將罷免權視為人民參與政治的核心權利,與選舉、創制和複決共同構成完整的直接民主框架。這種思想為台灣民主奠定了基礎。如今,台灣憲法第17條明確保障人民的罷免權,體現了孫中山的民主理想,也讓民眾得以直接行使主權,監督政府運作。罷免權的設立,正是直接民主精神的具體實現。
最近10年的時間裡面,臺灣進行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罷免活動,現在可以說一般民眾對罷免是相當熟悉,做不好就可以把原來投票支持的人選拉下來,在台灣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以2016年高雄市長韓國瑜的罷免案為例,民眾通過連署與投票成功罷免失職官員,顯示罷免權如何成為人民自救的「最後防線」。這種模式不僅提升了民眾的政治參與感,也強化了對公職人員的問責,體現了直接民主的真諦。
罷免的過程要連署成為一種另類的直接民主,作為直接民主的實踐,雖然價值顯著,也伴隨著挑戰。罷免要連署,讓人民直接參與決策,增強政治參與感與責任感,同時促使公職人員更加謹慎,真正反映民意。更重要的是,罷免要連署,彰顯了人民主權,讓民眾成為政治的主體,而非僅依賴代議制度。但挑戰同樣存在,罷免連署耗費大量時間與人力,決策效率可能受影響。民眾也可能因情緒或片面資訊而做出非理性決定,帶來民粹風險。罷免決策未必基於專業考量,可能影響治理品質。這些問題提醒我們,直接民主雖具活力,但需謹慎運用,以確保其建設性。
展望未來,罷免連署所帶來的影響,罷免權成為落實直接民主的主要方法,仍需不斷完善以適應時代需求。適度調整連署門檻可以避免權利被濫用,同時保持其可操作性。建立更嚴謹的監管機制,能確保罷免程序的公正與合法,防止政治操弄,加強公民教育有助於提升民眾的理性參與能力,讓罷免權的行使更具意義。這些努力將使罷免制度在直接民主的框架下發揮更大作用,進一步深化台灣的民主文化。
罷免權從孫中山的理想傳承至今,已經成為台灣民主的基石,而當前台灣的罷免行動作為一種另類直接民主形式,更展現了人民參與政治的決心與力量。罷免權的實踐不僅延續了瑞士直接民主的傳統,也實現了孫中山對人民主權的期盼。面對未來的挑戰,我們應繼續保護並完善這一權利,讓罷免權在直接民主的實踐中持續發光,確保台灣的民主之路在人民的參與下更加穩固與輝煌。
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