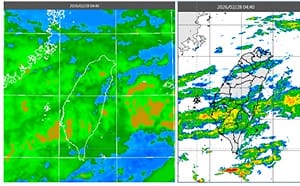賴清德總統收養的流浪狗「斑斑」因受設置在山中的山豬吊陷阱所困,導致左前肢節肢。此消息一出,動保團體順勢對山豬吊禁用議題提出倡議,紛紛以「不要有下一個斑斑」作為呼籲,希望能夠喚起大眾對流浪動物受到山豬吊殘害情況的關注,也透過「斑斑」的遭遇向總統和立法委員喊話,督促國家公權力介入限制傷害無辜生命的行為。
在臺灣,我們可以常常聽到動保團體以「任何人都不應將傷害、殺害其他生命視為一種『權利』」的理由對於狩獵行為加以批判。但是在動物權益保護的世界領頭羊德國,狩獵卻是以另一種正面的形象出現。根據德國《聯邦狩獵法》(Bundesjagdgesetz)規定,州政府公布「有害鳥獸」,並開放獵人狩獵。依照德國獵人協會(Deutscher Jagdverband)的資料,目前德國的「有害鳥獸」諸如:松鼠、山羌、浣熊等動物,甚至在大部分州政府的狩獵法規定,特定的情況下可允許獵人射殺貓狗(Nadine Carstens,2024)。透過狩獵得以去除有害野外生態的物種,以平衡各物種的數量維持良好的生態環境。換句話說,在德國狩獵不是什麼十惡不赦的事,獵人反而在動物保育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動物保護:一種信仰
基於數字統計、對於動物同情或者血腥畫面的傳播,都可以是支持動物及生態保育的契機,如果說支持動保單純的建立在「理性」、「務實」的科學觀點,並不現實。因為支持動保本質上就是一種「價值選擇」,動物保護主義者「選擇相信」哪些資料和理念可以證實他們心中所想的,如動物處境越來越糟糕的「事實」。這樣的事實建構在對於數據的著迷與多種情緒的交織,強大的說服力讓支持者深信不疑,最後成為動保主義者該當奮勇捍衛的「信仰」。
當然信仰動保其實沒有任何可以批判的地方,以動保為皈依的行動,一再的提醒大眾:「我們必須要為動物做些什麼了!」繼續漠視動物生命和權力非文明社會的樣貌。動保團體以悲觀詞彙配上驚悚的畫面告,努力呼喚大眾的同情心和道德感,以及「動物本位」的思考。
但是,動物保護行動作為環境保護運動的一環,環境保護之目的是為了讓人類生存條件得以永續,增加人類福祉。當我們只凝視生態與動物,並要求「做些什麼」的時候,我們真的有考量到最基本「人類」的福祉嗎?還是有些人的聲音因為傳不上「天聽」而受到忽視和粗暴的對待,最後成為被消失的一方呢?或許我們該問的是:如果今天有一群人因為他自己擁護的信仰要求你改變現在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接受嗎?
如果未能考量人生存福祉的信仰從倡議的階段爬了出來,變成了具體的「政策」實現呢?讓我們來想想最壞的情況,政府制定「只考量動物」的政策,推進把動物權利凌駕於人權利之上的強制力發展。若真如此,為提升人類福祉的理想頃刻間被拋棄,動保信仰此時不僅僅只是價值觀或街頭倡議,而是一支鋒利的劍隨時刺向沉默的人群。
如果信仰變成了武器
這不是沒來由的危言聳聽,在Virginius Xaxa教授於2008年發表的書中提到,印度政府在1952年以「保護國土森林面積」為由,將世居在森林的上百萬部落原住民視為「非法侵占者」,將森林劃為國有地,限制部落居民森林使用權,並且強迫部落居民遷出森林,大量族人頓時流離失所。諷刺的是,把部落族人攆走的同時,政府開始對森林進行肆無忌憚的開發用以支持國家的經濟發展,這時森林反而被嚴重破壞,連帶破壞野生動物棲地。不過為了繼續維持政府「保護國土森林面積」的信仰,又不斷的把破壞環境的責任推給「侵占者」,驅逐原住民設立國家更多野生動物保護區,導致更多的民族生存危機,如此惡性循環(Virginius Xaxa,2008)。
時間到了2006年印度政府基於糾正上述政策造成的歷史錯誤,制定並通過了《表列部落(森林權利承認)法案》(The scheduled tribes (Recognition of Forest Rights) Bill),總算承認並「重新賦予」部落對森林的管理,這意味著在政策上正視部落族人權利,正視一段不義過往的重大意義(Virginius Xaxa,2008)。可是,「原住民是森林侵略者」的汙名早就已經被深深的建構,「激進的動保團體對於國家把森林交給他們所認為破壞森林資源、狩獵野生動物的原住民感到厭惡」(Virginius Xaxa,2008)。甚至到今天印度仍然發生為了設立老虎保護區而大規模驅逐原住民的行動(Survival International,2024)。的確,當名為動保的利劍出鞘對準某一個族群時,所產生的傷害似乎就難以復原了。問題來了,如果我們覆盤整個悲劇故事,那麼讓動保信仰變質成冷血武器的關鍵因素是什麼呢?
誰被消失?沒有話語權的「當事人」
發現了嗎?真正受影響最深的原住民在政策中和論述中,基本上都被他者化,「入侵者」到「殺害動物的兇手」,至於最核心「當事人」的聲音呢?
在印度原住民的視角下,森林不是描述很多植物和動物的地方而已,森林代表是食物來源、經濟來源、習慣來源和神話及信仰的來源,也就是因為對森林的生存和文化的重度依賴,部落族人謹守包括森林和狩獵的嚴格禁忌,避免觸犯神靈。例如:把樹林茂密的地方視為祖靈的居所,不得進入和砍伐破壞;在印度東北部的庫魯克人(The Kurukh)禁忌裡規定「六月和七月期間,獵人不得殺死或捕獵任何野生動物或鳥類」(Virginius Xaxa,2008)。
總結來說,部落族人建立並保持與環境、動物的和平關係,就是民族能否安身立命永續發展的關鍵。再者,印度野生動物的確受到人類活動的嚴重威脅,然而造成野生動物生存危機的是政府和企業聯手,無節制對森林開發破壞動物棲息地,還有莊園主無差別的獵殺野生動物,根本無法證明原住民狩獵和生態的破壞有直接的關係(Virginius Xaxa,2008)。不過以上這些聲音全部被忽略,扣上「因為原住民長期佔用森林不會管理它、原住民狩獵導致野生動物減少」的帽子,來支撐政府與動保團體的信仰是一件廉價又簡單的事。一方面不是所有人都了解原住民文化,另一方面比起得罪有權有勢的人,將矛頭指向原住民真是一筆划算的生意。
印度原住民在話語權上根本無法與之抗衡,只能任由其掌握著話語權,被站在代表著「現代」、「文明」制高點上的「外人」擺布,甚至被迫流離失所。蓄意排除弱勢民族的話語權、參與權,非但無法展現動物保護信仰的優越之處,反而成為殖民式霸權再現,這一切都凌駕於弱勢民族的生存發展之上。
結論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不論是個人、利益團體還是國家要求,強迫你要依照他們堅持的信仰過生活,任何有理智的人一定會想:「憑什麼?」誰可以放任他人將自己信仰強加於社會中邊緣的群體,放任他人在論述和政策中持續排除沒有話語權的群體,放任他人自以為是的信仰,實則再現過時的霸權思維,加劇對於弱勢民族的悲劇和汙名化。
就像是某位總統候選人提出驚人的動保政見:「針對狩獵與野生動物保育衝突議題,本黨表示將嚴格取締陷阱、捕獸夾等傷害動物的手段與工具。此外,也會對原住民教育宣導,引導其改變宗教祭典方式、獵食方式等。」(窩窩,2024)
當我們看到這樣的說法時,也許我們應該想一想,動物保育的核心理念是什麼?政策抱持著什麼樣的思維和行動去捍衛動保的信仰,是重視參與、對話、協商的過程,還是上對下的「教育」呢?
文:林若翰(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學生)
參考資料:
Nadine Carstens. (2024/4/12). When Dogs and Cats Are Hunted. DeutscherTierschutzbund.取自:https://www.tierschutzbund.de/ueber-uns/aktuelles/magazin-du-und-das- tier/artikel/wenn-hunde-und-katzen-gejagt-werden#c10254
Virginius Xaxa. (2014). State, Society, and Tribes: Issues in Post-Colonial India(1st ed.). New Delhi: Pearson.
Survival international. (2024/9/ 20). India’s Indigenous Peoples Rise up againstEvictions from Tiger Reserves. Survival international.取自:https://www.tierschutzbund.de/ueber-uns/aktuelles/magazin-du-und-das-tier/artikel/wenn-hunde-und-katzen-gejagt-werden#c10254
洪郁婷 & 陳信安。(2024年1月9日)。2024總統候選人給問嗎?十大動物議題政策回應。窩窩議題懶人包。取自:https://wuo-wuo.com/infographics/lazypack/1898-2024-president-election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