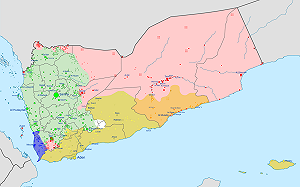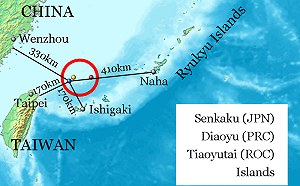與禎苓相識於連續幾日的交流會議,離開台灣,相同的成長脈絡長成血肉,儘管並非深交,卻讓在異鄉的我們覺得一體。
回到台灣不多久,便在人間福報副刊看見禎苓的〈拉窗簾〉。她細膩的描述自己與父親在窗簾拉開與否這件事上意見相左,父親喜歡大亮,而她習於隱蔽,從世代的差異態度,轉而談論到隱私與窺探的問題,身體的裸與蔽皆牽連著疼痛的感受,如文末:「為此,比起透視,我更慣於隱蔽自己,遮於層巒壁嶂之中,彷彿某種篩檢,不讓多餘的陽光進入裡頭,甚至下意識躲避每個曝露的可能。因為,我寧可燜燒,也不願晒傷。」都是痛的,但是經過選擇後的痛。
對於痛覺極敏銳的覺察亦在《腹帖》中呈現,疼痛如同震央的核心,不斷向外推展,連結家族故事。譬如〈腹語〉談的是經痛,透過子宮說出與母親之間複雜難解而又親密的關係。她自母親子宮脫胎而出,當她每月陣痛時,呼救的對象仍是隨成長漸生鴻溝的母親;相對的,經期一向無誤的母親卻因子宮肌瘤失去了子宮,作者如此描述那失去的鄉土:「爸告訴我,那子宮大得像個碗公,邊說邊比畫著。我臆想那模樣,我出生前十個月的故事就放在那,曾經孕育我的鄉土,如此要容納一個兩三千克的寶寶當然大。只是女人珍貴的秘密,被掏出,腐朽的、惡臭的、難以名狀的,血淋淋地攤在眼前,難以招架的恐慌與恐懼,通通麻醉、去除。月經不再,孕育終止,取消了女人的天賦,延長了存活的機率。生命,總是難以抉擇的。」子宮,是母女隱蔽的連結點,亦如女人命運的象徵,最終連結到肉身的生命抉擇,〈腹語〉的震央不斷向外擴散,欲語還休。
另一個獨特的關照點,是作者身為研究者的身份。譬如我特別喜歡的〈羊腸小徑〉一文,首段即以一張清代的人體圖破題,再談《小孩月報》上的腹腔,在醫生依憑想像拼湊器官原樣的時代,胃腸特別難以拼湊,「在衛生條件不佳的年代,禍從口入,病菌滑進胃腸,滋長。肥沃的胃腸是疾病的溫床,主宰著人們的生與死。/胃腸,是充滿變數、瀰漫不安的,吞吐著時代的語境。」自清代跳躍至現在,作者描述善於忍痛的外公兩次胃部手術,第一次是年初一圍繞滿桌美食時接到外公住進加護病房的通知,等待美食的胃對映穿孔的胃,切除的胃與守候在外牽腸掛肚的胃,這些對比將腸胃屬於日常屬於家的意義纏繞如腸。
第二次病發,外公終不敵病魔離世,作者發現外公另一副胃腸──外公的房間:「外公的房間是他另一副胃腸,即便烈焰澈底燒光肉身,腑臟付之一炬,還遺留徑路,讓我們見證匿藏多時的流光,那些不教人輕易看穿的點滴,被我們翻攪著、重新感受著。我們有如行在羊腸小徑,那條蜿蜒人體內部的腸管,觀賞裡頭的枝枝節節。」那裡有她不知道的故事:「原來外公那麼愛漂亮,那樣著迷時髦物件,原來我們不曾真正知道一個人。就像清代醫生想像人體臟腑,我們都是以想像認知一個人。」作者將親人的感受與研究者的關照巧妙緊密扣連,讓讀者隨她筆下的羊腸小徑一路低迴,也不停回望屬於自身生命裡的暗巷。
那些深邃而細瑣的痛,在禎苓的文字中被體貼地擺放,有溫度、有省思,更有對日常敏銳的觸覺,從肉身到心房,在一個故事裡夾藏另一個不說破的故事。
---------
徐禎苓,中央大學中文所畢業,目前就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班。曾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台北文學獎、吳濁流文藝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及地方文學獎等。作品散見《幼獅文藝》和報紙副刊,出版論文集《現代台灣文學媽祖的編寫與解讀》。2015年出版首本散文集《腹帖》。
作者:張郅忻(著有散文集《我家是聯合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