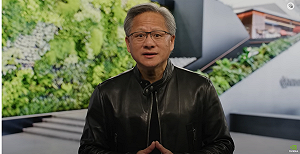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前不久受訪時證實,「反廢死公投是非常重要的議題」。法定公投日為8月23日。據瞭解藍營將會很快提案排入立法院程序委員會,趕在5月23日前送進中選會。
反廢死反戒嚴 藍雙案意在反罷
後來國民黨再增列反戒嚴公投,並在3月25日院會表決通過「您是否同意『各級法院合議庭法官判處死刑不須一致決』之政策?」公投案,及「你是否同意政府應避免戰爭,不讓台灣變成實施軍事戒嚴、青年喪命且家園被毀的烏克蘭?」公投案,均逕付二讀。顯而易見的是,國民黨要推動反廢死與反戒嚴公投,主要目的仍在於反制綠營結合民團大罷免藍委,不是因為他們對全民公投有何堅定信仰和不變理念!
2022年11月26日地方選舉同時舉辦18歲公民權的修憲複決公投,這是不分藍綠陣營、有志一同的修憲共識,應該比2005年第七次修憲讓國民大會走入歷史,和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更容易。後者只有國民黨及民進黨一起推動,親民黨與台聯黨是反對的,最後還是修憲成功。結果被笑稱是「18憲草」的18歲公民權修憲複決公投卻功虧一簣,足見各黨各派不是宣傳不夠就是動員不力,尤其是藍營,表面上支持,實際上也是算計選票的政治利益,投票人口的年輕化未必有利藍營選票的增加。名為支持,實仍杯葛。

往前一年的2021年,國民黨提出四大公投案,包括「公投綁大選」、「核四啟封商轉」、「反萊豬進口」及「天然氣接收站遷離桃園大潭藻礁海岸」,都是為了2022年地方選舉選票利益的政治操作。特別是「公投綁大選」的公投提案,完全悖離國民黨長期以來反對公投與反對公投綁大選的立場。2022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從2018年只剩6席又掉1席剩5席。
2018年縣市長選舉國民黨大贏的關鍵,除了「韓流」因素,多少也跟公投綁大選,加上2017年《公投法》修正降低通過門檻有關。那次總共有十大公投案,國民黨一口氣就提出三案,包括「反空汙」、「反深澳電廠」與「反核食」,全部獲得通過,也確實讓民進黨丟掉縣市長的半壁江山,從2014年的13席降到2018年的6席。
全站首選:傅崐萁提晶片國安法 律師轟:你領國家錢去中國都沒報備 憑什麼私人企業要被質詢?
起於民主自決 公投已21年
2018年、2021年、2022年乃至2025年,國民黨先後單獨或擬提出8項公投提案,另外與民進黨等其他政黨共同提出一案。除18歲公民權修憲複決公投提案外,民進黨則一案未提,連民間團體所提以台灣名義申請參加2020年東京奧運公投案,也不是那麼熱烈地支持。難道民進黨已經視公投如畏途,而國民黨曾幾何時改變對公投的看法與立場?物換星移,變成國民黨支持公投,力推公投綁大選,而民進黨迷信菁英領導,反對公投,甚至修法取消公投綁大選?
回顧全民公投在台灣的實施,短短21年,已成直接民主、普世價值的全民共識,是台灣民主進程中最彌足珍貴的資產。公投的基本人權,不能剝奪、限制,更不能沒收。這是天賦人權,位階甚至在憲法之上,這也是國民主權原理的具體呈現。不管在國內或是在海外,每一個人都會講台灣前途應由2,300萬的住民來做選擇;台灣的命運應由台灣人民來做決定。至於如何選擇和決定,不是透過間接民主的國會,也不是第四權的媒體輿論,尤其不是哪一個政黨比較偉大、哪一位總統比較英明。台灣的未來,只有台灣人民才有權選擇,不是總統個人或執政黨所能片面決定。「住民自決」、「公民投票」是影響我一生非常重要的民主理念,對我個人而言,早已昇華到「政治信仰」,而且牢不可破、堅不可摧。

早在1983年黃天福、江鵬堅、康寧祥等民主前輩參與的那一次立委選舉,共同政見是「民主、自決、救台灣」,當年「自決」是絕對的政治禁忌,不能做也不能說,否則就是煽動他人犯罪,要判七年有期徒刑。國民黨政府叫我們不能談,為候選人黃天福站台助選的阿扁議員偏要談,於是就把「自決」打「××」,變成「民主、××、救台灣」,改談「××」的事,大家都知道就是「自決」。如果不能談「××」,講出來要判7年,再把「××」改為「七年」,變成「民主、七年、救台灣」。不談「××」,改談「七年」,民眾反應更熱烈。住民自決的公投,原來是從台灣的民主××開始的!
1991年,我在民進黨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針對所謂台獨黨綱提出修正案,「基於國民主權原理,要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獲得無異議通過。所以,與其說是民進黨「台獨黨綱」,經過修正以後,毋寧說是「住民自決台獨黨綱」或「公投台獨黨綱」還比較貼切。
從市長到總統 扁8年催生公投
1994年出任台北市市長,阿扁身為民進黨員,當然要奉行黨綱,實踐黨綱「住民自決」、「公民投票」的民主理念和信念。當年核四存廢議題如火如荼展開,台北市剛好在核四廠30公里的安全逃命圈範圍內,作為市長,我覺得台北市民有權利針對核四存廢議題來做選擇和決定。所以我正式推動核四公投,礙於少數執政,藍營控制的台北市議會,認為沒有公投的法源,絕對不可以舉辦公民投票。就把「公民投票」的「公」改為「市」,變成「市民投票」總可以吧!仍有公投意涵!本來要和1996年首度民選總統投票日在同一個投票所一起投票,即「公投綁大選」。國民黨的中央政府以會影響總統選舉為由,禁止「核四市投」在同一個投票所。
只好改在投票所外面30公尺的地方,另設「市民投票匭」。為了給市民方便,先將選票透過里長、里幹事,分送至每一個家庭,然後在投票日當天,市民再將「市民公投」簽好的選票投進核四市投的票匭。當日開票結果,投票率很高,超過一半以上的市民都投了核四存廢的市投一票,多數贊成停建核四。這是一次非常大規模的民意調查,讓大家瞭解到關於核四存廢的議題,台北市民有不同的意見,而且多數主張停建核四。從1996年市民公投走到2004年全民公投,前後8年的光景。

2003年上半年,我宣布沒有公投立法照樣要舉辦公投。同時設想了三個公投議題,第一是國會改革:當時林義雄主席正在推動立委席次減半,可以交付公投決定;第二是國際參與:台灣要加入WHO(世界衛生組織),也可以透過公投讓人民決定;第三是核四存廢:我在市長任內,一個地方政府就推動核四存廢的公投,2000年宣布停建核四時,總統被藍委提案罷免,行政院長被送監察院彈劾,引發重大的憲政危機。2003年當我提出要舉辦三大公投時,由於沒有公投的法源依據,起初大家不以為意,後來國親兩黨知道我是玩真的,先是加碼阿扁有三大公投,他們有五大公投。阿扁認為藍營是喊爽的,幾十年來,將公投視為洪水猛獸,公投等同台獨,將會帶來災難、帶來戰争,是一條永遠不能踩踏的政治紅線。不出所料,國民黨很快就五條變沒半條,再通過「鳥籠公投法」,公投立法剝奪限制進而沒收公投的權利,把公投關在鳥籠裡了。
2003年11月27日國會連夜表決《公投法》,過程亂七八糟,版本一大堆。只知道民進黨團幹事長陳其邁說「輸到脫褲」。後來被我發現第17條(現在的第16條)有一扇巧門。所謂巧門,就是「鳥籠公投法」竟然出現第17條的破洞。因為這一條和總統有關,只有總統可以援用。原來第17條是行政院的版本。《公投法》通過第三天,我在松山饒河街慈祐宮的活動正式宣布,公投是我的理念,更是我的信仰,我找到了舉辦公投的法源依據,不用立法院同意,也不用國親兩黨掌控的公投審議委員會通過,總統可以在國家遭受外力威脅,國家主權遭受危害時,主動提出公投案,經行政院會決議,直接交給中選會,中選會沒有say no的權力。真是天佑我也!
經過國安會及相關部門詳加研議後,提出「強化國防」與「對等談判」兩大防禦性公投的議題,並和總統大選合併舉行。美國對公投題目沒有意見,中國則反對台灣舉辦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任何公投。反對公投綁大選的藍營則極盡杯葛之能事,不只呼籲大家不要領票投票,也堅持公投與總統選舉的領票不可以在同一張桌子。
而來自民進黨及綠營內部反對聲浪也不小,甚至認為公投的舉辦是「票房毒藥」。阿扁則始終如一,不受任何雜音影響。《相信台灣》這本選舉書特別提到,阿扁可以在競選總統連任失敗,但一定要推動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的公民投票,要讓公投成為台灣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由於推動公投導致落選,「我也甘願接受」。
已成台灣共識 盼綁大選法制化
總統選戰的最後一個月,我談的都是「公投100」,總統選一號阿扁,兩大公投都蓋○○。選舉結果,一對一的總統大選,民進黨第一次贏得過半數的全國選票,兩大公投投票率都有四成五,贊成「強化國防」的同意票高達651萬票,比我連任總統的得票數647萬多。按照目前的1/4低門檻,阿扁總統任內四大公投案應該全都通過了。

有「台灣公投之父」封號的蔡同榮—蔡公投,回到台灣奔走公投立法,經過13年的拚搏,終於在2003年完成法制化,也在2004年舉辦史上第一次的全民公投,雖不滿意也無法接受,但總算走出第一步。反對公投最烈的國民黨比民進黨更愛啟動公投提案,甚至還提出「公投綁大選」的公投案,不管動機如何,公投已成不分藍綠的台灣共識,期待國會多數的在野陣營應可修法,再將「公投綁大選」法制化,並推動無論多少公投提案,全部印在同一張公投選票,同時採用電子投開票。公投無罪,2018年縣市長選舉投票不是「公投亂象」,而是「選務亂象」,千萬不要劃錯重點!
賴總統最近召開國安高層會議後,首度公開指稱「中國是境外敵對勢力」,並提出五大國安威脅、17項因應策略,被媒體稱為「賴17條」。阿扁回想到21年前由總統啟動的首次全民公投,依據《公投法》也是第17條。

作者簡介:陳水扁
- 中華民國第10-11任總統
- 民主進步黨第9、12任主席
- 台北市第1任民選市長
- 中華民國第1-2屆立法委員
- 台北市議會第4屆議員
- 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