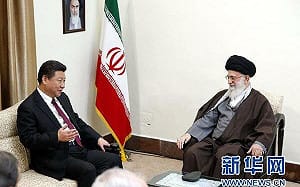1920年,剛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蔡培火,在臺灣人自己創辦的《臺灣青年》雜誌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我島與我等〉,在裡面引用了續日本學者泉哲的理念,喊出了一句擲地有聲的宣言:「臺灣乃帝國之臺灣,同時亦為我臺灣人之臺灣。」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這句話,可以說是臺灣人認同的開端,預告了隔年1921年,臺灣的知識菁英、地主仕紳即將聚合起來,共同尋找臺灣人的自我解放途徑,開啟了百年來如永劫回歸一般的團結與分裂、新生與苦難、妥協與掙扎。
現正最夯:伊朗遭空襲畫面震撼 楊植斗怒轟苗博雅:戰時還談正常上課?
臺灣的「主體性」好像腳邊的影子,轉身低頭就可以看見,卻永遠無法觸及、如同幻夢般永遠懸掛在那裡,直到2021年的今天,我們也還在追逐那近在咫尺,卻隔若海角天涯的「臺灣人的臺灣」。
臺灣文化協會及其精神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直到日中戰爭開始之前(1918─1937)短暫發出灼人光熱,在那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時光之中,除了尋求島民自治的可能性之外,也不斷探索自我存在的尊嚴、殖民地所有人彼此平等對待的尊嚴。
婦女運動的先驅
當前熱搜:會晤習近平前先打伊朗 澳專家:川普暗藏精明的地緣政治戰略
他們喊出三大解放「民族解放、階級解放、婦女解放」,在日本威權統治底下設法找到抵抗的方法,但同志之間卻因為對於解放的優先順序以及運動路線差異而起了爭執,最終在分裂與擾攘中,被日本人一一鎮壓。
臺灣現代婦女運動起始於1920年代,不過很難說是一場運動,毋寧說是幾名勇敢的女性挑戰了男性絕對霸權的一場社會事件,但卻也喊出了臺灣首次的女權之聲。
1925年的時候,彰化出現了台灣第一個女性平權團體——「彰化婦女共勵會」。當時彰化婦女共勵會是由幾名受過中學教育(當時女性在臺灣所能接受到的最高學歷)的年輕女性所組成,而臺灣文化協會的成員如王敏川等人,也非常鼓勵這些女性出來組織團體,打破傳統對婦女的人身限制及刻板印象。
她們曾經發起臺灣第一次的女性公開演講活動,在彰化的天公廟埕,沒想到很多人過於緊張,在上台演講前夕,因為底下好事男性不斷鼓譟,許多女性嚇到不敢上台,只好由文協的男性臨時上台代講。
那天是1925年8月22日,理應是臺灣性別平等運動的光榮之日,但卻磕磕絆絆,受到主流社會的無端訕笑,如同這一百年來所有性別運動者所承受的。
再之後,沒想到彰化婦女共勵會的成員,其中有些人走得比大家想像中的更要前衛,她們不僅要人身自由、要戀愛自由、更要主導自己的人生——沒錯,在20世紀中葉以前的臺灣女性,任何自由都是奢侈。
共勵會當中有五名女性,如潘貞與吳進緣等人,想一起到中國上海追逐「自由之夢」,想要去上海當電影明星、想要跟男友到那裡戀愛結婚。
結果她們真的逃走了,卻不幸在基隆港邊被抓了回來。跟她們一起私奔的男性楊英奇是彰化街長(市長)楊吉臣的兒子,其中一名女性吳進緣是彰化仕紳吳德功的晚輩,所以這件事就引發地方上的政治鬥爭,文協人士在《臺灣民報》上攻擊彰化街長的「毋成囝」把這群女性帶壞,保守派人士在《臺灣日日新報》上攻擊文協成員灌輸女性錯誤的道德觀念。雙方各執一詞,在報紙上連番筆戰,成為地方上茶餘飯後閒聊的「淫奔事件」。
最後事情是這樣解決的:彰化婦女共勵會開除這四名「追逐夢想的女性」的會籍。而楊英奇則向吳家長輩下跪道歉(但其實楊英奇的女朋友是潘貞)。不久之後彰化婦女共勵會自行解散。這樣臺灣第一個女性平權團體,就這樣黯然消失在公眾視野當中。
有沒有和今天的臺灣有相似的情節?所以我們說這是百年的永劫回歸。回顧歷史,其實就是用一面客觀的鏡子,審視當代的「我們」。我們是誰?要去哪裡?路線怎麼走?百年前的文協前輩們,已經蘸著血淚寫作歷史,走在我們前方親身示範給我們看了。
農工階級解放運動的動向
再者,三大解放裡的「階級解放」,談的是勞動者的尊嚴。一戰結束後,由於俄羅斯二月及十月革命相繼發生,全世界的弱小國家及殖民地開始流行共產主義,臺灣人大受鼓舞,也在二〇年代紛紛組織勞農團體,反抗資本家及殖民政府。文協裡面許多核心成員認為勞農階級受到嚴重剝削,文協應該往階級鬥爭的路線前進,所以1927年的時候,文協內部路線起了嚴重衝突,林獻堂、蔡培火及蔣渭水等人退出文協,而王敏川與連溫卿等人則留下來繼續組織「新文協」。
農民運動是由1924年的二林蔗農組合帶起抗爭先聲,接著簡吉、趙港等人組織鳳山農民組合、大甲農民組合等團體,繼而在1926年組織了全島性的「台灣農民組合」,發動如「中壢抗租事件」等大規模不合作運動,共介入了400多起的農村爭議事件,全盛時期臺灣農民組合共有27個支部,24,000多名成員。不過後來臺灣農民組合受到日本政府大力鎮壓,簡吉與趙港等核心成員遭到逮捕入獄,漸漸於二〇年代晚期失去抗爭動能。
而勞工運動的高峰則是在文協分裂後,蔣渭水另行組成臺灣民眾黨及全島性的「臺灣工友總聯盟」,與新文協連溫卿的「臺灣勞工運動統一聯盟」分立較勁。雙方各自在1928年左右發起各式罷工,例如黃賜與盧丙丁等人協助發起的「高雄淺野水泥工廠抗爭事件」,約七百多名工人集體罷工,臺灣勞工抗爭的力道與決心,一時震撼了當時的日本政府及資本家。不過與農民運動一樣,最終勞工運動也在政府打壓下,逐漸消聲下去。
二〇年代末期的左翼大清洗事件後,臺灣的階級抗爭運動逐漸消失,剩下較為溫和的議會請願運動還勉強運作下去,最終這一條自治路線算是有達到最基本的訴求——在1935年實施了臺灣第一次的「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會員選舉」,雖然不是普選,也僅限於地方議會層級,但至少臺灣人付出了十幾年的心血,總算踏出了非常艱難的第一小步。
三〇年代中期以前,雖然社會運動大多數遭到檢查並消聲,但此時卻是臺灣第一次的文化黃金年代,亦可稱為「跳舞時代」,各種文學、音樂及藝術創作蓬勃發展,文學家組成「臺灣文藝聯盟」、藝術家組成「臺陽美術協會」還有青年音樂家集結的「鄉土訪問音樂會」等等,都在三〇年代中期前發光發熱。
二〇年代風華長期遭湮沒
不過可惜的是,二〇年代的思想與社運、三〇年代的藝術文化都如此精彩,卻因為日中戰爭的關係而突然斷絕。二戰之後,相繼而來的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這些文化思想的遺產,又再度遭到無情的清算。直到七〇年代的「回歸現實」之時,遺失的文協精神才逐漸被一片片拾回、重新拼湊起來。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很多人在提及1927年文協分裂的時候,會說文協分裂成左派跟右派,而右派又分裂成自治派的林獻堂與中間偏左的蔣渭水。其實這是很奇怪的想法,因為當時的人們並不會預設自己是左派右派,例如文協分裂的時候被劃為右派的蔣渭水,後來組織「臺灣工友總聯盟」,協助全臺灣共65個勞工團體、將近八千名勞動者進行抗爭。
而且在1924年,二林地區由李應章醫師出面組織農民,反抗林本源製糖會社的剝削之際,身為大地主的林獻堂也有到二林為農民演講,當地農民還敲鑼打鼓,如同廟會一樣的熱烈歡迎他的到來。而共同組織二林蔗農的詹奕侯與劉松甫等人,其實也都是地主出身。所以我們區分文協內部誰是左派誰是右派,其實是沒有什麼必要,重點是成員各自的路線主張,與人格特質。
比較接近現況的,反而是日本警察暗中做出來的調查,警察在內部報告〈臺灣文化協會對策〉裡提到:文協粗分成「溫和派」跟「激進派」。溫和派底下又分成「合理派」(建制派)的林獻堂與蔡培火,以及「穩健社會主義者」的陳逢源及謝春木;而激進派則分成三派:「民族自決派」有蔣渭水跟王敏川、「無政府主義派」的連溫卿與彭華英、還有「妄動派」的無產青年。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以日本警察的角度來看,文協的分裂,主要差異是路線的激進程度,不見得是支持社會主義與否的原因。
百年前文協的掙扎與分裂,應該是我們當代臺灣人要不斷借鏡與反省的歷史。如果我們是1927年的連溫卿、蔣渭水、蔡培火,我們該踩上哪一條路線?該如何組織?百年文協的故事,不僅需要我們紀念,更需要我們深思。
作者江昺崙:台灣社會運動人士,現任職於國立台灣文學館。
著作:
《實踐哲學:青年讀史明》(合著)
《島國關賤字:屬於我們這個世代、這個時代的台灣社會力分析》(合著)
《這不是太陽花學運:318運動全記錄》(合著)
《濁水長流:濁水溪社十週年紀念專書》(合著)
《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合著)
轉載自思想坦克

百年文協的故事,不僅需要我們紀念,更需要我們深思。圖為文協百年紀念活動主視覺亮相。 圖:文化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