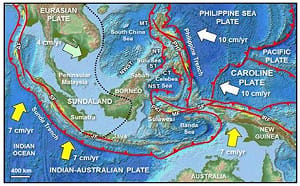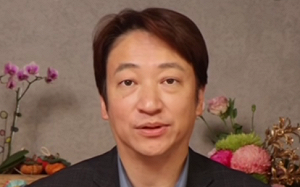在這個價值錯亂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講述自己的故事,以獲得嶄新的身份,找回有意義與價值的位置。這部小說藉由一個徬徨的青年作家,為了解封性愛的苦悶和對生命的探求,得到一個老政治犯的思想啟迪,從此走出思想的困境,進而了解底層人物的心聲,揭示存在於臺灣社會內部的禁忌和荒誕面相。同時,這也是由壓抑的性愛通往政治思想解放的現代喜劇。
第三章 無神論者的視界
祕辛總有個恐怖的開端
「衛國兄,事情不能這樣講,」賀蒙特不贊同童衛國的說法,「格雷特吳今天淪落到這個地步,並不是他自願的,如果我們換個角度設想他的處境,就會得出不同的觀點。」
童衛國的臉色掠過一抹冷笑,對於賀蒙特的辯解不以為然,「你替他找理由說項,當然,就會有不同的看法。再說,我們對他的幫助也不少……」
「你是指代墊電費和水費嗎?」
「……」
「我們不應該計較那點小錢的。每次我去找他聊天,就會順便帶點食物過去。其實,我的經濟情況並不寬裕,但是能力所及偶爾會塞點鈔票給他,贊助他的生活。」
「你太傻了。他拿了錢,就去買酒喝,」童衛國說得振振有詞,「我們透過赫大頭的關係,好不容易幫他找了個畫廊的差事。可是,他卻三天兩頭不待在畫廊,老闆看不下去了,好多次向赫大頭抱怨,說他簡直就是個冗員。」
「他是冗員?這話太污辱格雷特吳的專業了吧。」賀蒙特憤憤不平地說,「這種說法就是不折不扣的歧視!不是嗎?他曾經當過美術專校的講師,有著豐富的作品,畫廊老闆憑什麼這樣說?」
「你這樣辯解未免太極端了。支付薪水的是畫廊老闆,誰掌握支配和分配的權力,就等於他掌控全部的權力。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當然有權向怠忽職守的員工問責,即使他擔任經理的職務,總是要做出與其薪水相符合的事情吧。」
乍聽之下,童衛國這個說法好像引自馬克思的資本論,至少是站在資本家或工廠老闆的立場發言的。然而,賀蒙特不禁有個疑問,平時童衛國標榜著站在普羅大眾的立場上,為廣大的無產階級爭取最大的權益,要為底層弱勢的人群仗義執言,但現在,他卻悄悄地站在對立面來指責格雷特吳。這又是什麼心態呢?在童衛國的想法中,難道矛盾和悖論可以同時並存嗎?
就格雷特吳的上班情況,賀蒙特比童衛國更為理解,甚至知道更多因白色恐怖而來的恐懼。最初,格雷特吳到畫廊上班是非常賣力的,一有顧客上門看畫,他就恭順地立在一旁,等候顧客們的詢問,對於顧客向他詢問畫作的問題,他以專業畫家的視點予以解答,加上他待客親切服務熱忱,贏得許多顧客的好印象。畢竟,他比任何人體悟到,這是他出獄以來,第一份正式的工作,豈能不好好珍惜呢?總而言之,他不會也不想自毀前程。然而,有些不可抗的突發事件,強行改變了人性的規則。
「我聽童衛國說,你三天兩頭不去上班,真有這種事嗎?」賀蒙特劈頭問道,「你能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哎,老弟,你以為我是拿錢不辦事的人嗎?」
「不是,我相信你的人格。這其中有什麼曲折……」
「嗯。」格雷特吳閉上眼睛,彷彿正在排除橫亙在他面前的夢魘似地說,「這件事情,我一直憋在心裡,再不把它說出來,你可能要誤解我了。」
「我想也是,你就說出來吧。」
格雷特吳要揭開這往事序幕之前,向賀蒙特提出小小的要求,先讓他喝兩杯酒放鬆心情,否則接下來漫長的敘述很可能因緊張和莫名的恐懼而告中斷,甚至陷入記憶混亂的境地。在好朋友的面前,他不希望自己連回溯記憶這種小事,都被他給搞砸了。
格雷特吳說,事實上,他非常喜愛畫廊的工作,並且把那個地方視為他的人生避風港。但是,他上班第二個月的時候,在畫廊內部和畫廊外面,陸陸續續開始發生了怪事。一個陰鬱的午後,有兩名中年男子,一前一後走進了畫廊。看上去,他們沒有展現出藝術愛好者的舉止,不像是來買畫的,而且觀看畫作的時候,也不怎麼專注和投入,有點馬虎或者隨便看看。格雷特吳心想,如果對方只是一時興起,抱著好奇的心態藉此打發時間,倒是不必在意,但事情偏偏往相反的方向發展。那兩名男子始終板著面孔沒說半句話,兩隻眼睛看似盯著畫作,做出欣賞的樣子,但格雷特吳發現,他們眼睛的餘光卻是射向他來的。說得形象具體些,在偌大的畫廊裡,他們倆的餘光如同冰冷的光束,直指他所在的位置,彷彿要洞悉他全部的心思。而這個不為人知的情節,正在悄悄地進行著,正在逐一地拆除他所有的心靈防線。
任何有膽量的人,遇到這種森然視線的進犯,恐怕也要感到害怕和退縮的。而且,格雷特吳向來是心思細膩的人,也是神經衰弱的人。他坦承,這種氣氛已經讓他感到恐懼了,可以說是始料未及的衝擊。但話說回來,他又能做些什麼呢?首先,他沒有理由把他們倆從畫廊裡趕出去,也不能直問他們倆的真正目的;其次,他沒有黑道兄弟的膽量和手段,運用巧妙的黑話套出對方的企圖,然後抬起手臂搭在他們倆的肩膀上,宛如對待多年故友那樣將他們倆擁送到外面,以解除不安的威脅。
如影隨形的黑霧
「後來,那兩個傢伙怎麼離去的?」
賀蒙特表示關心,因為他之前有類似的經驗,他與伊謨尼斯基造訪哥達拉斯的時候,拾階前往他公寓的樓梯間,正巧與那個大肚腩特務人員撞個正著,雖然他們當場沒發生正面衝突,倒是嚇出了一身冷汗,半晌說不出話來。所以,依照他的判斷,格雷特吳描述的那兩名陌生怪客,不是來畫廊進行監視,就是透過跟蹤給這畫家施加心理壓力的。
「他們自始至終一聲不吭,不正面看我一眼,不問我畫作的售價,」格雷特吳的聲音有點顫抖,「……這讓我更感到恐怖了。誇張地說,在我眼裡,他們倆不是兩個生人,而是兩條具有人形的鬼魂。他們不是來向我索命,而是用行動的沉默之浪試圖淹沒我的靈魂。」
「他們沒有向你動粗吧?」
「沒有。」
「結果呢?」
「他們約莫待了四十分鐘左右。臨走前,彼此交會了一下眼神,自行推開大門,就揚長離去了。」
「你追出去了嗎?」
「當然不敢,我哪來的膽量啊。而且,他們若察覺到我竟然追了上去,萬一惱羞成怒來個大反撲的話,我可就慘了。」
「你怎麼做呢?」
「他們走出大門以後,我佯裝在大門口擦拭玻璃,這樣才不會顯得突兀。但在這時候,我卻發現了另一個祕密。」格雷特吳嚥了一下口水說,「簡直太可怕了。」
「咦?」
「外面竟然還有兩名怪男子!」
「他們是同路人嗎?」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同路人。他們四個人並沒有任何交談,但卻有交換某種訊息的可能。這一點,即使我眼拙也看得出來。如果有人問,政治犯有什麼能耐的話,我會告訴他,政治犯的天生體質,就是本能地探知監視和跟蹤行動。你可以說它是一種政治過敏症,一種對於使其人格消失的本能的反應。」
「所以,你才沒正常上下班,是嗎?」賀蒙特問道。
「嗯,」格雷特吳陷入了沉默,接著打起精神說,「賀蒙特,我們是老朋友,我不想對你說假話,我著實害怕坐牢,無論如何都不想重返監獄裡。坐牢的滋味,就像是煉獄之火在拷問你,它用漫長的時間刑求你,直到把你的靈魂打得扭轉變形。」(未完待續)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我的書鄉神保町》1-10卷(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