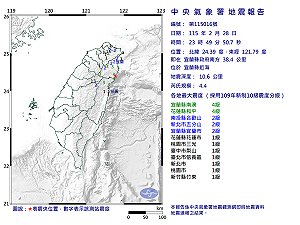中國中央電視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拍攝了電視連續劇《太平天國》,卻受到觀眾的冷遇,創下了最低的收視率。究其原因,除了劇情進展的拖沓和演員演技的低劣以外,更重要的還是編劇和導演沒有以嶄新的視角來審視歷史煙雲。電視劇一會兒采取“階級分析”的立場,一會兒又支持儒家“忠孝”的觀念。一邊大肆地美化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因為洪楊代表著“進步”的農民階級;另一邊又著力打造作為“中興名臣”的曾國藩的偉大形像,因為曾國藩是毛澤東贊揚過的人物。如此“騎牆”的立場和如此陳舊的觀念,使得整部電視連續劇彌漫著一股腐屍般的氣味。
其實,無論是起義的太平天國軍隊,還是以曾國藩湘軍為核心的“平暴力量”,都是殘害老百姓的劊子手。“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千百年來,中國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沒有選擇統治者的權利,“長毛”來了,拉男人去當炮灰,拉女子去奸淫;湘軍來了,同樣是拉男人去當炮灰,拉女子去奸淫。洪秀全不會愛惜百姓的生命,曾國藩也不會愛惜百姓的生命,雖然他們是對立的雙方,但是在建立或者維護專制制度上他們卻有著驚人的一致性。老百姓從來都是“沉默的大多數”——即使是今天拍攝電視連續劇的導演和編劇們,也不過是把數以萬計的“群眾演員”當作戰場上營造浩大陣容的工具罷了。
現正最夯:美以聯手轟伊朗!中國外交部發聲:立即停火、恢復談判
電影《太平天國》如何刻劃曾國藩?
我在《太平天國》中看到了這樣一個精心設計的情節:當六弟曾國華戰死之後,曾國藩哀痛得幾天吃不下飯。陳玉成致信曾國藩,要求只帶一名隨從會面,在會面時交還包括曾國華在內的三名清軍將領的屍首。曾國藩本著對兄弟的愛和對朝廷的忠,不顧手下的勸阻,毅然赴約,實踐了蔡鍔所編《曾胡治兵語錄》中的名言——“‘不怕死’三字,言之易,行之實難,非真有膽有良心者不可”。這不正是偉大領袖所贊賞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嗎?電視劇反復渲染曾國藩失去兄弟的痛苦和單刀赴會的勇敢,仿佛這樣一來,人物的形像就豐滿了、有血有肉了、立體化了。不可一世的湘軍領袖也是人嘛!
實際上,曾國藩所體現出的是一種極其虛假的“溫情”:一將功成萬骨枯,他只會為自己親人的死亡而悲痛,卻絲毫不顧及兩軍對壘時沙場上戰死的千萬名士兵,以及被他的軍隊血腥屠殺的普通老百姓。電視劇一味關注和凸現前者,故意掩蓋和漠視後者,正說明編劇和導演缺乏基本的人文主義的素質和人道主義的情懷。他們雖然生活在現代,但靈魂卻深陷在古代專制主義的泥沼之中。
全站首選:川普下令「史詩怒火行動」轟伊朗 國會炸鍋:未經授權開戰?
史學典籍裡的曾國藩
前些年,唐浩明所著厚厚三卷本的《曾國藩》風靡大江南北。就文學成就而言,雖然《曾國藩》尚不能與高陽這樣的歷史小說大手筆相比,但在國內的歷史小說中顯然是鶴立雞群。但是,該書走紅的更大原因,乃是因為其主人公是曾國藩(後來,唐浩明所著之《曠代逸才》、《張之洞》等書,雖然在藝術上有所進步,但發行量卻無法與《曾國藩》相比)。由這個小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曾國藩的為人和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近現代歷史,尤其是近代以來文化階層和政治人物的人生取向。因此,要了解近代以來的中國,不可不了解曾國藩——曾國藩可謂是一把“鑰匙”。
美國學者孔令飛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一書中指出:“曾國藩和他的圈子受到了一種強調自我修養及社會活動論的有活力的清教主義的激勵。”這正是後來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對曾國藩痴迷的主要原因。曾國藩堂前殺俘虜,堂後讀《論語》,兩者可以融為一體。近代以來的若干政治人物也一樣——他們的權謀與刻毒,他們口頭上的愛民如子與骨子裡的視人命如草芥,顯然都是繼承了曾國藩式的偽善。
文學作品裡的曾國藩
老詩人流沙河寫過《可怕的曾國藩》一文,他以自己當了幾十年“牛鬼蛇神”的豐富閱歷,看透了這個“中興名臣”的種種“可怕”之處。在所謂的“溫情”背後,是刀鋒一樣的慘刻嚴酷;在浩然的正氣背後,是狗一樣的奴顏卑骨。曾國藩屬於那種“厚黑”到了“無形”境界的家伙,天天念叨著“現在但願官階不再進,虛名不再張,常葆此以無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之類的“真理”,而他心裡究竟在想些什麼,連他的弟弟曾國荃也琢磨不透——曾國荃有時不禁感嘆說,這個活生生的“聖人”難道真的是我的親哥哥嗎?
易宗夔《新世說》中有“曾國藩氣量宏大”一條:“曾滌生未達時,讀書岳麓書院,與某生同居。某生性褊躁,其書案距窗可數尺。公因置案窗前以取光。某怒曰:‘吾案頭之光,全為汝遮矣。’公曰:‘然則令我置之何處?’某指床側曰:‘可置此。’公如其言。中夜讀書,某又怒曰:平日不讀書,此時乃擾人清睡。公為之低聲默誦。後治軍,從容談笑,有雅歌投壺氣概,日必圍棋一局。前敵交綏,或遇小挫,亦無太息咨嗟之狀。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對此,流沙河評述說:“這家伙,上承三省吾身的祖訓,下開自我批評的先河,時刻不忘修身養德,恨抓自己活思想,狠鬥私字一閃念,堪作樣板。”從王莽、劉備到曾國藩,中國文化盛產這類“聖徒”般的“奸雄”。當虛偽成了一種日常狀態的時候,偽善者也就享有了聖人的名聲。
曾國藩與儒家精神
雖然曾國藩對儒學理論的發展沒有作出太大的貢獻,但他“活出了儒家的真精神”來。這是什麼樣的一種精神呢?首先是無條件地捍衛專制秩序,忠心耿耿地將自己當作專制制度中的一顆“螺絲釘”。流沙河窮形盡相地描述道:“這家伙,可以說是無限熱愛本階級地最高領袖道光皇帝上。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欣逢皇太後壽辰,他以新任翰林院侍講學士的身份,同滿朝文武跪在一起,抬頭有幸目睹龍顏(其實看見的是給太後跪拜時高聳的龍臀),立刻想到咱們皇上春秋已高,種起種子來仍然強壯,六十一歲那年種出了八阿哥,今年六十四歲又種出九阿哥,可見‘聖躬老而彌康’。又目睹‘七阿哥僅八歲,意騎馬雍容,真龍鐘氣像’。
這些都是特大喜訊,宜函告家人,以分享幸福。如此忠愛老龍,如此慕愛小龍,難道不可怕?”中國數千年的帝制一直沒有中斷,其重要的支撐力量就是曾國藩之類的儒生。他們以皇帝的好惡為好惡,以皇帝的得失為得失,偶爾也寫兩首關心民生疾苦的詩篇,那也是為了鞏固帝國的權柄,“穩定”永遠壓倒一切。
其次,他們在爭奪權力和鎮壓反抗等方面,卻表現得比野獸還要野蠻和凶狠。像曾國藩這樣的“儒學大師”,天生就會“變臉”的絕招,根本不用再向川劇演員學習。同是易宗夔之《新世說》中有“曾國藩智斬叛將”一則,記述道:“曾滌生治軍時,午膳後,必邀幕客圍棋一局。一日,忽有告密者,謂某統領將叛矣。其人即某統領之部下也。公怒曰:‘汝誣上官反,罪當死!’命斬以循,著棋如故。頃之,某統領來謝,公召之入,某頓首曰:‘幸公知我,否則殆矣。’公變色,命左右立斬之。幕友皆諫,謂:‘某果叛,則告密者不宜斬;既知其誣而斬矣,何又斬某統領乎?’公笑曰:‘非汝輩所知也。’亟命斬訖,謂幕僚曰:‘告密之言確也。然非斬告密者,某統領且立叛,故誘其來而斬之。’蓋某統領本捻匪投誠者。此舉雖過於殘忍,然悟事之敏捷,亦有足多者。”
連基本傾向是贊賞曾國藩的記述者易宗夔,也嘆息“此舉過於殘忍”。可見,在中國要成就“大事”,必須先將自己鍛煉成沒有愛心、殘酷無比、翻雲覆雨的人物。他人的生命在曾國藩那裡輕如鴻毛,人僅僅是他的計謀中的一個環節罷了。人是手段而非目的。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邪惡的地方。
讀完曾國藩的家書和日記,流沙河感慨萬分地說:“這家伙,體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學辦實事,玩《莊子》以寄閑情,由封建文化培養見識,從傳統道德汲取力量,也許厲害就厲害在這裡吧?”正因為這樣的原因,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諸多政治人物(包括政治立場截然對立的國共兩黨的最高領袖)都不約而同地表示“獨服曾文正公”。不管他們口頭上宣揚何種塗抹上現代油彩的主義,他們的政治方略和生命形態都深深地打上了曾國藩的烙印。
曾國藩於電視劇之形象
電視劇大力吹捧曾國藩的謀略,卻對其假道學和殘忍的一面毫無涉及,其思路與二十世紀那些身體生活在現代、思維卻停滯在古代的政治領袖是一致的。曾國藩曾經大談:“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為要結粉飾之文。”但湘軍所到之處,與太平軍一樣荼毒百姓、殺戮不止、血流成河。無論曾國藩如何“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宣稱自己“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但百姓們眼睛卻是雪亮的。百姓們也許連大字也不認識一個,他們卻能認清這名儒學大師的真面目。老百姓給曾國藩起了個極其生動的外號——“曾剃頭”。也就是說,曾國藩屠殺的老百姓就像剃頭匠剃掉的頭發一樣多。
電視劇的編導們基本上都是一些不讀書的、也沒有任何價值堅守的文人,他們異想天開地塑造了一個“人情味”的曾國藩,並且還因此洋洋得意。電視劇將最沒有人性的人打扮成最有人性的人,其後果將是嚴重的。中國的許多年輕人抱著翻譯成白話的曾國藩的文字閱讀,學習他的工於心計和道貌岸然,模仿他那比海還要深的城府和比冰還要冷的心靈,以之來應付現代社會激烈的競爭。他們也許會成功,但他們喪失的將是做人的尊嚴、生活的幸福和聯結人與人之間的基本紐帶——“愛”。以泯滅人性和殘害生命為代價獲得“成功”,值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