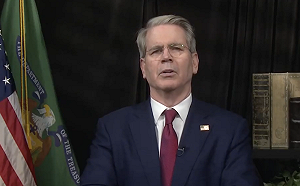在全世界範圍內,西藏是一處最不為人所知的區域。雖然青藏鐵路開通之後,每天增加了數以千計絡繹不絶的遊客進入西藏,布達拉宮的接待能力也受到嚴峻的挑戰;雖然在拉薩繁華的街道上,可以輕而易舉地吃到海鮮和各種西式大餐,可以買到巴黎剛剛上市的時裝和香水,但一般遊客所看到的西藏,只是西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只是一個五光十色的櫥窗。在櫥窗的背後,有些什麼呢?
在西藏,仍然矗立著一道高高的「柏林牆」。當年,阻隔西德和東德的「柏林牆」並沒有像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所期望的那樣「千年永不倒」,在雷根總統「戈巴契夫先生,推倒這道牆吧」的呼籲中,在千千萬萬渴求自由的民眾的詛咒中,柏林牆一夜之間轟然倒塌。今天,在西藏這片世界上最大、也最具傳奇色彩的高原的四周,仍然存在著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柏林牆」。這道高牆的受害者,不僅是世世代代生於斯、長於斯的藏族人民,也是所有的中國民眾。
普通的中國人比世界其他任何國家的人都更加不瞭解西藏,「柏林牆」牢固地豎立在他們的頭腦之中。一說起西藏,他們便認為這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曾經盛行殘酷的奴隷制度,布達拉宮是用奴隷的骨頭堆砌起來的,是漢族給西藏帶去現代文明和現代生活方式;中央政府長期以來給予西藏巨額投資,西藏人理應感激不盡;達賴喇嘛是一小撮分裂主義分子的頭子,是西方利用來反華的工具……這就是中共當局通過長期的教育、宣傳和洗腦,而讓普通民眾形成的既定觀念和思維方式。即便某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已經在西方生活很多年的人士,亦從不懷疑以上種種說法的真實性。幾年前,我在洛杉磯華人作家協會為我組織的一次演講會上,就遭到過兩位自稱北大校友的人士的猛烈攻擊,他們的名片顯示他們在美國某大學任教,可他們對西藏的看法跟中國大陸中學教科書上的那一套一模一樣。愚昧已經成為一種難以醫治的慢性病。
推倒西藏的「柏林牆」,第一步便是讓藏人自己開口說話,便是傾聽藏人自己的聲音。阿媽阿德的回憶錄《記憶的聲音》,便是這樣一部跨世紀的西藏悲壯史詩。阿媽阿德是一個平凡的藏族女子,1932年出生於康區梁茹。50年代初共產黨軍隊進入藏區的時候,她還只是一個新婚不久的少婦,相夫教子,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然而,當共產黨開始系統地摧毀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的時候,引起了藏族人民的反抗。阿媽阿德先後失去了父親、丈夫、兒子、婆婆、姐夫和無數的親人朋友,她本人也因為給抵抗組織通風報信而被捕入獄將近30年,在獄中受盡酷刑的折磨,可謂九死一生。1985年,她輾轉來到印度達蘭薩拉,並在美國「女兒」佈雷克斯莉的幫助下,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這本杜鵑啼血般的回憶錄。正如作為記錄者的佈雷克斯莉所說的那樣:「像多數藏人一樣,阿媽阿德沒有受過正式的教育。因此,她的故事讀起來更像豐富多彩的口頭敘述,而非精雕細刻的文學作品。」但是,也正因為如此,這部回憶錄以驚人的真實性和樸實無華的風格,而成為藏族當代歷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阿媽阿德是一位幸運的倖存者,她的許多同代人都慘死在戰鬥中以及此後漫長的集中營生涯中。倖存是一種幸福,是一種不可以揮霍的幸福,倖存者有責任講述記憶,並竭盡全力讓記憶成為歷史,達賴喇嘛在給這本回憶錄所寫的序言中指出:「我很高興,不僅是為人們可以讀到阿媽阿德的故事,而且也為她能在苦難中活下來,把自己的經歷告訴世界。這個故事體現了中共佔領西藏後,所有藏人如何受盡折磨,也體現了西藏婦女如何像男人一樣做出犧牲,投身正義和爭自由的戰鬥。正如阿媽阿德自己所說,這是一種聲音,一種令世人記住那些失去生命的受難者的聲音。」毫無疑問,這也是一本值得推薦給每一個中國人閲讀的書,它能夠打破共產黨炮製的虛假的「西藏觀」,能夠喚起有良知的漢族人士重新審視當局的西藏政策並重新看待相處了上千年的藏族鄰居。
當共產黨軍隊剛剛進入藏區的時候,大部分藏人都持觀望態度。這支陌生的軍隊比此前的國民黨軍隊顯得更加威武、整齊、富有朝氣。阿媽阿德回憶說,在共產黨進入藏區的最初階段,「士兵們沒有動過任何武力,也從沒有威脅過我們。……中國士兵儘力做各種演講,以模範行動贏得我們的信任。」她的回憶是真實的,她並沒有刻意扭曲事實。她特別指出,當時共產黨幹部和士兵對藏人的佛教信仰表現出了一副虔敬、虔誠的樣子。而藏人根本不知道,為了贏得他們的信任,研究他們的宗教和習俗,已成為共產黨軍隊的軍事訓練的一部分。共產黨軍隊在這一階段的「秋毫無犯」,僅僅是為了麻痹藏人而已。
很快,共產黨便在藏區展開了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這是他們粉碎藏人的社會組織結構和歷史文化傳統的一招殺手鐧。阿媽阿德發現,共產黨逐漸重用一些「根正苗紅」的乞丐,將他們提拔為各種領導機構中的傀儡角色。她寫道:「中國人確實影響了一些乞丐和窮人。那些乞丐,以前沒有人阻止他們過自己選擇的生活,而且還一直慷慨地接濟他們,可就在大家最需要他們的時候,卻背棄自己的人民。看到這些,真令人無比痛心。……乞丐們接受任何任務之前,都要被灌輸共產黨的教條,讓他們堅信富有的藏人和當地的頭人是他們的敵人。還說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去監督社會、彙報誰在民眾之間散佈民族主義情緒。」由此,中共將昔日的西藏社會撕裂開了一個口子。
緊接著,共產黨大肆開發西藏,掠奪西藏的各種資源,西藏的自然環境從那個時候開始便遭到嚴重破壞。當然,藏區的破壞是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破壞同步進行的,許多領域的破壞是永久性的破壞。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及其幫兇乃是人類的千古罪人。阿媽阿德在家鄉渡過了田園詩一般美好的童年和少女時代,儘管自然條件惡劣、物質生活匱乏,但他們的精神生活卻充實而富足,他們與自然萬物之間的關係也十分和諧,阿媽阿德說:「在藏人眼中,大地是有生命的。土壤、高山、河流和天空諸神呵護著大地,滋養著大地。我們的文化一直追求與環境的完美和諧。我們只種那些我們需要的,這足夠了。在共產黨身上,我們看到的只有貪婪。現在,他們似乎計劃開墾所有可利用的土地,養活他們的軍隊。」今天青藏鐵路的修建,也是出於同樣的貪婪。西藏的一草一木,惟有無聲地哭泣。
阿媽阿德所在的康巴地區,民風最為剽悍,當時的反抗運動也最為激烈。然而,面對裝備精良、多如蝗蟲的共產黨軍隊,數量有限的藏人單憑勇氣和體質與之對抗,宛如以卵擊石、螻蟻撼樹。「人們發現藏族戰士死去時,仍緊緊地握住手中的藏刀,那麼緊,那麼用力,手都變成了黑褐色。」不久,阿媽阿德也被捕了,並且受到種種酷刑的考驗:「審訊的警察開始對我動粗,一連四天我都戴著手銬,手還被拷在後面,他們拚命往我大腿上踢,腿上腫了一大塊,過了39年後還能感覺得到。」
還有更可怕的酷刑在等待著她:「有時他們扯我的頭髮,有時拉我站起來,強迫我跪在削尖的木片上。有一次,他們把竹籤楔進我食指的指甲蓋兒下,把指甲下的皮肉都撕裂開了,一直裂到第一個指關節。他們把竹籤子慢慢地往裡插,想要強迫我交待。我眼前浮現出一張張家人和朋友的臉孔,現在已經很明白,如果我開口,這樣的逼供就會沒完沒了。最後我疼得昏死過去。」這位信仰堅定的女子,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從未出賣和揭發過別人,從未背叛自己的民族,從未向毛澤東像表示效忠。當她出獄的時候,已經由一名鮮花般的少婦變成了傷痕纍纍的老人。
這些章節讓我不忍卒讀,同時我也為自己身為漢人而感到羞愧。近代以來,藏人不曾侵犯過漢人;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後,藏人也從未試圖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可是,毛澤東卻要徹底征服並按照他的方式改造西藏,不惜為之付出血的代價。在通常情況下,殺戮是有理由的,可是中共政權對藏族的殺戮卻毫無理由。如果硬要找出理由的話,也許就是因為毛個人瘋狂的野心。毛澤東政權對西藏人的種族屠殺,雖然數量上沒有達到希特拉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但性質完全是一樣的。
此前,我們對此罪惡一直缺乏清晰的認識,我們譴責毛澤東發起的種種政治運動以及大饑荒造成數千萬人死難,卻很少對藏族的悲慘遭遇表示同情。我們的人權觀和自由觀是有選擇的,是有缺陷的,我們自己卻從未意識到這一點。直到今天,西藏在中國年輕一代的「小資」心目中,僅僅是一個「香格里拉」一般的夢幻之地。在各種小說、遊記和攝影作品中,西藏常常被當作浪漫的愛情故事的最佳背景和對平庸的日常生活的一種反動。因此,那一切懷著「獵奇」的心態的、以西藏為題材的漢語文學,在阿媽阿德的這本回憶錄面前,都黯然失色,都輕得失去了重量。
每個民族都需要見證者,尤其是那些被殺戮、被侮辱、被漠視的民族。大屠殺見證者、華盛頓大屠殺博物館的創始人、作家韋塞爾於1986年獲諾貝爾和平獎,頒獎者稱他是「人類的信使」,讚揚他記錄下了「在人類遭受極大羞辱和徹底蔑視時的個人經歷」。韋塞爾把保存苦難受害者的記憶當作自己的使命,他說:「歌德說,人在悲痛時會沉默,這時候,上帝便把歌唱悲傷的力量給了人。從此,人再也不可能選擇不歌唱。……我為什麼寫作呢?為的是受害者不被遺忘,為的是幫助死者戰勝死亡。」如果說韋塞爾是猶太民族的見證者,那麼阿媽阿德便是藏族的見證者。最為可貴的是,在經歷了地獄般的勞改生涯之後,她仍然保持了人類的尊嚴、寬容和慈愛,她並不憎恨那些對她施加過暴力的人,更不試圖尋求報復。她對西藏被戕害的命運深感悲傷,卻不主張用激進的方式尋求獨立,她在回憶錄的結尾處呼籲說:「願人們認識到和平是這個世界不可或缺的空氣,願人們都能理解紛爭不可能靠武力來解決。」可惜的是,迷信武力的、傲慢的北京當局根本不願聽取達賴喇嘛和阿媽阿德們真誠而富有建設性的呼籲。
這是一本記憶之書,這是一部法庭的證詞,阿媽阿德不是熟悉遣詞造句、學識淵博的作家和學者,她的這本口述回憶錄卻具有特殊的文學和歷史價值。學者徐賁在《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一文中指出,大屠殺倖存者的見證為其它災難見證設立了重要的先例。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亞歷山大稱災難倖存者的見證為「一種新的歷史憑證」,稱作見證的倖存者為「一種新的歷史行動者」。韋塞爾也說過:「如果說希臘人創造了悲劇,羅馬人創造了書信體,而文藝復興時期創造了十四行詩,那麼,我們的時代則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見證文學。我們都曾身為目擊證人,而我們覺得必須為未來作見證。」
我相信,阿媽阿德的《記憶的聲音》完全有資格成為世界「見證文學」寶庫中倍受珍惜的作品之一。未來漢族和藏族實現和解的那一天,這本回憶錄將被收藏在歷史博物館中。我們的後人將會驚嘆於自身的歷史中出現過如此黑暗的一頁,更將為我們有過阿媽阿德這樣一位如同「壓傷的蘆葦不折斷」的前輩而感到自豪。

阿媽阿德的回憶錄《記憶的聲音》,是一部跨世紀的西藏悲壯史詩。 圖:翻攝博客來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