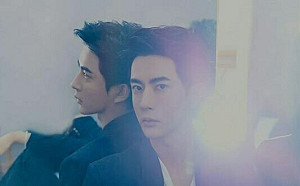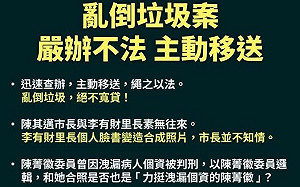在這起非洲豬瘟事件中,「廚餘」原是日常語彙,卻成了防疫體系中最危險的導火線。當社會追問病毒從何而來、責任誰屬時,真正的警訊早已赤裸裸呈現:廚餘,是所有潛在傳播途徑中風險最高的一個環節。而我們這次看到的,不只是病毒的頑強,而是行政制度與風險意識的全面失能。
非洲豬瘟病毒(ASFV)極為堅韌,可在豬肉製品與血液中存活數週乃至數月,冷凍狀態下仍具毒性。這也讓廚餘變成病毒理想的藏身之所。當未經妥善處理的肉渣與血液被倒入豬舍餵養系統,就像一顆外觀平凡、內藏殺機的定時炸彈。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因此要求,廚餘必須在90°C以上長時間加熱或高壓滅菌,處理後更不得與污染源接觸。這不是繁文縟節,而是針對ASFV耐活性的最低防線。唯有達標,廚餘再利用才安全,否則便是病毒直通豬舍的捷徑。
但這樣的標準,在台灣卻往往只停留在紙上。涉案養豬場自六月起,連續四個月未依規定上傳該廠的蒸煮紀錄。更諷刺的是,環境部設有具影像驗證與時間戳記的廚餘蒸煮申報系統,地方政府卻幾乎未監督。制度的眼睛原本開著,卻選擇閉上。
這不只是行政懈怠,而是風險管理的斷線。10月10日該場豬隻已出現異常死亡,中央的化製廠系統早有異常訊號,但地方在四天後仍決定「不採樣,持續觀察」。這不是資訊不足,而是對風險判斷出了錯。在手握紅燈訊號時卻不轉方向盤,錯過了阻止疫情擴大的黃金時刻。
更嚴重的是,疫調發現有11頭病死豬下落不明。ASFV雖然不會感染人,卻對豬群具高度致死性。若這些病豬被非法棄置或流入黑市,病毒就可能透過野生動物、器具或人員擴散。這些「去向不明」不只是行政漏洞,而是活生生的病毒破口。
回頭檢視制度,我們早有完整的數位監控與自動通報機制,但一切都敗在「看見卻不作為」的地方執行。數據可以警醒,制度可以防堵,但唯有人能決定要不要採樣、要不要稽查。因此,這次的災難,不是資料斷訊,而是判斷斷線。
有人辯稱「國外也用廚餘養豬」,但事實恰相反。歐盟早在2002年全面禁止餐廚廢棄物餵養家畜;日本、韓國雖採取技術開放制,但都以高門檻與嚴格監督為前提。台灣若執行鬆散,只會讓「技術容許」變成「風險容忍」。
這次事件不是單一錯誤,而是高風險技術、紀錄掛零與風險判讀失靈所交織而成的結構崩壞。「制度不是沒設計,而是沒使用;資訊不是沒提供,而是被忽視」。防疫最大的破口,從來不是病毒本身,而是我們對風險的輕忽。
當系統長期「看見卻不行動」,高風險就會一點一滴積累,直到壓垮整個體系。那根稻草,也許只是原本該丟入高壓鍋、卻被輕忽的一塊豬骨。這次我們付出了代價;下一次,倘若仍是學不會,恐怕是要付出更大代價。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