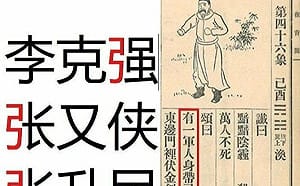台灣光復節一直被視為慶祝中華民國接管台灣的重要紀念日,然而這個節日的正當性卻長期存在爭議。1945年日本在二戰中投降,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命令蔣介石代表同盟國接收台灣,當時台灣仍是日本法理上的領土,並未經正式和平條約明確交還中華民國。因此,「光復」一詞是否適當,還是另一段軍事佔領的開始,值得我們重新檢視與反思。
在此,筆者欲透過美術先驅陳澄波與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兩位民主前輩的經歷,來探討這段光復的意涵。
1945年日本戰敗後,陳澄波因曾在中國上海任教且能口說流利華語,被推舉為嘉義市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副主任,並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隔年代表中國國民黨當選嘉義市第一屆參議會議員,正式踏入政治領域。然而,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他以和平使身份到水上機場與國民政府談判,卻遭軍隊拘捕並槍決,曝屍示眾於嘉義火車站。陳澄波的人生戛然而止,光復後的政治及藝術生命走向悲劇終點。
同一個歷史時間軸上,林獻堂代表台灣人參加南京的受降典禮,出任「台灣光復致敬團」團長,帶領團隊赴中表達對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的支持與期待。隨後他積極參政,當選第一屆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然而,二二八事件及其後國民政府的高壓統治,使林獻堂對政府腐敗、社會動盪及政治鎮壓感到極度失望,期間還曾被視為「台省漢奸」。在國民政府敗退到台灣前,他以治療頭暈等健康理由移居日本,實際是對複雜政治環境的逃避,不願成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林獻堂餘生終老於東京,寫下「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可見其對當時台灣政治亂象已感到絕望且悲憤。
透過這兩位民主先驅的故事,我們見證所謂光復節下的真實血淚與悲劇。台灣從一個殖民政權轉向另一個獨裁政權,社會裂痕深刻,政治迫害殘酷。光復的背後,是無數生命的犧牲與理想的破滅。飲水思源的台灣人民面對光復節,不應單純慶祝,更該正視這段被壓抑的歷史,從中學習,攜手前行,才有可能真正迎向屬於台灣人的公義與和平。
(作者為國小社會科教師)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