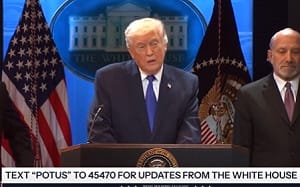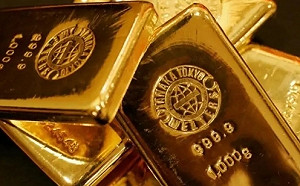《中國時報》刊出一篇投書,批評國防部以三包乖乖紀念抗戰,將之定義為「敷衍」、「政治操作」、「令人髮指寒心」。筆者一方面佩服此番詞鋒的修辭張力,另一方面也忍不住想問:請問紀念的「正確姿勢」,是哪本手冊裡寫的?在當代社會,難道除了石碑、演講與儀式,就沒有其他可以通往歷史記憶的路徑?
歷史,不應只是長者之間的對話
事實上,國防部近年來在抗戰歷史紀念上已持續多元嘗試,包括攝影展、音樂會、口述歷史專案與多場戶外嘉年華,規模與層次遠非三包乖乖所能涵蓋。餅乾包裝只是一種引子,一種以低門檻進入大眾視野的策略。年輕人或許不熟張自忠、謝晉元,但會因一則乖乖限量消息點開簡介,這樣的接觸,就是教育的第一步。
當代文宣,目的不是自我感動
國防部這次的設計若有可議之處,也應落在細節而非形式本身。批評者如果真關心歷史傳承,不妨從「如何做得更好」出發,而不是用感性抒懷包裝成價值審判,將現役軍人的努力一筆抹殺。特別是當發文者本身也是退伍軍人,更應理解:形式創新,並非對傳統背叛,而是對責任的另一種堅持。
歷史需要說服,而不是守舊
抗戰是全體國民共同的記憶資產,不應壟斷於特定語調或世代手中。軍人最懂紀律,也最懂傳承的重量。我們當然可以討論什麼樣的方式最能觸動人心,但討論的前提,不該是質疑同袍的誠意。畢竟,一個社會若只接受單一記憶方式,那才是真正令人髮指的事。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