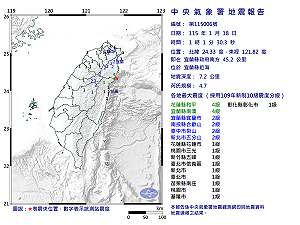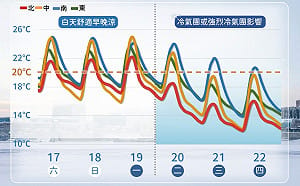我的名字周清月,在很多年以前的臺灣,曾經與宋楚瑜,陳文成這兩個名詞,於新聞報導中,緊緊連在一起。
我曾是美聯社駐臺記者。1981年,我因為報導臺裔美籍教授陳文成的政治謀殺懸案,用了“autopsy”這個英文字,被時任國民黨新聞局長的現任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認為報導不實,取消採訪權達一年之久,而知名於臺灣社會。當時曾有三位無黨籍立法委員,由康寧祥帶頭,在院會中為我向政府提出質詢。
陳文成事件迫使我被美聯社遠調印度,開始我那漫長的國際記者生涯,最后切斷了我與臺灣新聞界之間的臍帶。
我曾應臺灣某基金會之邀,回顧往事,寫了下面的感想:“陳文成的死亡, 也是我的死亡。(當年)的遭遇,對我和他,都是一種不可置信的大玩笑。陳文成不用再夢想人生可能的奇遇,我卻再也無法拾起當年的新聞美夢。”
事情過了快30年,我還是無法完全搞懂,為什麼會因為一個簡單而正確的報導,受到殘酷的處罰。
我離臺往印度工作之前,宋楚瑜在新聞局召見我,並告訴我,一切都是誤會。他並請當時新聞局國際處處長戴瑞明,在來來飯店為我餞行。
1981年發生了兩件轟動臺灣的新聞,我由於報導了官方刻意隱瞞的事實,而導致我被迫離鄉尋求發展。
第一件事是空軍少校黃植誠駕駛F5E戰鬥機從桃園基地飛到中國福州投誠。快降落時,機上的另一位飛行員許秋麟中尉不願投共,黃植誠乃在油量快用罄的情況下,掉頭飛到臺灣控制的東引島,讓許秋麟跳傘,目送他安全下降後,才再飛回福州降共。大陸欽佩黃的義舉及決心,舉起雙手歡迎他。臺灣政府則很快舉行了一場國際記者會,說黃植誠是迷航,非蓄意投降。我有朋友在桃園基地工作,告知此事件的來龍去脈,因此在記者會上發問求證,後來並引用空軍消息來源報導黃是投誠。這個報導,可想而知,繃緊了臺灣當局的神經。
第二件事是比較為人所知的陳文成事件。陳在美國取得統計學博士學位,任教於匹茲堡的卡內基美隆大學。他平時喜歡在臺灣人的聚會中,批評國民黨。在他返台探親期間,被警備總部帶走,後來陳屍於臺大校園。他的死因有謀殺之疑卻一直未能被證實。
我訪問了陳的父親,寫了一篇報導,說陳文成的屍體被兩位來臺調查陳案的美國人驗屍(autopsy)。新聞局長宋楚瑜堅持是"審視” (view) 屍體,非驗屍,要求我更正。美聯社說我是引用陳父之語,非個人意見,無法更正自己。美聯社建議引用宋之語,或訪問陳父或驗屍的美國人,來更正。宋楚瑜不准,雙方堅持不下,宋乃取消我的採訪權。
無黨籍立法委員康寧祥,張德銘與黃煌雄,在院會中提出質詢。那次的質詢,可說是宋楚瑜政治生涯中的處女秀。他通知電視記者到場,在閃亮鎂光燈之下,他大聲說,美聯社的報導是外國殖民主義再度想陰謀操縱中華民國的證明。他誓言將保衛台灣,不讓外國勢力得逞。這樣一來,原本只是簡單的新聞報導問題,卻演變成台灣政府與反對黨以及殖民主義之間的大戰。
三位立委的質詢,可想而知起不了作用。我的父親,在華南銀行當經理,是黨外的同情者,他於臺北王子飯店的日本餐廳請三位立委吃飯,以表達對他們的感激。
被取消採訪權期間,我只能天天到辦公室喝茶看報紙。但是警備總部沒忘記我,派了兩位英俊高大的美男子約我去喝咖啡,百般套我的話,想了解我的想法。我家裏的電話被監聽,行動被監視。我有天與友人去北港媽祖廟散心,數日後,一個雜誌報導,説我去跟媽祖懺悔。
一年之後,新聞局恢復我的採訪權,要求我不得對外發表意見。之后數月,美聯社調我到印度。3年後,美聯社調我回台灣,新聞局卻通知我不得從事記者工作,理由是我的採訪權從未被正式恢復。我只好轉身再出國。
1981年,真是好久以前的事,當年政治的封閉,言論的壟斷,異己的肅殺,已成昨天的夢魘。臺灣人誰也不想,也不會再過那種日子。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