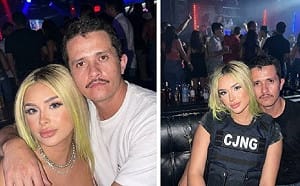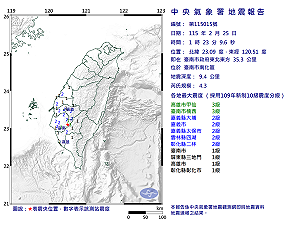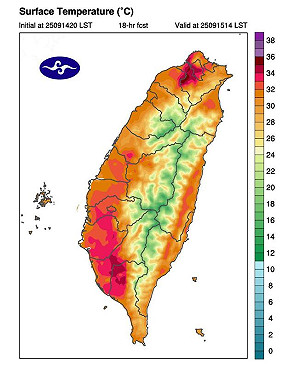《求騙記》最成功之處,在於它讓清代的故事與當代社會產生共鳴。主角金登科的「神算」騙局,在今天看來,何嘗不是各種「假新聞」、「資料造假」的隱喻?村民的盲從,像極了網路時代的集體跟風,而官老爺們的腐敗,更讓人聯想到權力與謊言的共生關係。
國光劇團三十而立推出的經典戲《求騙記》,該劇首演於2011年,原劇名為《神算記》,由福建高甲戲劇作家林戈明參考清代福州地區流傳的閩劇「金登科算牛」故事,如《貽順哥燭蒂》、《神算傳奇》等,重新改編而成。全劇由李超編腔作曲,生旦雙掛頭牌主演者為盛鑑與朱勝麗。當年不僅成功地將地方戲的市井幽默轉化為當代社會寓言,在音樂、表演、文本三個層面,也同時作了一次戲曲現代化的實驗。這部作品札根傳統,大膽創新,為台灣京劇舞台具有突破性的樸實製作之一。
時隔14年,國光再次推出,最大的不同,女主朱勝麗演而優轉任主排,演出棒子交給了後起之秀黃宇琳。談起《求騙記》,故事原型可追溯至清代福州閩劇班社的演出,主角原是一個落魄書生,因生活所迫,借算命行騙維生。傳統版本強調「惡有惡報」的道德訓誡,而林戈明的改編則賦予角色更複雜的心理層次。
當前熱搜:被情婦害到沒命! 墨西哥大毒梟「門喬」行蹤遭鎖定 春宵一度後遭擊斃
國光首演時的文本,經台灣戲曲學者劉慧芬修潤之後,過場情節更具戲劇層次,男主金登科不再只是一個滑稽的騙子,而是一個被時代擠壓的讀書人。他的騙術並非單純為了謀財營生,而是一種對現實的反抗,當社會不再相信學問,也只能用「神算」的外衣包裝一切。戲的潛台詞是藉由「騙」,把真相重新排列審視,直指當代「後真相時代」的荒謬。而金妻也不再是傳統戲曲裡逆來順受的女性,她的機伶與處事態度,映射了現代女性在婚姻與社會壓力下的智慧展現。
李超的編腔作曲是這齣劇最令人驚豔的部分。他打破傳統京劇文武場的框架,大膽融合閩劇元素,創造出獨特的「閩韻京腔」。男主的主題音樂以墜胡和單皮鼓為核心,象徵他「文人表皮,江湖內裡」的雙重性格。唱腔以京劇丑行為基礎,並帶有老生化處理,刻意加入不穩定音高和節奏錯位,表現其心虛與矛盾。如「算牛」一段,他唱的是「西皮原板」,但每句尾音故意「塌調」,模擬江湖術士的虛張聲勢。
女主的唱腔則更富戲劇性,李超把閩劇「哭調」的哀怨旋律與京劇荀派旦角唱腔結合,並在反二黃中融入福州小調,一種近似〈真鳥仔〉襯詞「哎喲喂」的元素,既突顯地域特色,也強化角色的市井氣息。最精彩的是男女主的對唱,兩人調門故意不對等,女主唱傳統閨門旦音域(F調),男主卻突然轉丑角破音(降E調),象徵夫妻關係的價值觀差異。
當前熱搜:「以一敵三」對峙外艦47小時! 西沙衝突 中國稱長沙號主副砲掛彈、導彈通電
盛鑑飾演的金登科,算得上近年台灣京劇較複雜的角色之一。他出身老生,卻演繹一個介於「文丑」和「窮生」之間的角色。他的表演既有老生的沉穩,又帶丑角的狡黠,尤其在「公堂自白」一場,他以「反西皮散板」演唱,聲腔忽高忽低,配合顫抖的身段,將角色的精神崩潰表現得淋漓盡致。
黃宇琳拿捏的金妻角色,相較朱勝麗,完全不遑多讓,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傳統戲曲中的「閨門旦」多屬依附角色,但她賦予了這個角色更深刻的情感層次,尤其唱腔活潑中帶點激憤,表現在生活困頓的肢體語言更為豐富,那種近似面無表情般的詮釋,打破傳統悲情套路,相當具震撼力。
《求騙記》最成功之處,在於它讓清代的故事與當代社會產生共鳴。金登科的「神算」騙局,在今天看來,何嘗不是各種「假新聞」、「資料造假」的隱喻?村民的盲從,像極了網路時代的集體跟風,而官老爺們的腐敗,更讓人聯想到權力與謊言的共生關係。
林戈明的劇本沒有讓故事停留在簡單的道德批判,而是透過主角脫下儒生服,換上術士袍的開放式結局,暗示「墮落迴圈」的無解。這種處理,也讓這齣劇超越傳統戲曲的框架,成為一則關於人性與時代的深層寓言。
該劇呈現的,無疑是傳統戲曲因應時代的翻新,不能只靠簡簡單單加入新科技或改編劇情,而是要回歸在音樂、表演、文本三個層面找出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方式。擁有新創的「閩韻京腔」,演員掌握跨行當演技,加上對社會現象犀利觀察的劇本,讓這部作品成為好看的戲碼。
戲曲,可以傳統、可以前衛、可以札根歷史、可以直面現實,是不必在守舊和逐新之間搖擺,而是應該在每個時代裡找出自己的日月星辰。

國光劇團三十而立《求騙記》男主勝鑑與女主黃宇琳。 圖片:國光劇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