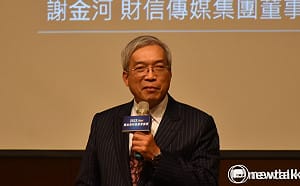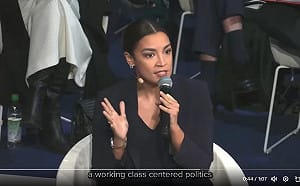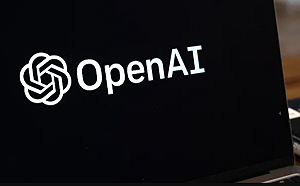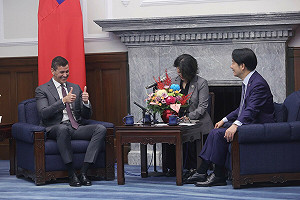本屆立法院的選舉,出現罕見的「矛盾多數」。國民黨在區域選票、不分區選票雙雙落後給民進黨,但卻利用選區的制度缺陷,放大了票票不等值的問題,反而席次上成為第一大黨。這種直接民意落後、轉換為席次卻領先的問題,已經先凸顯了選舉制度的代表性、選區規模落差過大、以及席次轉換的問題。不僅如此,後續的政治效應繼續擴大,國民黨反以「少數選票、多數席次」的矛盾來主導立法擴權的修法,民眾黨也配合演出,成為當前國會亂象的主因。
國會機關代表民意,監督行政是天職,這毋庸置疑。但如果擴權濫權,並且在立法程序上不顧程序正義,這就是另一個層次的憲政問題了。當前的立法院,以選票來看,真正具有「多數民意」的是民進黨,但轉換為席次後,國民黨成為第一大黨,先是在二月民眾黨默許下,就用「少數民意」讓韓國瑜當選為立法院院長。這是選制與選區的問題,在既有的制度下只能選擇接受,並且進一步討論是否該進行制度的改善。然而,「少數民意」取得了立法院院長的職位後,國民黨繼續以「少數民意、多數席次」的矛盾多數,主導了國會擴權的法案。按照目前修法的方向,一旦「少數民意」主導的修法通過,未來立法院勢必成為難以制衡的憲政怪獸。
當前熱搜:中國排擠爛招漸失效!謝金河:台灣在世界貿易舞台終於有顯著位子
以憲政原理來說,行政立法的僵局,在內閣制國家就是進行倒閣或解散,由選民重新選舉來建立行政立法的信任關係。在總統制的國家,行政立法相互分立而且制衡,沒有任何一權可以利用政治權力要求另一權對其負責。即使是分立政府,要進行否決或反否決,也有較高的門檻設計,更不用說沒有利用「藐視國會」以司法手段逼迫行政權讓步的作為。用意就是確保憲政機關之間,依據分立制衡的原理來運作,而不是破壞權力分立的平衡。試問,如果藐視國會成為立法院動輒使用的武器,不只是破壞行政權的專業、施政穩定、甚至要求洩密等詢答過程,造成的憲政動盪、國安問題、立法失職等,又要誰來監督國會呢?
因此,立法對行政的監督,是政治責任的監督,不是把藐視國會司法化成為鬥爭的工具。歐美等先進民主國家,即便有藐視國會的問責設計,對於標準設定一方面相當嚴謹,二方面也多以「提出譴責」為主,也就是讓過程透明之後,交由選民在下次選舉的時候進行政治決斷。
回到立法過程來說,立法委員制訂、修改法律,是另一項天職,本也是立法委員對人民負責的表現。但此次國會擴權的修法過程,我們看到立法委員亂象叢生。這種涉及變更憲政秩序的修法,不僅沒有先嘗試凝聚共識,甚至過程草率,沒有經過縝密審查,用盡各種民粹方式、極大化肢體與道具的表演過程,在充滿朝野衝突的過程中就倉促通過。這是另一個多數暴力的展現,更何況這個多數,還是一個直接民意上的少數,是在制度設計下的矛盾多數。
當前熱搜:派遣第2支航艦打擊群赴中東 川普:未達核協議將是伊朗糟糕的一天
賴總統的就職演說,呼籲國會的政黨競爭,應該要有三個原則:程序正義、尊重少數、服從多數。很遺憾的,目前國會擴權的修法過程,不僅欠缺程序正義,也沒有看到相互的尊重,更在矛盾多數下出現「少數民意霸凌多數民意」的詭異現象。依據當前政黨政治極化、民粹氣氛高漲的情況下,未來這樣的劇碼恐怕會不斷上演。一個失去理性的國會、擴權的國會、矛盾多數下的國會、將成為台灣未來民主憲政運作上最大的不確定性。
我們呼籲,一個矛盾的多數黨應該尊重少數席次的政黨,更何況被霸凌的還是一個民意上擁有相對多數的政黨。而涉及憲政運作的重大法案,在欠缺共識與討論下更不應輕易的表決通過,也不應在沒有充分審議的情況下,以表演的方式草率通過。立法過程需要跨黨派的討論、需要朝野持續的對話,重大的議案更需要社會一定的參與。當前的國會亂象,甚至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這是台灣民主運作的一個關鍵時刻,各政黨要對選民與台灣的民主負責,歷史也將記住這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