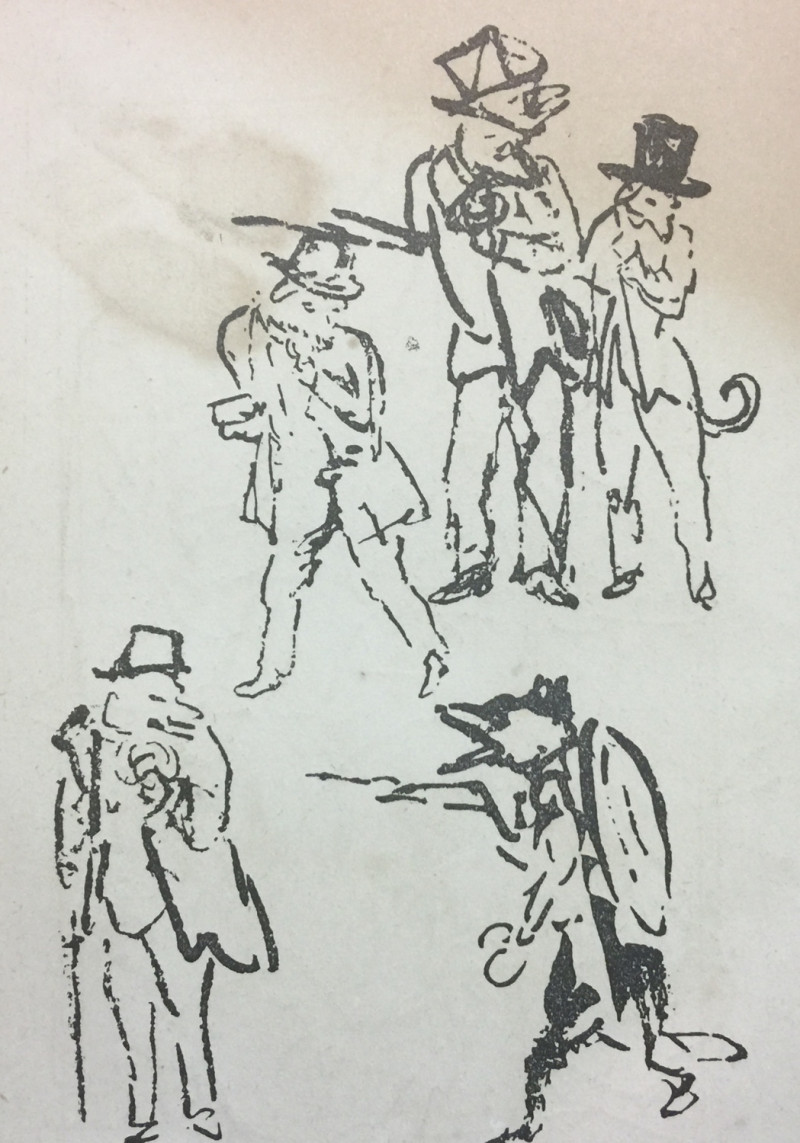引言:左翼除了参與直接改造現實的行動,更急於爭奪歷史思想文化領域的領導權,而傳播精神思想病毒可以有效消滅競爭。
3.
他的左手托住黑狗的下巴,如同牙科診療椅的扶手一樣,給予患者安定的感覺。接著,他的右手搭在黑狗的額頭,然後挪動大拇指,撫摸著牠的鼻樑。這些動作親切又輕柔,讓浸潤其中的黑狗很是享受。過了一會兒,他撫摸的動作停住了。
當前熱搜:美對伊戰爭耗損嚴重! 8百愛國者導彈、11架MQ-9、3架F-15戰機損失
「牠的額頭有一道傷痕,」林曉說道,「而且,骨頭有點凹陷……」
「你終於看出來啦。」大媽嚴肅的神情變得柔和了。
「嗯。」
「你想知道那傷痕怎麼來的嗎?」
「嗯,我想知道其中的原由。」
「好的,仔細聽好,我講完了事情經過,你來評評理,不能置身事外。」大媽試圖用冷靜理性的語氣說,「先說第一件事。去年春天,我拉著四輪菜籃車去買菜。那一次,我採購了很多東西。各式蔬菜和水果自不用說,我特地轉到豬肉攤,買了三斤五花肉、一付豬肝、兩斤絞肉;在熟識的魚攤上,買了一斤花枝丸、兩斤貢丸、兩條鯖魚、一條鰹魚、三條烏賊、兩條白帶魚,準備做出豐盛的菜餚。」
「買這麼多魚肉蔬菜,大媽家裡開餐館嗎?」林曉故意打趣似的問道。
「不是,我家寶貴孫子,剛上小學不久,也許還沒適應新環境吧,最近食慾不佳。他原本就是小個子,可這一折騰,越來越像瘦皮猴了,我這個當奶奶的有責任,做些營養的料理,給他補補身子。」
「我好羨慕啊,」林曉不無欽羡地說,「我出生之後,爺爺奶奶去世了,父母四處打零工,在家時間很少。所以,我從未體驗過這種親情的溫潤,奶奶為孫子烹煮料理……」
「每個人命運不同,有些時候,很難把它說個清楚。不過,命運這種東西,一開始就排定好的,不管好壞,你不接受也不行。」大媽說出自己的人生觀,繼續黑狗闖禍的細節。「那天,黑狗一反常態,竟然朝我的菜籃車撲了過來。牠用力之猛,速度之快,簡直讓我無法反應。如果具體形容的話,牠撲撞菜籃車的樣子,與闖入亂葬崗扖墳的瘋狗沒有兩樣。」
「有那麼嚴重嗎?」
「有,正因為我是受害者,受到嚴重的驚嚇和損失,才能如此理直氣壯地控訴。你不相信嗎?」大媽用銳利的眼神看著林曉,而林曉似乎善意接受她的說法。
「我相信,大媽。」林曉探問道,「……你有沒有受傷?」
「瘋狗的力量很大。我一個踉蹌跌倒在地,左腿膝蓋和手肘破皮了。」
林曉陷入了一種微妙的尷尬。首先,他絕不能替闖禍的黑狗辯解,更不能幸災樂禍地說,哎呀,這只是皮肉之傷嘛 ,很快就是結痂的。其次,他們是不期而遇的對峙。由於他給黑狗餵食牛肉乾,她看不慣出面制止,他們才有了短暫的交集,而現在要他好言安慰大媽,自己也覺得有些勉強和做作。所以,與其說出不得體的話,不如沉默以對,也不算是壞事。
「這麼說來,那輛菜籃車一定翻倒了,儘管它底下有四個輪子。」
「那當然。」大媽憤憤不平地說,「而且,菜籃的搭扣彈開了,菜籃裡的蔬菜、魚、肉品,全掉了出來,散了一地,看得我好心疼。年輕人,你說黑狗的行為,不是很可惡嗎?這不是偷襲什麼才叫做偷襲?」
「是啊,的確很過分。」林曉終於接受大媽對於黑狗的指控。
「我想,在場的目擊者都知道,黑狗原先就預謀犯案的,牠趁我不注意的時候,先把我和菜籃車撞倒,原本鎖在菜籃車裡的魚丸和貢品,就會從透明塑袋裡溜出來,只要它們散落在地上,牠就有絕對的優勢,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們一個不剩地吞下肚。對牠來說,即使散落在地的丸子,沾滿了灰塵和沙粒,牠都會吃得津津有味。」
林曉聽著大媽描述黑狗的行為,分析黑狗如何偷襲致勝的心理狀態,驀然間,湧上了一股莫名的敬意:黑狗因於飢餓的驅使攻擊菜籃車的事情,她為什麼有辦法描述得如此具體而生動呢?莫非,眼前這位大媽是個高人,牠也懂得批判現實主義的手法?這是他所仰慕的左翼精英分子常用的修辭法。
「這麼說來,掉落出來的魚丸和貢丸,全被黑狗吃掉了嗎?」林曉索性問個明白,不再拐彎抹角。
「哈,可以這麼說。」大媽冷笑了幾聲說,「你可以想像,我驅趕牠的時候,情況一定很混亂是吧,剩下兩粒丸子,經過一番折騰,最後狼狽地掉入水溝的孔洞裡。你說,這世界還有比這更荒謬的事嗎?」
「嗯。」林曉說。「可是,黑狗額頭上的傷痕怎麼來的?」
「情況是這樣的,」大媽又恢復平靜的語氣說,「之前,我丈夫就聽里長轉述,住家附近有幾隻野狗,精神不大正常,為了找東西吃,到處流竄串連,有時候也會追趕老弱婦嬬,出門務必小心。那天,我丈夫恰好出來買菸,走到巷口,聽見我被黑狗攻擊,二話不說,折返家裡,抄起一把木劍,往事故的現場奔了過來。我丈夫是個果斷的人。他掄起木劍,毫不猶豫地朝黑狗的額頭劈去,黑狗慘叫了一聲,然後,慢慢地倒下來。我丈夫說,牠倒下的姿勢,像一個蹩腳的臨時演員。」
聽到這裡,林曉有點不以為然了。一個人持著木劍劈打黑狗的額頭,挨打的狗兒已經倒下了,竟然還說牠是拙劣的演技。但換個角度想,作為受害者及其家屬,自然採取這種觀點和說法。
「……牠只是倒下,沒有死掉吧。」林曉問道。
「牠當然沒死,」大媽理所當然地說,「否則牠就不會出現在你面前,津津有味享受著你給的牛肉乾了。年輕人,我看你呀,是個很容易受騙的人呢。」
「怎麼說?」林曉流露出困惑的眼神。
「黑狗倒下了,只是假死行為,一種防禦機制。這種擬傷避險的行為,在動物界裡多的是,連野狗們都學會了這個招式。簡單講,黑狗哀聲地倒下,只是裝死罷了。當牠察覺得制裁者離去,就會登時站立起來,拚命似地逃得老遠,這就是牠們的生存之道。我再告訴你,狗的本性就是恃強凌弱,你不徹底壓服牠,牠根本不把你放在眼裡。而且,狗是沒有尊嚴的概念。」
「所以,牠的額頭才留下那道傷痕?」
「嗯。黑狗做錯事情,本來就應該受到懲罰,否則這社會秩序豈不亂成一通?我丈夫只是給牠教訓一罷了,並沒有取牠性命的打算,」大媽沉吟了一下,似有所想地說,「你看,連狗兒都懂得裝死騙人了,人比黑狗的心思更複雜,欺騙的手法更高段了。你要睜大眼睛,不可被眼前的假象給騙了。」
「那隻黑狗除了偷吃大媽的魚丸和貢丸之外,還闖出什麼禍來嗎?」
大媽說,在那之後,黑狗的確安份了一陣子,以避免木劍嚴厲的訓誡,這是動物的本能,也是趨吉避凶的必要經驗。不過,正如她經常所說,當外部壓力的條件改變了,流浪狗就會恢復野性的本能,完全忘了之前的教訓,又胡亂惹事生非了。有一天,她寶貝孫子下課回家,快要走進巷口的時候,那隻黑狗發神經似的追咬上來。不用說,狗跑的速度比人還快,她寶貝孫子來不及反應,硬生生地被牠撲倒在地,當場哇哇大哭起來。而黑狗顯然是做惡心虛,在她丈夫尚未掄起木劍跑出來之前,這傢伙一溜煙似的逃走了。
「這附近的狗都這樣閙事嗎?」
「不能說全部,但的確不少就是。所以,我才跟你說,不能依眼前的假象做判斷,還得配合長年與狗打交道的經驗,否則倒大楣就是自己了。」
話畢,大媽用複雜的眼神,朝蹲在林曉面前的黑狗瞥了一眼,她似乎無意做出更多的退讓,黑狗也了然於胸,始終保持著低調的作風,不敢與大媽四目交接,更不敢呲聲造次了。也就是說,黑狗比以前變得世故了,比其他狗輩變得聰明了。
「謝謝,我知道怎麼做了。」林曉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從口袋裡取出一個紙條,遞給大媽問道,「對了,請問這地址怎麼走?」
接過紙條之後,大媽看了一下,指了指隔著小公園後面的方向。乍看去,小公園裡有兩三株香蕉樹,碩大的葉子伸得很長,幾乎全被風雨給撕裂了,無精打彩的樣子。此外,就是一些綠色植栽了。看著它們,林曉的腦海中浮現出嘉義鄉下的扶桑花來,那是生機勃然的綠籬,給人一種希望的力量。小時候,他經常和玩伴們跑到親戚家的住家外圍,採摘燈籠似的扶桑花。它們有紅色的和淡紅色的,花型非常美麗。其實,他們不全然是口渴嘴饞,而是因為好奇和好玩。他們摘下花朵,拔掉它的細梗,模仿忙碌的蜂鳥,就著嘴巴吸吮起來,享受著那股淡然的甜味。可惜,那塊小公園裡沒有扶桑花的樹叢。
林曉向大媽道了謝,正要往那個方向走去,忽然間,有個人向他打了招呼:「你是林曉嗎?」然後,朝他緩緩地走過來。
這是他們倆第一次見面。
「嗯,我是林曉。你是楊格嗎?」林曉揮手回應道。
「是啊,我看了看時間,你也快到了,就來這裡接你。」楊格說,「喏,你看,我幫你帶了什麼東西。」
「米酒?」林曉驚訝地說,「你怎麼知道,我喜歡喝米酒?」
「當然知道,我老家開鐵工廠,很了解師傅們的嗜好。而且,這個冬天冷嗖嗖的,簡直快把人凍死了。咱們喝點米酒,多少可以驅寒。」
這時候,大媽看見這位外地青年的朋友來接他了,不需要她繼續說明,聽他們說話也尷尬,便一聲不吭地轉身離去了。反觀黑狗的情況也是。牠看見鐵娘子般的大媽離去了,終於如釋重負似地站了起來,彷彿很世故地理解到,給牠牛肉乾的好人,已有人來接應了,牠也應該退場了。於是,牠猛然一個轉身,迅速地奔向小公園,黑色的身體消失暗處了。
「剛才,你跟那個大媽聊了些什麼?」楊格問道。
「噢,這個大媽真有趣,很特別的人。」
「她怎麼說?」
「一開始,她不客氣地制止我,叫我不要給黑狗餵食,還說那隻黑狗有傷人的前科,要我不可輕忽大意。其實,我只是給了牠幾塊牛肉乾,順便蹲下來歇息一下。」
楊格的臉上掠過一絲冷笑,彷彿對大媽的說法不以為然。
「另外,她說了什麼奇談怪論?」
「她指責黑狗的犯行之外,並藉機會叮囑我,這社會的騙局太多了,不要隨便相信別人。我想,她大概看我是外地人,出於善意才這樣說。」
「哎,」楊格嘆了一聲,接著說道,「據我所知,那個大媽是個狠角色,說話的口氣,就像大學校園裡的教官一樣。在她眼裡,壞人總是多於好人,在都市討生活的流浪狗,等於為非作歹的代名詞。你聽聽就好,不要把她的話放在心上。」
「嗯。不過,她的說法很特別,居然把人與狗的心理,分析得如此生動,儘管最後指向不好的結果。對我來說,還算是耳目一新。」
「外面太冷了,有些話在外面不好談,咱們上樓去再聊。大家正等著你呢。」
「真的?我太榮幸了。」林曉流露出喜悅的神情,語聲微顫地問道,「文學大師程紅也來嗎?」
原以為楊格會明快回答,不過,情況剛好相反。他不但沒有答腔,卻對著周遭打量了一番,兩只眼睛充滿警戒之色,彷彿在搜尋可疑的人物,或是在提防某個人的現身。
這個動作引來了林曉的納悶,讓他一時摸不著頭緒,以為自己說錯話了,於是,趕緊補上一句:
「程大師不來嗎?」
「……」
楊格依然緘默以對,絲毫沒有放鬆下來,兩隻眼睛像探照燈一樣,繼續掃瞄四周的動靜。
林曉為了趕走這片不合時宜的沉默,逕自對楊格說道:
「對了,那隻聽懂人話的黑狗已經消失不見了。雖然我與牠交談的時間很短暫,其實很想多聊一下。話說回來,在寒冷的夜晚中,要辨認出牠黑色的身軀並不容易,其困難程度完全超過人類的視力極限了。」
「你說的沒錯,林曉,」楊格接過話柄,「有些動物不宜在人們面前出現太久的,因為牠們要活著、要吃喝,要消化,而一旦填飽了肚子,就得儘快閃到一旁,與人類保持安全的距離。」
「楊兄,你家裡養狗嗎?」
「以前,我養過一隻小黃狗,」
「難怪這麼了解狗的心理,跟那位大媽一樣……」
「不全然是這個因素,」
「為什麼?」
「後來,發生了一件怪事,」楊格的語氣落寞。
「什麼怪事?」
「我家的狗兒莫名地被毒死了。」
「在都市,也發生毒狗事件嗎?」林曉難以置信地說。
楊格冷笑了一下,對於毫無政治風險概念的林曉,既是抱以同情,又為他捏一把冷汗,作為當代的現代詩人,豈能不懂伊摩黨人高超而殘暴的政治手段?
「你知道,殺狗的生意有人做,幹掉政敵的滅門血案從來沒有少過。只是,他們始終祕密進行著,不容易被人發現;就算事件後來公諸於世了,受害家屬也無可奈何吧。」
說到這裡,林曉總算明白楊格的弦外之音了。林曉直覺地認為,今天晚上,程大師也會來。只是,在不設防的地方,說出他的名字來,似乎不符合安全的法則。
「楊兄,我明白了。」林曉說。
楊格「嗯」了一聲,沒往下說,用眼神示意林曉趕快離開寒風的圍繞,再耽擱下去,他的身子也吃不消。進一步地說,有關《解凍詩刊》為林曉做專輯的種種細節,喝過熱酒之後,再詳細討論了。而一路冒著嚴寒來訪的林曉,經歷著與黑狗的交談、愛惜孫子的大媽從反面的立場向他剖析人與狗的心理距離,於他都是複雜而有趣的體驗。於是,他不由得推想:倘若時間是一種毒藥的話,那麼在他多次弄錯方向的時候,想必已隨著寒風吹散了;即使有些時間的毒素以偽裝形式留存下來,它們應該不會加害於他。因為時間有時會自在變化的,變成像暴風雨似地呼吼過去,徹底地將殘留的時間毒素統統帶走。
他們二人默默走著,大約走了五十公尺左右,來到一棵的大樹前面,因於枝葉茂盛的披覆,夜色似乎變得暗淡了。說來奇妙,當你置身在這種蕭索的景物中,似乎都要懷疑起自己的視界,懷疑它們被消褪了、被歪曲了、被篡改了,最終不還原其形象和面貌。
楊格再次用眼神示意林曉,然後像鷹隼似地抬起頭來,指著三樓公寓透出亮光的窗戶,咱們已經來到聚會的地點了。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值得慶祝的偉大之夜。(完)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文化隨筆三部曲《日輪帶我去旅行》、《我的枯山水》、《燃燒的愛情樹》(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