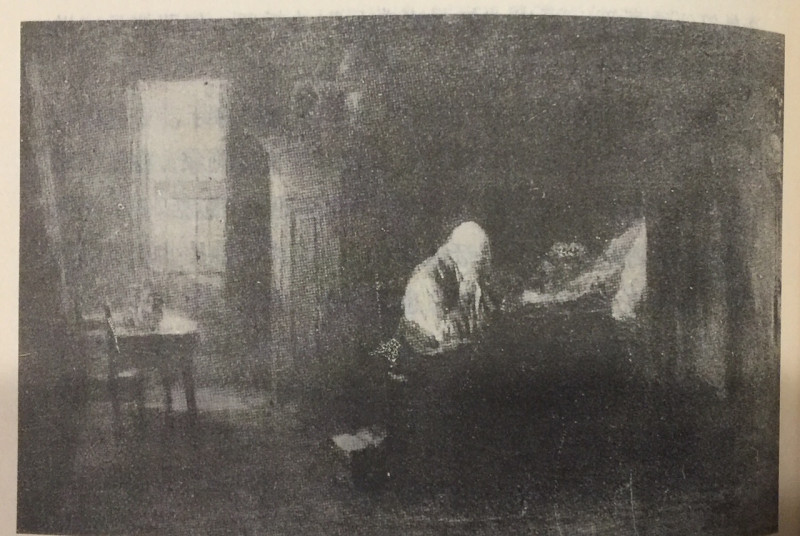對聰明睿智的人,也不知其深度,對勤奮用功的人,也不知其真諦,我的思想在世上找不到接受者,如同海水只能在自己體內老去。----法稱(古印度詩人)
12.
馬僮終於打來電話了。他的聲音顯得疲憊和嘶啞,彷彿不是剛從會議室走出來,而像經歷過一場搏鬥分出勝負之後被抬出來似的。
「阿尼基,你要不要上來坐坐,我請工讀生幫你沖杯咖啡。」
「噢,不用了。」
「為什麼?」
「你們公司的三合一咖啡,我領教過好多次了,」我毫不掩飾地說,「我的胃腸很敏感,禁不起即溶咖啡的折磨。上次,喝了以後,胃痛了兩三個鐘頭。」
「有那麼糟糕嗎?我覺得很好喝耶。我們開會的時候,都喝這種即溶咖啡,沒聽說同事喝了閙胃痛的。」
「咦?這麼說,人家以色列有鐵穹防空系統,你和公司的同事都有個鐵胃,才免除了胃痛的折騰。你不要仗著身材瘦小,有嗜糖的本錢。健康醫學指出,人過中年以後,糖份攝取過多,除了容易蛀牙之外,很容易誘發胰島素阻抗,增加肥胖、代謝症候群機會,並使血壓、血糖、血脂升高,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加速身體老化……。總而言之,糖還是少碰為妙。」我語重心長地說。
「還是阿尼基有品味,」馬僮說,「我呢,只要物美價廉的東西,一定舉雙手贊成。」
「別抬槓了。我正在名人西餐廳,你快來吧,我請你喝杯頂級咖啡。」我催促道。
「真的?嗯,我十分鐘內到。……可以的話,順便幫我點一客沙朗牛排,我還沒吃午餐。」
我思忖,馬僮算盤打得精確,我說要招待頂級咖啡,他順勢加碼又補上高價的牛排,難怪克拉克博士說,他是個吝嗇的鐵公雞。不過,我們同為狄德羅中學的同學,有著深厚的情誼,即使戲劇性的重逢之後,見面聚餐不那麼頻繁,我作為他曾經的大哥(阿尼基),偶爾他一起品嚐高級咖啡,招待他享用美味的牛排,倒也順乎人情義理。我始終認為,真正的友情不是算計,而是善意與包容。
大約過了十分鐘左右,馬僮準時現身了。他出現在餐廳門口時,朝裡面探頭探腦,像是看我坐在哪裡。我坐在臨窗的位置,過道中間有一堵裝飾牆,從入口的地方,他無法一眼就看見我。
「馬僮,我在這裡。」我立起探出半個身子,向他揮了揮手。
他尋著聲音的方向,看見了我,立刻泛起了笑容,步履疲乏地朝我走了過來。他一落坐,我把裝著檸檬水的玻璃杯,輕輕推到他的面前,杯底在厚厚的桌布,滑出一道輕柔的聲音。這是一家走復古風味的西餐廳,許多名人和作家都喜歡在此用餐,喝咖啡聊天,藉著這個類似文藝沙龍的場合,莊重和襯托自己的人文氣息。
「喝杯水,解解渴吧,」我開口說道,「你要的沙朗牛排,我已經點了,二十分鐘以後,就會送上來。」
「謝謝。」馬僮抱怨著說,「哎,最近我忙碌得人仰馬翻,每天有開不完的會議,不僅如此,還得安排座談會、邀稿、製作競選文宣等等。我簡直就是萬能便利屋……」
「咦?你是《海馬斯論壇報》的主編,除了編務和邀稿之外,其他也是你的業務範圍嗎?」我立刻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所以,我才自嘲是萬能便利屋。」
「可是,你這麼說也不對呀……」我說。
「什麼意思?」
「當初,海馬斯雇用你的時候,已經告知你的薪資和負責範圍吧?」
「沒錯。」
「我認為,這是你應盡的責任。《海馬斯論壇報》既然是你老闆的機關報,你就是這個媒體的執行者。而且,之前你說這個媒體,正符合你的政治立場,可以實現你的政治論述主張。所以,就此而言,你應該是如魚得水才對。」說到這裡,我不以朋友的身份說話,而是以阿尼基的角度說話。
馬僮沉默了一下,接著辯解似地說:
「是啊,拿人薪水就得認真辦事。不過,人累了心情不好,就愛發牢騷。……還是阿尼基有底氣。」馬僮說。
「對了,你的英語一直念得很好,又讀了名牌大學研究所,為什麼不當英語教師呢?」
「這樣說吧。自從我投入社會運動之後,我發現,我的英語念得再好,對於社會不能改變什麼。你知道,我個子不大,以體力絕對打不過敵手,但我若練得一手好文章,就能彌補身材上的弱勢,甚至成為強有力的武器。這是我反敗為勝的關鍵……」
「原來如此。」
說著,我忽然想起了嚴向冬先生,他一直在自家書房裡,為編著臺灣歷史孤軍奮戰著。中午,承蒙他的好意,特地送我到雷馬克站,我沒有告訴他,我要與海馬斯的主編碰面,但我一定替他問明退稿的原因。
「話說回來,你們海馬斯接受投稿嗎?」
「當然。」馬僮說得斬釘截鐵。
「包括手寫稿嗎?」
「哈,」馬僮笑了一聲,「手寫稿已經被時代淘汰了。現在,投稿者都發電子郵件附檔文字稿。」
「在你印象中,曾經收到署名嚴向冬的投稿嗎?」
馬僮沉思了一下,很快地,就做出了回答。
「有,投稿過三次,但都是手寫稿件,所以,就把它退稿了,讓工讀生跑了三趟郵局。」
「馬僮,我做個譬喻,如果對方大有來頭,或者說,你老闆的朋友,他投寄的是手寫稿,你會採用嗎?」
「這個嘛……」馬僮嘟嘟嚷嚷著,最後支支吾吾地說,「這種情形,老闆通常會特別交代,我就得想辦法完成這個任務。」
「意思是說,工讀生不為你代勞的話,你就得為手寫稿打字是嗎?」
「嗯。」
「哈,我終於理解,你為什麼自嘲是萬能便利屋了。」
「阿尼基,」馬僮說,「我的便利屋服務不止這些呢。」
「你說說看。」我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地說。
「最近,國會議員選舉將至,我老闆特別緊張,擔心上次的事件,壞了他的選情。他雖然不在天龍國,每天晚上,一定打電話給我,交代我為他出謀劃策弄點議題,或者強有力的文宣。有時候,我都覺得自己的精力都快被我老闆給榨乾了。」
「的確,你需要吃牛排補補身子。」我打趣地說。「不過,這也證明你是個能手。我想,將來你老闆當選縣市長,一定會重重提拔你。」
「很難說。……我老闆有他的人事考量,到時候,有人會攀親帶故套交情,向他討個職位,反正情況很複雜就是。」
「在你看來,你老闆採選的標準?」
「哈,」馬僮又笑了一聲,「當然,是以那個人能否成為他的戰力為採用標準。」
「這麼說來,如果你老闆當選以後,沒有給你安插職位的話,就表示你不能給他帶來戰力,而是用來停車暫借問的花瓶,是嗎?」我單刀直入地說。
「……」馬僮不示弱地說,「不過,從花瓶的角度來看,未必就是輸家。假如我老闆不幸落選了,那些被他視為最佳戰力的人,也要跟著失業了。而我,至少還能守住這塊陣地,雖然影響力不大,但我有固定薪水可領,生活受到保障,又能藉由這個平台,建立各種人際關係,將來有什麼變故的話,我就有下一條船搭乘……。」
「不簡單啊,」馬僮這番話,讓我對他刮目相看,「你布局如此之深,與當初老是被杜豪欺凌的馬僮判若兩人了。就此來說,我要恭喜你。因為要戰勝比自己強悍的對手,並沒想像中來得容易啊。」
說到杜豪對馬僮施加的暴力,以及變態般的羞辱,作為受害者的馬僮似乎很不願想起它,哪怕只是記憶的片斷,它都像隱形的刀片一樣,潛入他的心口上,快狠準地劃下。
「剛才,我向阿尼基抱怨,忙得不可開交什麼的,事實上,我的同業《伏爾泰年代報》副總編輯茱利亞,她比我更忙碌幾百倍,工作量和壓力大得驚人。」馬僮說。
「她到底有忙碌?」
「她告訴我,她每天時時刻要督促底下各組的記者群,有沒有漏掉重大新聞,而且還得審核實習記者的稿子,是否符合新聞寫作的規模,若不符規範或記述不準確,她就得確認內容、查證消息來源,迅速地修正刊登。」
「最糟糕的情況是什麼?」我好奇地問道。
「茱利亞說,如果新聞報導有所偏差,總統府的高層立刻來電話質詢她,是不是收了赤魷黨的好處,否則怎會寫出這種稿子;同樣的情況是,與她有交情的地方縣市長,認為《伏爾泰年代報》對他們的報導不友善,火速地打來電話質問她,是不是被伊摩黨的金主給收買了。」
「的確,這副總輯真不好幹呀。」我又問道,「此外,還會遇到麻煩的事嗎?」
「有,當然有。」馬僮轉述的時候,為這位新聞同業叫屈,「有一次,工讀生上網抓了一張照片,以為這是免費使用,就搭配新聞刊登出來。但是,麻煩來了。兩個星期後,《伏爾泰年代報》收到了外國寄來照片使用費的帳單,那一張照片索價三十萬元。後來,還打了官司,他們敗訴了,不得不支付這筆錢。這種活生生慘痛的教訓,她作為主管都要概括承受的,這也是編輯檯始料未及的壓力。幸好,我們海馬斯都選用維基共享的圖片,避免被罰款的危險。」
「馬僮啊,」我語重心長地說,「其實,我今天來找你,還有一個目的。」
「什麼目的?」
「那天,我在萬年春麵館吃水餃,無意間從電視裡看見你被赤魷黨的女人打傷了,左眼角流血了,突然有一種感觸,你的工作有著高度的危險性。剛才,又聽你談起自己像陀螺忙得轉個不停,我們活到這個年紀了,何必一輩子為人做嫁衣裳呢?你很有才能的,何不辭掉工作,當個專業作家呢?我的出版社不大,但我一定支持你。」
「阿尼基,謝謝你的好意。」馬僮說,「寫書是賺不了錢。剛才,我已經說過,抱怨歸抱怨,我寧願選擇安穩的道路。如克拉克所說,我馬僮終究是平庸世界的人。」
「這麼說,與你相比,我是極端世界的人囉?」
「是啊,阿尼基和克拉克,你們都是極端世界的人,對我應該不適合。」馬僮說道。
服務生端來沙朗牛排了。盛著牛排的鐵板滋滋作響,馬僮連忙拿起白色餐巾紙,擋著不斷往他身上撲來的煙氣,一邊細瞇著眼睛,臉上掛著滿意的笑容。美味的煙氣散去之後,我探身向前,湊近馬僮的耳旁,輕聲問道:
「克拉克博士說,他很關心你的事情,特別為你介紹了波斯貓論壇,你去了沒?」
「波斯貓論壇?」馬僮收斂住笑容說,「哎呀,這可是要花錢的玩意,而且很危險呢。我一點興趣也沒有。」說完,他拿起亮閃閃的刀叉,慢條斯理地切劃下去,津津有味地享用柔嫩的牛排。
而我則退回到原來的位置,啜飲著偏愛的藍山咖啡,回想著幾十年來經歷的風雨冰霜。過了一會兒,不知什麼緣故,我抬頭注視著馬僮的面容。在那當下,或許,視角和室內光線的關係,我彷彿覺得馬僮的左眼角又淌下鮮血了,不由得想要伸手擦拭它,但又縮了回來。一隻銀色的大蒼蠅,很不合時宜地闖了進來,在我們面前飛繞著。我不知道,這大蒼蠅是在挑釁,或者是在喧鬧(完)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文化隨筆三部曲《日輪帶我去旅行》、《我的枯山水》、《燃燒的愛情樹》(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