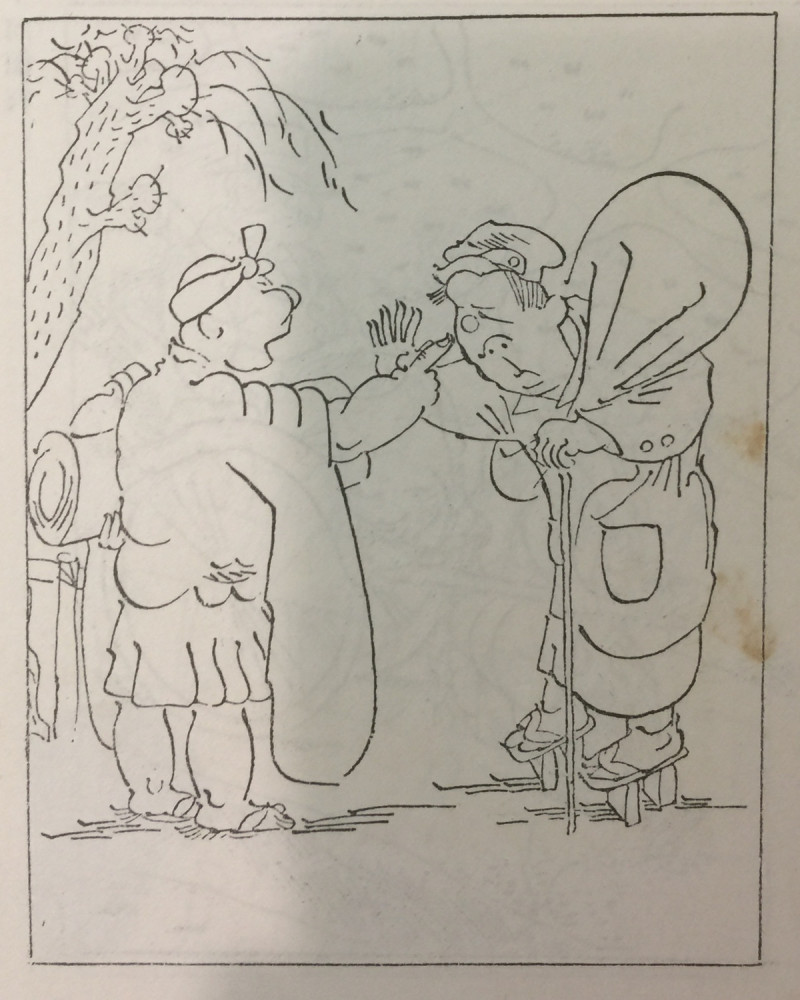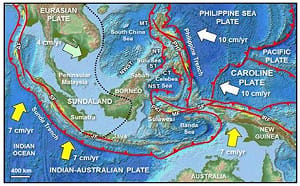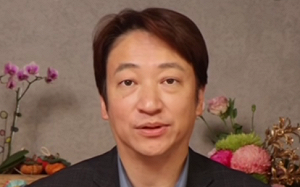在這個價值錯亂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講述自己的故事,以獲得嶄新的身份,找回有意義與價值的位置。這部小說藉由一個徬徨的青年作家,為了解封性愛的苦悶和對生命的探求,得到一個老政治犯的思想啟迪,從此走出思想的困境,進而了解底層人物的心聲,揭示存在於臺灣社會內部的禁忌和荒誕面相。同時,這也是由壓抑的性愛通往政治思想解放的現代喜劇。
第三章 無神論者的視界
無法安放的同情
賀蒙特聽著格雷特吳的遭遇,心裡升起一股悲涼,但當下,又無法給予恰如其分的安慰。他繼而想著,也許聆聽他者的痛苦,他者就能稍為得到解放吧。
「在那以後,他們又上門來嗎?」賀蒙特探問道。
「有,來過三次。正如之前的那樣,他們進入畫廊以後,不怎麼走動,各自看著牆上的畫作。彷彿牆壁就是他們傳遞情報的鏡子。」
「另外,那兩個人還守在外面嗎?」
「嗯。下雨天,他們照樣站在外頭,手上撐著一把黑傘。」格雷特吳皺著眉頭,似乎不想回憶那個場面,「不知是不是雨天的緣故,我認為,他們的目光是冰冷的,比冬天的寒雨冷得多。」
「這麼說,你們最終照過面了?」
「嗯。不過,僅止那麼一次,」格雷特吳說道,「不是那種正式的交會。他們佯裝成路過的行人,像是在打量對街的樓房什麼的。」
「對街的樓房,有什麼特別的標誌嗎?」
「沒什麼特別的。如果說,有什麼令人醒目景觀的話,那就是五樓住戶的陽台上那棵九重葛了。它長得枝葉茂盛,開著紫紅色的花,煞是好看。我覺得,看著九重葛生機勃然的樣子,或多或少能夠使人心情愉快些,但是比起抬頭看向天空,我更多的是,從門板的窺孔中看向外面。」
「所以,那株美麗的九重葛成了特務份子跟蹤的道具了?」
「……」格雷特吳似乎嘆了一口氣,「想不到,九重葛也被他們利用了。這不是一種諷刺嗎?」
賀蒙特對著格雷特吳說,他的朋友查利提曾經是個政治犯,與他的案情相似,因為參加左派傾向的讀書會,在神鬼不知的情況下,被車輪黨的細胞給滲透了。他捱過殘暴的刑求拷打,仍然沒有供出同伴的名單,最終坐了五年的苦牢。不過,查利提是個聰明人,他很快地就擺脫貧窮的糾纏,而且很有商業頭腦,在那些好時機的年代裡,他抓住難得的機會,不到幾年的功夫,就賺進和累積了近億萬元的房產。令人敬佩的是,他不是守財奴,而是善用賺來的錢財,做有意義的應用。
「他出獄以後,沒有被特務份子跟蹤嗎?」格雷特吳關注這個問題。「我實在不相信,一個身心俱疲的政治犯,他們能找到什麼出路嗎?」
「在戒嚴時期,這是個敏感的問題。不過,出於好奇我還是想問個究竟。他自嘲地說,在車輪黨的特務系統看來,因為他不是傑出的藝術家,或者思想銳利的作家,不構成立即的危險性,也沒有顛覆政府的具體行動,因而不需要對他長期跟監。他又說,比起寫文章批評車輪黨的獨裁統治,揭露車輪黨弊端,他投入做生意的行當,自然比較來得安全,不會引來車輪黨的盯梢。但是,你的情況不能相提並論。」
「我們同樣身為政治犯有什麼不同?」格雷特吳追問道。
「當然不同了。你是批判現實主義的畫家,所描繪的社會底層群像,總是那樣感人至深,日子久了,就會得到大眾的支持,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換句話說,你們在思想本質上是不同的。查利提成功地成為生意人,他可以擺脫跟監的夢魘,而你的才華和處境卻與他相反,車輪黨似乎對你不放心,不想放棄對你的監控。」賀蒙特看見格雷特吳陷入沮喪的漩渦裡,而且頭髮沒有梳理,顯得蓬亂和頹靡,「對了,畫廊老闆怎麼說?他應該了解情況,才雇用你的?不全然是因為赫大頭的關係吧?」
「……老闆馬蒂斯是個有情有義的人,他願意收留我這樣的人,我是非常感激的。所以,我把自己在畫廊努力工作,視為是對他的回報。」格雷特吳說著,「不過,就算他有心維護我,他也有頂不過的時候。」
「莫非是特務人員給他施加壓力嗎?」賀蒙特同情說道,「在這種情況下,他向赫大頭抱怨,說你經常無故缺班?」賀蒙特問道。
「應該是吧。」
也許,這情況正如格雷特吳自己所說,一個人只要被打上政治犯的烙印,一輩子就別想把它剔除掉。再說,一個平凡的畫廊老闆,沒有黨政軍背景的關係撐腰,哪禁得起情治人員經常請喝咖啡的恐怖壓力呢?這時候,作為受害者的主體應該主動表示,很識相地辭掉這份差事,退回到自己的洞穴裡,以免無辜的雇主受到株連。
那些沒有掩體的畫作
「對了,你家的電費和水費,真的由童衛國代付的嗎?」賀蒙特再次確認。
「嗯。我離開畫廊以後,沒有固定的收入,心裡非常不安。雖然這套公寓是我大姐供我居住的,不向我收取房租,但我總是要弄點什麼來賺取生活費吧。於是,我自告奮勇給出版社做插畫或者繪製封面。」格雷特吳說道,「即使這樣,我的經濟狀況仍然不見好轉。」
「出版社給的費用不高嗎?好歹你也是有點名氣的畫家,他們總不能虧待你啊!」
「我不知道市場行情,說不上到底合不合理。」
「他們怎麼支付費用?」
「我回想一下,」格雷特吳閉上眼睛,表情有點痛苦的樣子,一道既深且直的皺紋,如一把利刃插在眉心中,「……我記得為播種者出版社繪製書籍封面,他們支付三千元,這樣算是合理嗎?而且,有許多原畫素描都沒有還給我。」
賀蒙特承認自己沒當過出版社的編輯,不了解當年出版社支付給畫家的封面設計費是否合理?但是在他看來,出版社僅有使用權,而不可將原畫占為己有,付印之後必須交還給畫家。如果格雷特吳的說法屬實,那麼出版社的做法,未免太沒有商業道德了。多年以前,他的印刷廠老闆里斯本向他透露一件祕密:獨角獸之火出版社的老闆艾蒙尼差點捲款逃往加拿大。這件事情是該出版社的外務員麥克轉述的。麥克說,獨角獸之火出版社曾經風光一時,後來經營狀況出了問題,出版品嚴重滯銷,讓他老闆艾蒙尼睡不好覺,為未來的日子擔憂,為發不出薪水而煩惱。然而,所謂勞動產生智慧,煩惱即是菩提。有一天,艾蒙尼在缺錢危機的刺激下,突然像小沙彌獲得大頓悟似的。他連日在報紙上刊登大型歷史圖書全集廣告,用誘人的折扣優惠每套15000元來招攬讀者。在那個年代裡,那個套書售價不算便宜,幾乎要花掉公司職員半個月的薪資。但是,依照艾蒙尼的盤算,只要他手上有4000個讀者預約訂購,他就有6千萬元的進賬。這是一筆多麼閃亮的巨款啊,絕對能夠照耀著他的下半生。進一步地說,他帶著6千萬元移民到加拿大,保證得以過著優渥的生活。自從他在報紙打出全版圖書廣告以後,這個偉大的計畫便開始讓他感到自信起來,對於人生不再沮喪。
奇妙的是,可能是他們家供奉的財神飲酒過量,竟然答應出手搭救,圖書廣告的效果出奇的好!他原本預計一收到4000個訂單,就要遠走高飛了,可是實際的情況,卻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料。按照麥克的說法,預購的郵政劃撥單簡直如雪片般飛來,他每天到郵局提取郵政劃撥單,拎著的整個大提袋塞得快要膨滿出來,因為每一張預購圖書全集的郵政劃撥單,就自動化約為嶄新的紙片大鈔。這個計畫成功了。與此同時,它也改變了艾蒙尼移民加拿大的計畫。不過,艾蒙尼還必須解決一個問題:當初,他打出的圖書廣告是空砲彈,沒有實質的出版內容,僅只是他畫給讀者充飢的大餅。這就是說,除了白義行捉刀所寫的廣告文案,全集裡一個實體的文字都沒生出來。然而,艾蒙尼在出版社混跡多年,畢竟不是個簡單的人物,否則他哪構想得出以圖書謀取移民的偉大計畫呢?於是,他立刻召來最得力的助手胖周瑜白義行,他是獨角獸之火出版社歷史線的主編,常年與歷史作家們有往來,擅長於奉承和偽善的技藝。艾蒙尼相信,以白義行的天份和卓越才幹,必定能把事情辦得圓滿周全。果真,白義行不負重大使命,沒多久,他就用最高等級的陣仗迎來了那位歷史大師。而這又是極大的宣傳機會。獨角獸之火出版社趁這機會對外宣稱,他們特地為大師設置專室,並提供責任編輯斟茶奉飯,而大師不負所託正式為這套全集開光點眼,帶著屬於他們製造的聖光進行劃時代的偉大工程。
「哎,老弟,出版社的老闆需要把事情搞得那麼複雜嗎?」格雷特吳淡然的感嘆,「說起來,還是你講義氣,我由衷感動。」
「怎麼說?」賀蒙特睜大眼睛說道,「莫非你又遇到不愉快的倒楣事?」
「嗯。童衛國每次來我這裡,手上拎著一瓶威士忌,說是要請我喝的,一擱下酒瓶,立刻在我的房裡搜找一通。他一看見我完成的畫作,兩隻眼睛亮了起來,從來不問我這是否要拿去寄賣的,他就拿在自己的手上了。有些時候,連我半成品的畫作,他都要一併帶走。他以為我發酒瘋什麼都不知道,其實他帶來的威士忌都是便宜貨,我一眼就能看出來。」(未完待續)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我的書鄉神保町》1-10卷(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