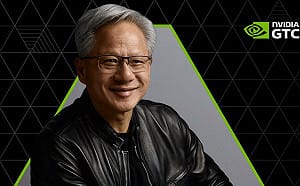2000年4月23日,即將接任國史館長的恩師張炎憲教授,邀請我前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的台灣國際會館,參與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主辦的一場別具意義座談會—「重建台灣歷史記憶:『4‧24刺蔣事件』與台灣座談會」。當天經過三個小時的聆聽,不僅讓我對4‧24刺蔣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對於現場兩位刺客的紳士風度感到印象深刻。這是我第一次目睹鄭自才先生的丰采。 轉眼已是2020年4月24日,「刺蔣事件」邁入50週年!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如果命喪紐約,台灣將會如何?這已經成了永遠無法回答的假設性問題。至於蔣家王朝在台灣留下的統治神話,正等待全體台灣人共同去解構;蔣家王朝在台灣留下的殘餘勢力,也正等待全體台灣人共同去進行轉型正義。
1. 成長環境與歷程(1936~1962)
1936年12月1日我出生在台灣台南市。1943年進入台南市寶公學校(今立人國小)就讀,直到1945年停戰,總共接受了兩年的日本教育。由於躲避空襲,最後一年的教育是很不正常的。我在八歲的幼年,就親眼目睹死亡的現實;不久之後,又親身經歷戰爭的苦難。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恐怖的戰爭終於結束了,我們在鄉下的避難生活也就隨之過去。可是,我們的生活並沒有隨著改善。
現正最夯:獲徵召就鬧事! 藍動員千人擠車站迎接游淑貞 作家傻眼:這是21世紀台灣嗎?
這場戰爭,帶給無辜的台灣人民經濟破產、物資缺乏、醫藥不足與房舍、道路交通的嚴重破壞。再加上中國佔領軍的違法亂紀,使台灣的社會陷入地獄的邊緣。
台南市區被美軍轟炸得殘破不堪,馬路上到處是炸開的深坑,燒毀的房屋不計其數。不久,冬天就到了。家裡的棉被連被單都沒有,全家人就只蓋這一件,沒多久,棉被就被拉成好幾塊。有一晚,我捲著一塊破碎的小棉被,就像捲春捲一樣,但無論如何都無法使身軀溫暖,冷得流下眼淚。就這樣,度過了整個寒冬。
好不容易春天到了,鄰居的孩子跟我說學校有學生在上課。於是,我就跑到寶公學校去看。學校裡並沒幾班,每班都在教《三字經》。就這樣,我繼續接受學校教育。中國軍佔領台灣之初,教育體系極為紊亂。沒什麼制度,也沒有課本,老師也不會教。
現正最夯:伊朗彈道飛彈轟土耳其!遭北約防空系統摧毀 恐觸第五條款
在1947年的某日,父親忽然不准我們小孩出門,他只說出門危險,馬路上有人在打架。十一歲的我並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後來長大了,才知道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屠殺事件」。
小學的最後一年(1948年9月到1949年6月),老師每天幫學生補習,我們則整日坐在教室內。
老師要我考省立工學院(今「國立成功大學」)附設工業職業學校,他認為職業學校可以學習一種職業,因為我們不是富裕的家庭。那時候,學生並沒有表達自己意志的機會,也沒有說話與選擇的機會。放榜後,我錄取了建築科。
這一年正是蔣介石政權在中國被共產黨擊潰,逃難流亡來台灣的一年!學校的生活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學生早晨上課前必須參加升旗,下午放學前亦必須參加降旗。不准在學校講台灣話,必須講中國北京話。「三民主義」、「國父遺教」、「總統訓詞」被列入職業學校的必讀課程。於是,職業學校也變成中國佔領軍的政治學校。後來,更變本加厲,所有的學生都被編列入所謂「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團員。教育變成中國佔領軍政府的統治工具。學生在上課期間,經常被驅使去參加遊行、向蔣介石祝壽等等的活動。
工學院附設工業職業學校從初一讀到高三,叫做「六年一貫制」,我便一路讀到高三,從而避免了另一次升學考試的災難。1955大學考試放榜時,我錄取省立工學院建築系。
在大學時,第一個明顯的感覺是,同班同學近一半是中國人。這些中國人同學與台灣人同學在性格上有顯著的不同。他們都是跟隨蔣介石逃難來台的「政府官員」的子女,對台灣同學有一種自以為是的優越感。
大四時,朱尊誼系主任跟我面談過,跟我說:「你退伍後可以回成大當助教。」1961年退伍後,我便回到成大建築系向朱尊誼系主任報到。兩個禮拜後,成大教務處卻說我不能擔任助教。才知道,原來是因為當年我拒絕入黨,有這個紀錄在,就不聘我當助教。於是我只好打包行李離開。
2. 1960激盪的年代(1962~1970)
1960年代是激盪的年代,國際社會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動。美國為了鞏固其亞洲的利益,發動越戰,但是因為越戰激起了強烈的反戰聲浪,而黑人運動、民權運動也方興未艾。在共產世界方面也發生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大型運動。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同時受到強烈挑戰。
在台灣,中國佔領軍政府靠著日本政府殖民時代的資產和美國的政經援助,推行以加工出口為主要導向的計劃經濟,使台灣經濟從戰後的蕭條中開始成長。然而在以反共復國為名的戒嚴體制下,整個台灣社會籠罩在人人噤若寒蟬的白色恐怖肅殺氣氛之中。因此許多知識份子在中國軍政府的高壓統治下,異常苦悶,不是投身工商界,絕口不談政治;就是出國留學,不再回來。
我向美國大學硏究所申請入學許可及獎學金。結果有三間大學給予入學許可,但是只有一間大學給我全額獎學金,就是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之前是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位於美國Pittsburgh,Pennsylvania。所謂全額奬學金就是學校提供註冊費、宿舍費含早晚餐,所以我自然而然就選擇去就讀該校了。
1962年9月1日由松山機場起飛,經由東京、Honolulu 、San Francisco 到Seattle 。9月3日晩坐Greyhound bus 離開Seattle,9月9日晨抵達匹茲堡。9月17日註冊日,開學日則在9月19日。
除了功課,我每禮拜日參加Pittsburgh Symphony Orchestra 的演奏會,也參加教會舉辦的音樂會,閱讀課外書籍。其中有一本John Kenneth Galbraith 在1958出版的「The Affluent Society 」給我非常大的震撼,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我所了解的美國是一個很富裕的國家,為什麼在富裕的社會裏有大量的貧窮人?因為過去的黑奴制度,現在的種族歧視政策,使白人以外的族群失去平等的就業及受教育機會。一代一代悪性循環,窮人愈來愈窮,富人愈來愈富,造成社會嚴重的貧富差距。公平正義的偏差,使我傾向於支持並同情弱勢族群。
1960年代的校園學生運動、反越戰運動,主要是以在學的大學生為主。黒人人權運動則是以黑人為主体。1963年8月28日黑人人權運動團體發起有史以來的最大規模的華府示威遊行。因為我同情美國黑人的被歧視及被不公平的對待,所以,我參加了這一次的示威遊行活動。我一個人坐火車由匹茲堡去華府,車廂裡擠滿了要去參加遊行的人,抵達華府時是人山人海。當天,黑人人權運動領袖Martin Luther King Jr. 在華府林肯紀念堂前發表歷史性的演說:「I have a dream.」。參加這次有歷史性遊行活動,給我很好的機會教育與經驗。
我剛出國的時候,還是受到中國佔領軍政府的教育的影響,在留學生的圈子裡都是說北京話,1963年我在校園裡在台灣來的學生聚會中,遇到一位研究物理的王俊明校友,他對我說:「你不會說台灣話嗎!」這句話點醒我是台灣人的認同意識。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只講台灣話,不説中國話了。
我閲讀George H. Kerr的「Formosa Betrayed」及在東京出版的「台灣青年」刋物。支那人蔣介石集團佔領台灣,屠殺台灣人。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上等,台灣人被支那人迫害與歧視。對台灣的歷史與現況開始有初步的認識。在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兩年的學校生活中,雖然校園是相對平靜的,但是被自由、民主的風氣與氛圍潛移默化。我開始說台灣話,拒絕説支那話,並堅信自己是台灣人。1963年我加入「美國台灣獨立聯盟」。那時候我還不認為自己是什麼運動者,只是很簡單地認為,身為一個台灣人,應該加入這個運動。加入這個運動之後,我就不能回去台灣了。但事實上我在1962年飛到美國之後,就把那本支那護照丟了,早就下定決心不再回去台灣了。
1964年,黃文雄也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的獎學金。他來的時候,剛好我畢業,沒多久我和晴美就結婚了。9月我和晴美離開匹茲堡 到Baltimore, Maryland,我就在一家建築師事務所工作。
1965年我在位於紐約市,一間相當著名的「Marcel Brueuer建築師事務所」找到新工作,於是全家由Baltimore 搬到離紐約市47公里的Metuchen, New Jersey居住。
之後我們有機會搬進Jackson Height, Queens , New York。搬進Jackson Height 之後,與台獨聯盟的盟員有更密切的互動。因為當時台獨聯盟有一個策略,就是希望幹部盡量集中在一起。
1969年9月,全球性台灣獨立聯盟籌備會議在美國的紐約召開,來自美國、加拿大、歐洲和日本的各地台獨組織都同意成立世界性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1970年1月1日,組織正式對外宣佈成立,由蔡同榮和張燦鍙分別擔任該組織的正、副主席,我則擔任執行秘書。也是在1970年,當時擔任台灣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應美國國務卿的邀請,計畫赴美進行十天的訪問。正是在這樣的機緣下,開始運籌刺殺蔣經國。

鄭自才在1969年228大屠殺忌日在Columbia University大門口分發傳單。 圖:張文隆/提供

鄭自才的畢業照,成功大學建築系1959年。 圖:張文隆/提供

黃晴美、鄭自才與女兒鄭日青,1967攝於Columbia University。 圖:張文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