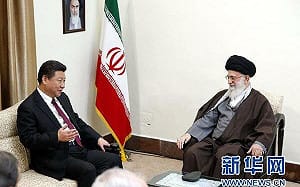2019年5月,報載44歲的港星吳彥祖得了闌尾炎,卻被誤診為單純腸胃不適,從發病到住院,9天沒吃東西,體重驟減7公斤,最後盲腸破裂、腹腔發炎、潰爛,引起敗血性休克後,才確認病因並緊急手術挽回一命。
術後連醫生也訝異,一般人只能撐幾小時,吳彥祖卻撐了這麼多天,真是命大!但不只是人的身體裡有盲腸,政府裡也有。
現正最夯:伊朗遭空襲畫面震撼 楊植斗怒轟苗博雅:戰時還談正常上課?
有些冗員機構的產生,是因1949年的流亡遷徙,國民黨政府為了標榜正統,所以堅持存在的一國兩省(台灣福建)一省兩縣(金門連江)。也有些是兩蔣擔心百里侯坐大,就將行政區分割到雞零狗碎,產生一些根本無法財政獨立的窮縣(苗栗雲林等)。
但比起行政區劃分不當,台灣最不該存在的組織,就是孫文天馬行空的妄想,把一些帝制時代才有的官職與機構,橫柴入灶的放在民主體制的政府裡。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後,又將這些妄想一一落實,制憲時更公然入憲,成為當權者的酬庸工具。
資政、戰略顧問、監察院、考試院……都是台灣迄今仍尾大不掉,很難割除的盲腸。更可笑的是別說是廢除這些組織很難,連縮減規模,減少酬庸的人數都這麼難。
盲腸為什麼會越來越大?
2019年12月10日《新頭殼》報導〈立院三讀》考試委員19人砍至7至9人 且不得赴中國兼職〉:
「立法院會今天(10日)三讀通過《考試院組織法》修正案,將考試院考試委員》人數,從現行19人,減為7至9人,任期由6年改至4年;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任期,從6年改為4年。
為精簡政府財政,考量考試委員之職務、相關人事支出之財政節流等,立法院會三讀通過《考試院組織法》修正案。三讀明定,考試委員名額定為7至9人;……而考試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即使是不修憲就無法廢掉的考試院,在憲法裡也沒有規定考試委員的人數。根據馮惠平博士《考試院的誕生與失落》(新學林,2019,頁90)考證,考試委員原先也沒多達19人這麼多。
在1947年制憲時,「考試院組織法」是將考試委員的人數訂為11人。但1928年就擔任北伐後國民政府考試院長的戴傳賢(時年37歲),已擔任院長近20年且臥病中。官大學問大的戴傳賢,認為訓政時期的考選委員會,委員人數就已經從5人逐步擴增為17人,如今制定五權憲法,考試院既然是院級組織,考試委員的人數豈能降為11人?
但原來的考選委員是設在考選委員會裡,並非考試院這一層級。但戴傳賢在黨國體系裡,說話超有力量。因為他的堅持,1947年底「考試院組織法」修正時,考試委員的人數就從11人擴增為19人。
另一方面,行憲後的考試委員,也不像訓政時期的考選委員會裡的委員,還要負責考選業務。因為在戴傳賢的堅持下,考試院之下又成立了一個與銓敘部同等級的考選部,專責考選業務。那麼設置多達19位的考試委員,究竟要做什麼?在中國時就已經是一筆爛帳,誰也說不清。
藍委為何堅持闌尾不能割?
1949年遷台後,很多中央部會的行政組織都縮編,甚至裁撤。例如行政院裡的衛生部,先降編為衛生署,再降編為內政部衛生司。因為中央政府流亡,國土嚴重縮水,連醫療衛生這種與民生重大相關的組織,都難逃縮編降編的命運。
但考試院裡的考試委員,卻成了國民黨政府裡最幸運的冗員。一來有五權憲法裡法統的象徵,二來又可滿足大中國的想像,三來也是最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這19個錢多為位尊卻又沒事做的考試委員,成了掌權者最好的酬庸工具,所以人數始終降不下來。
前銓敘部次長徐有守,在2002年的座談會曾提及,當初設立19名考委,是為了分區負責考選業務,華北、華中、華南等人口稠密地區一省一考委,東北、西北及西南地區則各一考委,因此才有19位。
但這種說法,1949年之前在中國時,容或還有些許合理性。可是過了70年後,現在別說反攻大陸,大陸不來武力解放我們,我們就要偷笑了。這種來台之後,才來「先射箭後畫靶」,為「19」這個數字找理由,也是有點可笑。何況行憲後監察院的29位監察委員,這是分省選出的;但19位考試委員,選出來時就沒分區,日後又要怎麼分區?
鄉民們或許對考試院這一闌尾衙門,當年的那些爛帳毫無興趣。可是立法院裡的藍委卻興趣很大,堅持就是不能降低人數。如果非降不可,就降3到5個,意思到了就好,不要一次就減半。至於考試院裡的藍委,反應或許就更激烈了。
2019年12月12日《新頭殼》報導〈不滿人數及任期縮減 考試委員主張提釋憲〉:
「考試院上午召開院會,不具名考委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現場共有8名考委陳述意見,分別是蔡良文、周玉山、周萬來、黃錦堂等人,討論時間約1小時左右,現場過半的考試委員主張提出釋憲。……」
把盲腸縮小一點也好吧?
五權憲法其實從頭到尾就是一個笑話,孫文說:「五權憲法乃『兄弟我』所獨創,………」戒嚴時代有個天才考生,考三民主義時看到題目問:「五權憲法是誰所獨創?」這天才竟回答:「兄弟我」。
考試院這個孫文異想天開的創意,即使被蔣介石當成聖諭,設立後的運作,也從未像個正常的行政機關在運作。考試院裡的銓敘部長、考選部長及保訓會主委,也都不是考試委員,有些考試委員甚把自己當成立法委員,把考試院院會當成立法院院會。考試院與人事行政局,已經是雙頭馬車;考試院裡每個委員,人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更是19頭馬車。
把考試權從行政權裡分割出來,根據馮惠平博士《考試院的誕生與失落》( 新學林,2019,頁393)的看法:孫文遺教原創「單純的考試權」,行憲後卻轉變為「擴張的考試權」。在此訓政階段「考試權」還不是國家第一層權力,行憲後卻由原先「部內制」轉換成為「部外制」機關。
馮博士把國家權力的分配運作比喻為棒球,「立法」是棒球規則的訂定者,「司法」則是本壘及各壘裁判,而「行政」就像是參加比賽的球隊。其中立規者或裁判者都可以分立,當然也可相互制衡,這一點鄉民們應可理解。
但棒球比賽時,球隊裡的投手、捕手、一壘手、二壘手、三壘手、外野手及游擊手,若各自為政,相互牽制,不顧團隊合作,不聽教練指揮,請問要這隻奇怪的球隊,究竟要如何贏得比賽?敗戰責任又要怎麼歸屬?
因此,行政權下各機關組織的設計,原則上必須重在分工合作、指揮一體,而不是偏重於相互制衡,否則就成了徒然內耗、相互抵消。
行政權裡縱然有設置獨立機關的必要,例如中選會、公交會或NCC,在組織架構上也不能完全獨立於行政體系之外,仍須受最高行政首長一定程度的監督,這是「行政一體」的法理所在。更何況行政機關最重要的人事權,有看過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或哪個公司,把招考新人的權責,從人事單位獨立出來另設一制衡單位的?
考試委員人多口雜,院長又不願表決,以致任何一個委員有意見就全案擱置,造成銓敘部、考選部或保訓會的許多政策法案都難以施展,甚至讓部長被羞辱。有些考委更誇張,以立委審法案的繁瑣程序,審議考試相關議案,讓公務人員疲於奔命。
就算修憲門檻太高,無法立即廢掉考試院這盲腸組織,但高達19位的考試委員,若能縮減一半,把盲腸縮小一點也好吧?
(關於考試院的相關史實,請參閱馮惠平博士《考試院的誕生與失落》〈新學林,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