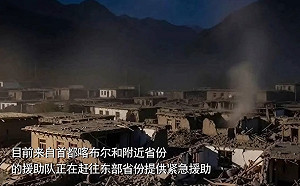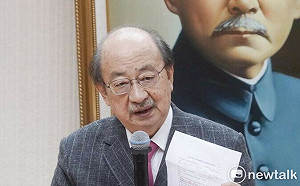她是一位每天早上九點進辦公室,隨即開始規劃學生的實驗,或是帶著學生做實驗,通常會到晚上十一點才下班,研究工作時間長達十四小時的新任大學教職的博士教師。
由於她的專長背景與生物科技相關,所以實驗室的耗材、設備花用都十分驚人,必須倚靠研究案經費的補助,才可以讓實驗室得以正常運作,所以每年通過研究案審查是極重要的任務,而目前大學教師評鑑制度上仍是偏重研究這一區塊,這樣的評鑑制度同時也掌握教師升等的生殺大權,因大學教師聘任不是終身職,且必須升等為教授,在這些攸乎工作生存權的條件前提下,她怎能不戰戰競競,如屢薄冰。
最近實驗室的學生出了一些事,造成她必須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來協助學生,這是一個道德兩難情境,她最後決定把時間花在學生身上,縱然她知道這樣的評鑑體制下,如果用工具理性來決策,現今許多大學老師的選擇可能將課程交給助教去教,而自己忙於實驗室研究或者擔任企業顧問,但這個有『教育愛』的生科系大學女老師,還是願意選擇一個在體制下不利於自己的決定。
一、台灣的大學教授「多元升等」制度和文化未完善
筆者觀察到台灣大學教師評鑑政策修正的迫切性,因2021年台大植物所張姓副教授在實驗室內上吊自殺,留下遺書表示主要是因為升等壓力大,而現今台灣高教界有關注到大學教授研究升等問題,雖有「多元升等」的新路徑,但實際上研究仍然是主要成績,多元只是為派系和權貴開方便小門,一般老師很難受惠,因台灣的大學教師升等,主要依據是學術論文,導致許多教師埋首研究、輕忽教學,雖然教育部102學年起推動教師以教學、服務等非學術成果升等,此類升等人數已從當年的2人,攀升至108學年的216人,6年成長108倍,此類教師難免被同儕質疑「夠格升等嗎?」,台灣大學教師多元升等健康風氣仍待建立,因憑教學升等不等於研究能力差,如具備教學和研究能力合一,反而研究能力更強。
二、現行大學教授升等制度所導致的怪現象
台灣高教界過去出現所謂的「6年條款」,在大學教師聘書內載明,助理教授如果6年內無法升等為副教授就必須離職,讓年輕老師壓力非常大,矛盾的是照理說老師如果拿到副教授,就等於教職有保障,但台灣許多大學裡卻出現「萬年副教授」,不願意做研究,也不想升教授,只想輕鬆過日,又讓許多學校訂有內規,要求副教授也必須盡快升等為教授,如果長期未升等,就會在系所內被冷嘲熱諷、甚至是「集體霸凌」的壓迫。
三、不是每間大學都必須成為中研院 勿忽略大學使命是「教育」
目前台灣的大學教師工作包括「研究」、「教學」、「社會服務」、「學生輔導」,但大學教師評鑑制度的獎勵卻多偏重研究卓越的老師,忽略了其他三項同樣表現傑出的大學教師,這樣失衡的大學教師評鑑標準卻可以持續決定一個大學教師升等與否的現實生存問題,這種評鑑制度特別以研究發表於的特定期刊論文,例如:是SCI、SSCI、EI來作為升等依據,如此的評鑑制度,在時間心力重要性的比重權衡之下,造成大部分的大學教師必須面對現實地以研究為主,對教學的態度則為應付就好的工具理性思維,這樣單一簡化的評鑑標準、僵化的升等機制以研究發表的特定期刊論文為依據,將會造成扭曲學術研究性與創造性,忽視論文的多元與品質,而大學教師最終被「異化」為生產論文的機器!淪為被研究經費奴役的一群工作者。也漸漸忘卻了大學的本質與使命是教育,研究固然對大學教育是很重要,「但並非唯一」,研究也是教育的一部分,而大學老師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讓學生能獲得最新的知識,也是本著學生為主體的教育精神,大學的教學專業地位不應被研究地位凌駕,在當下部份大學教師因評鑑制度而過度重視研究,卻忽略學生教學的時代狂潮下,我們是否應該想想英國牛津大學紐曼的名言:「如果大學的目的在科學與哲學的發明,那麼,我看不出為什麼大學應該有學生。」
四、社會一起助力推動大學教師評鑑制度的典範轉移
然而,必會有人回應說現實就是現實,不要自我膨脹想當英雄想當砲灰,人必須順應現實制度才能有效生存,筆者在此想提到一個世界大學發展史的真實案例,世界大學發展史的典範轉移曾發生兩次,第一次為19 世紀德國學者兼柏林洪堡大學創辦人Wilhem von Humboldt,他用行動帶起第一次大學的學術革命,產生了大學發展的典範轉移,而 Wilhem von Humboldt的介入性行動是做一個新的大學--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ät zu Berlin, HU Berlin),讓柏林洪保特大學能成為「現代大學之母」(Mutter aller modernen Universitäten),用做新大學的介入性行動提倡「教學與研究合一」的精神,大學發展發生典範轉移,改變了舊大學只有教學職責而無科學研究,使得教育與科學研究的功能同時在大學發展被重視,Wilhem von Humboldt的介入性行動直接影響到歐洲、美國大學的發展,承上所言,目前現實生活中的大學老師評鑑制度,可能正遭遇到二元對立式極化發展的挑戰,需要政府與高等教育圈的正視,也需要社會大眾一起採取介入性行動的關心,因事關大學教育培育人才的品質,大學培育的人才資源正是社會發展能否向前的關鍵來源,最後,在高教品質保證及國際化領域的政策議題上,政大教育學院侯永琪教授是目前高等教育品質領域排名全球第五的學者,說出具公信力真話,侯永琪勇敢點出這類國際大學排名系統的指標問題,因目前QS、THE、上海交大、美國的U.S. News & World Report等國際大學排行榜共同點皆以研究為主,有操作空間的事實,這也是此政策議題需要社會大眾一起用實際行動介入,讓大學教師評鑑制度發生好的典範轉移!
文.張天泰(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