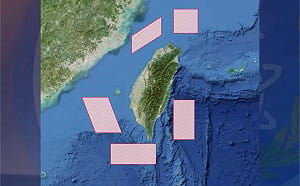海倫 清桃(呂東熹攝影)
我不是影評人,無法就專業電影橋段去評論這部電影,就像編劇兼導演蔡銀娟映後吐露:「這部片子,已經籌備年多,因為經費不足,曾經求助企業界,他們要她拍攝鬼片,她拒絕了,所以一度無法完成拍攝,幸經雲林縣政府伸出援手,才讓這部片子能順利完成。」這是台灣企業文化的落差與無奈。

導演蔡銀娟(右)
算是小品電影的「候鳥」,是繼「台西風雲」之後,一部以雲林人為故事體裁的電影,但它與「風雲」不同的是,這其實是一個關於「島內移民」與「遊子」的故事,也是雲林出身的導演蔡銀娟說,她也是只有每年會在掃墓或過年的時候,才會回到雲林鄉下老家,像這種在固定的季節,在兩個地方遷徙,這樣的特質,就像候鳥一樣。

的確,甚至以往很多鄉下人很重視的中秋節,近幾十年來,已逐漸淡化,這是「島內移民」的無奈,因為隨著第二代的成長,大人要工作養家、小孩要補習功課、學習才藝,以便跟得上都市人的程度,勢所必然地,故鄉的老爸、老媽,沒有遺忘,但已漸漸排在第二順位。
家雄的媽媽,念著他,只會幫別人墊高房子,自己家裡因為地層下陷、老是淹水,沒辦法,不是每個出外打拼的遊子,都能功成名就,都能衣錦還鄉,幫家裡起大厝;每一次颱風、豪雨來臨,打電話問說︰「有沒有淹水?」、「淹到哪裡?」好像已成為一種習慣,就像禮拜日向神父告解一般,只是愧疚似地進行一種心靈的治療。我比較幸運,沒有像家民的媽媽,有事會打電話叫他回家,因為媽媽怕我擔心,甚至連住院、跌倒等大小事,她從來都不會告訴我,但這也是心中潛藏的痛。
而那一位楚楚可憐的越南媳婦(海倫‧清桃飾演),也早成為台灣鄉下的必然寫照,姪兒10多年前娶的越南媳婦,也跟清桃一樣,回去越南多年,她騙丈夫去南越南投資,卻將他們兄弟共有的農地房產拿去貸款而留下大筆債務,兩人所生孩子也抱了回去,中秋那天,我去看他,黝黑、落寞,如同家雄;堂弟和略有小兒麻痺的鄰居小弟,經常為了越南媳婦要寄錢回越南,爭吵不斷,….。
幾乎很多家庭,都有類似的故事,因為家雄的父親突然肝硬化去世,念大學的哥哥家民,原本想休學賺錢,其實也蠻會讀書的弟弟家雄(都是班上前五名),為了成全哥哥,中斷學業,賺錢幫哥哥支付學費,我腦子想到了姐姐們,也一樣的犧牲學業與家庭畫面,這是很多鄉下兄弟姐妹普遍的遭遇。儘管導演只是輕輕地,安排家民向妻子告白一段隱藏多年的秘密,但卻讓人眼淚盈框。
「候鳥」不僅僅是雲林人的故事,它幾乎是所有台灣鄉下人的寫照,特別是漁村、農村,這是城鄉嚴重落差的現象,以往,鄉下有讀書的,無法避免,絕大多數只能留在都市工作,沒讀書或學歷不高,剛開始或許尚能在家種田、養殖維生,但隨著農村的破敗,多數年輕人,也紛紛逃離,留在鄉下,很多真的就像家雄一樣,天天與酒為伍。
坦白來說,「候鳥來的季節」算是一部平凡不過的電影,但也因為平凡,它刻畫了城鄉之間,極嚴重落差與無奈。
單純以雲林人來說,「台西風雲」只是個案式、單一年代,一部個別真實、卻非全然真實的商業電影,但「候鳥」卻更寫實、更平凡地呈現「島內移民」的真實苦楚。
多年之後,重新審思「台西風雲」,長期以來,它其實是讓雲林人揹負了「流氓的故鄉」,這個不名譽的烙印,這個烙印,如同跟我一樣北上求學、工作的南部人,經常被恥笑的「台灣國語」一般。
很多歷經風霜的雲林人,特別是我這個從事超過25年新聞工作的記者而言,雲林人沒有這個能耐來承擔「流氓的故鄉」這個烙印,講流氓幫派,雲林或彰化以南縣市,充其量只是個別小角頭而已,它們沒有一個角頭,比得上起源於台北的幾個大幫派,也沒有一個縣市角頭有能耐,可以縱橫海峽兩岸,甚至到美國去暗殺異議份子。雲林不是「流氓的故鄉」,也承擔不起。
如果說「候鳥」,有什麼可以為它喝采的,或許,它不只為台灣西部海口人,卑微地重塑了一個善良、勤奮的形象,也不僅僅敘述單一縣市的遊子故事,特別的是,它清晰地描述了一個時代的變遷,以及政府長期重商輕農、重北輕南,城鄉嚴重失衡的農村悲歌。
導演沒留下答案,因為故事還在發生,悲歌還在延續。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