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熾是郭雨新最得力的助手,由郭雨新一手提拔出來,並且可望是郭雨新的接班人。但在1971年不幸車禍死於台北市,當時很多人深信這是一樁政治謀殺,郭雨新曾在張光熾遺體前悲痛欲絕地撫屍痛哭。張光熾的慘死,的確對郭雨新造成非常大的打擊。
郭雨新也曾談過當時經歷此類事件心裡的感受,他說:「……乃至於加我『分歧』之名,視我形同『叛逆』,長年監視,多方打擊,雨新既以獻身台灣社會為職志,早已置個人死生於度外,自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孰料!『射將先射馬』,既不欲陷老朽於囹圄,偏移禍於左右股肱,自1960年籌組台灣民主黨至1975年《台灣政論》創刊,立委增選以迄今,此其間,多少與雨新有所切磋之仁人志士,或羅織入獄或橫遭摧折或亡命海外,雨新縱身免,然眼見四圍生離死別,寡妻弱子,呼天搶地,觸目驚心,如同刀割!而白髮哭少年,雖欲哭而無淚,但無語問蒼天!此情此景,歷歷在目,錐心刺骨,痛不欲生!
當前熱搜:最大「內鬼」逃往以? 被處決? 網傳伊朗聖城旅指揮官卡尼涉摩薩德間諜案
至於賴茂輝為了賣打字機跟鐵櫃吃官司,張金策為了五千塊錢路燈吃官司,兩個後來都流亡海外。
葉煥培則在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在宜蘭親自勸他選省議員以打擊郭雨新不成後,當他從宜蘭跑到台北考選部作完檢覈,要趕回去登記的時候,在礁溪火車站被黨國特務拖下去軟禁到拖過登記的時間。之後,不到一個月就吃官司了。
最後林義雄因緣際會接下郭雨新的棒子。
當前熱搜:上午才求幫忙撤離外交官 伊朗下午轉頭就轟炸! 「這國」總統怒嗆要復仇
林義雄和郭雨新是這樣認識的,林義雄回憶說:「我和郭先生認識是在大學時代,在宜蘭學生會的活動裡。當時他做省議員,而那只是普通一個同鄉後輩和同鄉前輩的認識而已。那時候只知道他是一個省議員,事實上我自己本身對民主意識或是台灣政治環境並不瞭解。我對他比較認識,是在1975年的立法委員選舉。當時他請我和姚嘉文做選舉期間的法律顧問;接下去又為抗議這場選戰的不公打官司,我們做他訴訟的代理人,才有較多的接觸。競選期間做法律顧問,事實上還是以一個律師的身份和他一起工作,而且也是他忙他的,我們忙我們的。我們在法律方面提供的意見,也不很多。後來他選舉落選了,打官司時才較常在一起。之後,官司打完了,因為同鄉的關係,同時我對選舉感到有興趣,想要更加深入參與宜蘭的政治運動,所以我就有更多的時間和他在一起。他要出國那年(註1977年),好像三、四月,他有一次帶我回宜蘭拜訪他這些老朋友──我們一般說樁腳。差不多幾天時間,我和他一起去看他這些老朋友。之後他就出國,在美國期間和我偶而有書信來往,還是算做很平常。我跟他的來往很平凡,時間不長,公事的來往較多。出國之前帶我到宜蘭繞一繞,可能也有這個意思—─讓我瞭解這些人,我若要參與政治,或許這些朋友會幫忙。差不多是這個意思,並沒有很深的私交。」
當林義雄從事《虎落平陽》的寫作時,選舉的經過常像電影的特寫鏡頭似的,一幕幕不斷湧現:著急、焦慮、悲憤、無助、木然、無奈各式各樣選民的臉,清晰強烈地衝擊著他。尤其當他想起那些由憤恨、不平所化成的,震天如雷煙硝滾滾的鞭炮聲時,他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他所看到的是一股驚天動地的偉大力量。那些平時默默工作,天天忙著討生活的百姓,絕不是可以任予宰割的羔羊;有一天,他們終將厭倦一再地容忍,他們終將為最基本的是非奮爭。如果不告訴他們並給他們合理爭是非的途徑,那麼有一天終會發生不忍睹的慘象。什麼是合理爭是非的途徑呢?林義雄認為是「法治」。而法律是由誰來制定?林義雄認為法律必須由國民公意來決定,否則法律不過是統治者的命令,跟他們擁有的刀槍一樣,都將成了桎梏人民的醜惡工具;只有在一切政策、法律取決於國民公意的「民主」國度裡,才有資格談法治。「民主法治」一再地在林義雄的耳際迴響,可是它會從天上掉下來嗎?林義雄心裡這樣想著。選民的臉,選民的心,民主法治的理想,各種各樣的問題,在他寫《虎落平陽》的幾個月裡,始終在腦海裡激盪。有一天,他終於領悟到:有些事情必須有人去做,更重要的是必須有人領先去做。他想起「笨鳥先飛」的老話,決定不再明哲保身,因此在《虎落平陽》的後記裡表明了他的基本政治理念和從政的決心—─「鄉先輩郭雨新先生競選立委,乃慨然受聘擔任其競選期間之法律顧問及選舉官司之訴訟代理人,並因此得能體驗全盤選戰及訴訟之經過,深覺所謂民主法治,非僅未在此土生根,且其初生之嫩芽,仍隨時可能橫遭摧殘毀滅,有識之士,如仍自甘緘默,以明哲保身為戒,則勢危矣!」
1977年4月郭雨新流亡美國,同年11月林義雄決定繼承郭雨新在宜蘭縣的民意基礎,投入臺灣省議會議員競選。在宜蘭縣民眾對於郭雨新的支持以及為郭雨新討公道的熱切要求下,林義雄在宜蘭縣獲得了73,000多票的第一高票成績、遠遠超過國民黨提名的兩位候選人而當選第六屆省議員,宜蘭黨外在郭雨新被迫棄選第五屆省議員後,終於重新鞏固住原本的半壁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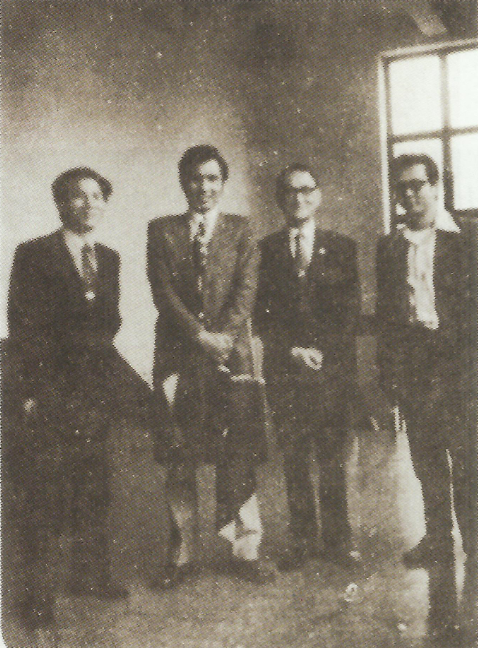
林義雄、姚嘉文合著《虎落平陽》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