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與仇恨:患病的不是肉體而是心靈
當前熱搜:美3架F-15E戰機墜毀! 美軍中央司令部:遭友軍科威特防空部隊誤擊
“武漢義務送藥人被舉報賺差價”——《新京報》的一則報導,日前引發關注。二十五歲的中學實習物理老師吳悠在武漢封城後的一個多月,騎著電瓶車為網上求助者特別是一些孤寡老人義務送藥。花清瘟、口罩、酒精等物資都是免費送給求助者,奧司他韋、阿比多爾等稍貴一些的藥品則收取低於市場價的費用。吳悠和朋友們為六百多戶求助者送去藥品和防護物資,他自己投入上萬元儲蓄。然而,吳悠卻被人以非法售藥和牟利舉報,並接受公安機關調查。在配合調查期間,吳悠的奶奶因腦溢血昏迷,被送進醫院。
“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證”,跟北島原作中膚淺的樂觀主義相反,這才是中國的現實。在這場瘟疫中,吳悠不是第一個被傷害的好心人。武漢火神山醫院開始建設時,正是無數人拼命逃離武漢之時,建築工人張元二話沒說就報了名,從老家“不怕死”地來到武漢晝夜施工。可工期結束,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卻被全村的人擋在外面,理由是:從火神山來的,是高危人群。這個勇敢的逆行者,被與確診及疑似病人隔離在一起,之後的命運如何,不得而知。
遼寧有兩名普普通通的貨車司機,在網上看到雲南有大批蔬菜要支援武漢,向社會徵尋免費運輸車的消息,直接從貴陽駕車到雲南裝貨,又風塵僕僕地運到武漢協和醫院。卸了貨,顧不上休息,又啟程回到雲南繼續裝貨。十二天,往返雲南武漢之間三次,行程一萬兩千萬公里,分文不取,還倒貼五萬元油錢。當他們終於回到家鄉,希望好好歇息時,卻被鄉親們罵“瘟神回來了”。
現正最夯:伊朗宣布封鎖荷姆茲海峽!美國情報單位評估水雷數量驚人
疾病帶來恐懼,恐懼滋生仇恨。在武漢肺炎席捲全球之際,很多人想起法國作家加繆的名作《鼠疫》。而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的《失明癥漫記》卻無人談及。《失明癥漫記》是一本虛構和想像的預言,武漢肺炎宛如其現實版本。
《失明癥漫記》是這樣開頭的:繁忙的路口,綠燈亮了,中間車道的頭一輛汽車卻停止不前,司機在擋風玻璃後面揮舞著手臂,圍觀的人打開車門之後,才聽到他在喊:“我瞎了!”沒有人會相信,因為他的眼睛清晰明亮,鞏膜像瓷器一樣潔白緻密。他卻一再絕望地喊著:“我瞎了!我瞎了!”一位偷車賊假扮好心路人送他回家,順便偷走了他的車。在開著這輛偷來車離開時,偷車賊卻被傳染上了失明的怪疾。第一個失明者由妻子帶著去看眼科醫生,眼科醫生成了第三名犧牲品。失明癥迅速蔓延,整個城市陷入一場空前的災難。普通的盲人眼前是一片漆黑,這次的失明癥卻讓失明的人眼前是濃濃的白色,彷彿睜著眼睛沉入牛奶的海洋中。白色的黑暗比黑色的黑暗更加可怕,正像薩拉馬戈追問的那樣——誰告訴我們這種白色眼疾不正是一種靈魂疾病呢?
文學評論家哈樂德·布魯姆指出:“《失明癥漫記》是薩拉馬戈最令人吃驚和不安的作品。他那極具說服力的想像震撼人心,讓讀者深刻意識到,人類社會竟是如此脆弱、荒誕。這部作品必將永存。”《柯克斯書評》評論說:“與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卡夫卡的《審判》並駕齊驅。”《泰晤士報》則評論說:“薩拉馬戈成功地刻畫了人類的缺陷,創造出當今世界最卓越的一部作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部驚人的現實主義作品,我們在“歲月靜好、閒來無事的悲劇”中麻木不仁太久了,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居然如此荒謬。

關押與槍殺:當病人成為敵人
失明癥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現的海潮那樣洶湧澎湃,拉枯摧朽,淹沒一切,而是如同千萬條涓涓細流緩緩滲透,逐漸把土地泡軟,突然間把它變成一個澤國。
政府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處理這一公共衛生危機。薩拉馬戈模糊了故事的背景,沒有明確指出是哪一個國家的政府,讀者可以聯想到任何一個他們不喜歡的政府。不過,從書中政府對軍隊高度依賴的情節可以看出,作者融入了自己在葡萄牙獨裁政權之下生活大半輩子的經驗。衛生部長的助手,以其豐富的想象力,用中性的“白色眼疾”代替難聽的、讓人談虎色變的“失明癥”——正如現實生活中,中國政府堅持聲稱“武漢肺炎”帶有歧視意味,而操縱世界衛生組織改名為“新型冠狀病毒”。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堅持使用“武漢肺炎”這一名詞,並非無意為之。
委員會經過討論得出解決方案:在找到處理和治療失明癥的方法之前,把所有失明者,包括與之有肉體接觸或直接聯繫的人,統統收容起來加以隔離。隔離在哪裡呢?衛生部長建議說,正好有一所廢棄的精神病院。於是,失明的男男女女都被運到精神病院。
病患剛剛進入各自的房間,廣播裡就傳來政府宣佈的十五條規定。其中第一條說得溫文爾雅,政府希望所有公民在此艱困時刻表現出愛國之心,與政府配合,遵紀守法,被隔離是一種支援全國其他人的行動。中國政府的修辭術比書中的政府更為加高明:中國政府自我表揚說,「現在我們應該理直氣壯的表示,美國欠中國一個道歉,世界欠中國一聲感謝,沒有中國的巨大犧牲和付出,就不可能為全世界贏得寶貴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時間視窗,可以說中國一己之力,硬生生的將新冠肺炎疫情擋住了很長一段時間,真的是驚天地、泣鬼神!」加害者變成拯救者,甚至不需要川劇變臉那一瞬間的招式。
第二條規定就殺氣騰騰了:“在事先未獲允許的情況下,離開所在建築意味著立即被打死。”那名偷車賊稀里糊塗地跨越了紅線,被一名緊張萬分的士兵開槍擊斃,成了第一個犧牲品。開槍的士兵擔心自己會受懲罰,長官卻表揚他當機立斷、殺人有理。一名團長在軍營中說,盲人問題只能靠把他們全都從肉體上消滅解決,包括已經失明和必將失明的人,無須假惺惺地考慮什麼人道主義,團長說的話與切除壞死的肢體以拯救生命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狗死了,它的狂犬病自然就治好了。
官員的地位越高,越是視人命如草芥。陸軍部長對衛生部長說,我們這裡有一位上校,他認為解決辦法應當是盲人一出現就隨即把他們殺死;以死人代替盲人不會使情況發生很大的改變;失明不等於死亡,但死人都是盲人。陸軍部長下令組織二百名公車司機去運送病患到隔離點,但他沒有告訴公車司機,等運完病患,官兵將奉命將司機們也關到裡面去。同一天傍晚,陸軍部長把衛生部長叫去,告訴衛生部長說:“你想知道件新鮮事嗎,我對你說的那位上校失明了。現在要看看他對原來出的主意怎麼想了。他已經想過了,朝自己頭上開了一槍,可見他的態度前後一致。這樣的軍人是好樣的。”這就是當局的真正意圖:“蟲子死後,毒汁也就完了。”病人都是敵人,要麼自生自滅,要麼被像韭菜一樣割掉。
不久,作為隔離點的精神病院爆滿,政府轉而主張由各家各戶把自家的失明者關在家裡。很快,全家都被感染,全家都變成盲人,沒有剩下一個人看護他們,給他們引路,保護他們不受眼睛還好的鄰居和其他人的傷害。最後的結果是:“不論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顧,他們只能像圖畫上畫的那樣,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
人與動物:不像動物那樣生活有多難?
“肉眼上的失明,代之以靈性的視域,足以補償。”這是荷馬、彌爾頓和博爾赫斯等偉大作家失明後的信念。他們堅信,失明或許是另一種光明的開啟,失明與一種超自然力量拉上關係。然而,在《失明症漫記》中,整個城市都失明了,社會沒有開啟“另一種光明”。社會秩序迅速垮塌,人類“下降”成為動物。
首先是被隔離者的脆弱的秩序迅速崩潰了。在什麼也看不見的情況下,人們開始隨地大小便。政府沒有向他們提供衛生紙,大便之後人人都不擦屁股——現實生活中,武漢肺炎引發了搶購潮,人們到超市哄搶的一個重要物質是衛生紙,看來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在廢棄的精神病院,就連擁有博士學位的醫生都不得不生活在自己和眾人的屎尿堆中,“他知道自己骯髒不堪,想不起一生中有什麼時候這麼骯髒過。人變成野獸有許多方法,而這是人變成野獸的第一步”。
人們為了尋找食物到處亂沖亂撞,一旦越線,就被在遠處看管他們的士兵射殺。到處是白色的耀眼的光,但人們就是什麼也看不見。伴著彌漫在空氣中的令人難以忍受的臭氣混雜,光似乎也散發出令人作嘔的氣味。“豬,一群豬。”有人終於忍受不了,如此吼道。精神病院夜晚的月光映襯著高聳的樓牆,冷漠陰沉的槍管,還有不斷的閃現在盲人白色視界中的晃眼的探照燈。這些失去的職業和身份的行屍走肉,還是人類嗎?薩拉馬戈冷靜地做出判斷:是的,他們是人,不過他們是一群失去視力的男人和女人。他們失去了人類的尊嚴,一半是冷酷無情,一半是卑鄙邪惡,最終使不幸變得更加不幸。
更可怕的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處境並沒有讓失明癥患者們彼此友愛、彼此扶持、彼此幫助。生病的不單單是眼睛,更是心靈。盲人的靈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無拘無束,脫離了軀體更能為所欲為,尤其是做壞事,盡人皆知,做壞事最容易。一夥盲人強盜入院後,以武力壟斷了政府配送的食品——士兵們只負責將食品放在大門口,究竟如何分配,是病患自己的事情。強盜們先是要求人們拿隨身攜帶的財物來交換食物,然後強迫女盲人前去“服淫役”。所有病房內的男性必須用妻子或情人的身體換來賴以苟活的食物。你吃的下麼?有人還保留一絲可憐的反思,但很快,所有人的耳邊都傳來極富穿透力的、低聲啜泣中不假思索地咀嚼麵包的聲音。
此一場景不禁讓人聯想到英國作家戈爾丁《蠅王》中的情節: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一群孩子逃到一座孤島上的生活。天真、善良、純潔的孩子們從熟悉的生活環境進入陌生的“異境”,到底會發生什麼變化怎樣呢?在荒島上,孩子們暴露出來的不再是天真、善良和純潔,而是瘋狂、邪惡和非理性。他們像成人一樣彼此廝殺。戈爾丁說,我們必須正視自己體內那隻動物,那隻邪惡的動物。這隻邪惡動物從我們生下來的那一天起,就潛伏在我們體內,隨時躍躍欲試,一不小心就會跳出來,控制我們的大腦。
第一位盲人暴君死於非命後,一名曾是會計的盲人取而代之——可見他們並非天生的強盜。這名盲人強盜頭子犯的最大錯誤是,他以為只要拿到手槍就大權在握,結果恰恰相反,每次開火傷害的都是他自己,每射出一顆子彈他就失去一些權威,子彈打完以後將會如何呢?薩拉馬戈不無輕蔑地寫道:“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執權杖的不一定是國王,最好不要忘記這條真理。”
要想不像動物那樣生活確實很難,但值得一試。醫生的妻子是唯一沒有患失明癥的人,為照顧丈夫,她假裝自己失明,跟丈夫一起進入精神病院。她看到並經歷了可怕的一切,當看得見眼前的痛苦已然變成一種負累時,當因視力正常不得不為其他的夥伴們的生死存亡負責時,她一度自我詛咒說,“還不如也失明了的好。”但最終,她仍然信仰“耐心有益於視力”,並耐心地行動著,照顧著身邊的六位盲人,教導他們“如果我們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樣生活,那麼至少應當盡一切努力不要像動物一樣生活。”他們活了下來,逃離了瘋人院,並熬到視力恢復的那一天。
人與上帝:沒有上帝,邪惡就是理所當然
薩拉馬戈在書中發出一系列的天問:“我們為什麼會成為現在的樣子呢?人類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歷程中,是從何時開始我們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或者說越來越缺少人性的呢?經過數千年之後,在創造了如何之多的美好事物之後,在對宗教和哲學進行了如此之多的探索之後,今天我們走到了這樣的一種境地:在與環境和其他人的關係中,我們不能真正成為人類,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薩拉馬戈是一名激進的無神論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員。他認為,這個世界要是沒有宗教的話,將會和平得多。但在小說中,他不斷地探討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尤其在其晚年的作品中,他更專注於寓言式的寫作,比如《失明癥漫記》,讀者很容易從中解讀出人類文明是何其脆弱的真相。那麼,救贖之道在哪裡?
有意思的是,《失明癥漫記》的扉頁,引用的不是馬克思的名言,而是聖經《箴言書》中的兩句話:“如果你看,就要看見。如果你能看見,就要仔細觀察。”薩拉馬戈沒有找到最終的救贖之道,但他至少是一名誠實且嚴肅的觀察者——只要還能觀察和記錄,黑暗,即便是白茫茫的黑暗,就不再是不可以戰勝的威脅。
薩拉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這樣的墓誌銘:“這裡安睡著一個憤怒的人。”無論在《修道院紀事》還是在《失明癥漫記》中,薩拉馬戈都對這個世界極盡抨擊和諷刺,之所以憤怒,因為他認為,“雖然我生活得很好,但這個世界卻不好”。他不像中國最後一位儒者梁漱溟那樣,在經歷了一輩子的政治苦難之後仍相信“這個世界會變好”,他對人性的認識比梁漱溟深刻。但他並未意識到,這個世界的“不好”其實跟每一個人、包括他自己息息相關,人人都難辭其咎,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在小說的結尾處,倖存者們逐一恢復了視力。醫生大聲疾呼道:“我甚至覺得比原來看得更加清楚,真的更加清楚。”他說出了大家想說但沒有膽量大聲說出來的話。武漢肺炎之後恢復自由和健康的患者和被隔離者們,會有這樣的生命頓悟嗎?這時,醫生的妻子哭了起來。“她當然高興,我的上帝,竟然如此容易理解,之所以哭泣是因為精神上的耐力突然用盡,她像個剛剛出生的嬰兒,發出尚無意識的第一聲啼哭。舔淚水的狗走到她跟前,這條狗總是知道人們什麼時候需要它,所以醫生的妻子把狗摟住。此時此刻她產生了強烈的孤獨感,只有這條狗如饑似渴地喝她的淚水才能減輕她難以忍受的孤獨。”這是這部長篇小說中讓人感動落淚的段落。重生的希望是愛,而不是其他東西。
薩拉馬戈沒有找到他的上帝,但他承認,在被隔離和被剝奪的、混亂且原始的情況下,宗教的必要性突顯出來。沒有誠實守規矩的人遵守一套秩序來生活,生存幾乎不可能。但手無寸鐵又同樣脆弱的人當中,難以找到一位正直的領導並且制定一套公正的規矩。大概只有在人們面對共同的敵人時,或擁有共同的信仰時,他們才能依偎著勉強生存下去。
失明癥、武漢肺炎、鼠疫、黑死病以及極權主義,本質上都是同樣的邪惡。加繆在《鼠疫》中寫道:“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最無可救藥的邪惡是這樣的一種愚昧無知:自認為什麼都知道,於是乎就認為有權殺人。殺人兇犯的靈魂是盲目的,如果沒有真知灼見,也就沒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愛。”習近平派到武漢的錦衣衛、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宣稱:“要在全市廣大市民中深入開展感恩教育,感恩總書記、感恩共產黨,聽黨話、跟黨走,形成強大正能量。”由此可見,比武漢肺炎更大的邪惡仍然籠罩在武漢、籠罩在中國。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和共產黨就是武漢肺炎,習近平和共產黨就是失明癥。武漢肺炎與失明癥誰更可怕並不重要,因為習近平和共產黨比它們可怕千百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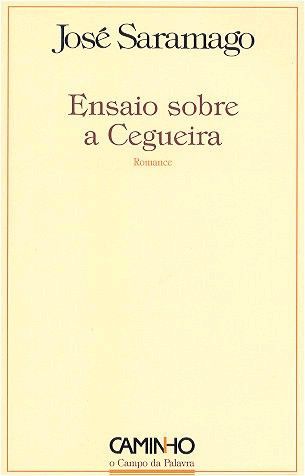
薩拉馬戈的小說失明癥漫記 圖:擷取自WI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