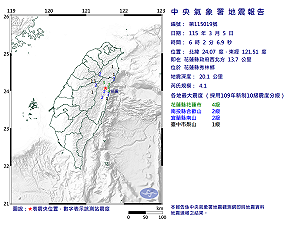香港淪為北京屠夫「路西法效應」的實驗室
我已經十年不能去香港了。十年前,我還不相信有一天自己不能踏上香港的土地。
全站首選:謝典霖稱是賴清德不讓謝衣鳳選 學者轟:國民黨是只會甩泥巴、製造仇恨的毒瘤
從二零零三年到二零一零年間,我差不多每年都有機會訪問香港,我的新書也在香港一本本地出版,政治評論集《中國影帝溫家寶》甚至有機會進入香港圖書獎的決選名單。然而,自從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案發生之後,香港的出版業全面崩壞,我再也無法在香港出版任何一本新書,也極少有香港媒體願意發表我的文章。
我沒有親身嘗試過自己能否入境香港,香港政府從未公佈過那張傳說中的“黑名單”。但是,我看到持美國護照的前天安門學生領袖周鋒鎖被香港海關拒絕入境,甚至暴力驅趕,身上留下傷痕,便決定不作這種無謂的嘗試。
短短二十年間,香港政府變得跟北京政府一樣“黑”。文明改變野蠻,需要幾代人的教育規訓、耳濡目染,香港花了一百年時間來學習大英帝國與新教文明的觀念秩序,才成為東方之珠;反之,野蠻改變文明,只需要短短幾個小時就能完成,北京只需動一根小手指,就能釋放無窮無盡的“平庸之惡”——你聽說過那個名為“路西法效應”的心理實驗嗎?今天的香港,不就是一個北京屠夫放大的實驗室嗎?
當前熱搜:又抓到內鬼?塔伊布見哈梅內伊後「身體不適」落跑 20分後導彈來襲 傳卡尼被吊死
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根據真實的實驗經過寫成《路西法效應:好人如何變成惡魔》一書,成為探討人性之惡的經典之作。一九七一年,津巴多在史丹福大學進行了一個心理實驗(即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他找來二十四名志願者,在模擬監獄內分別扮演「獄卒」和「囚犯」。本來實驗為期兩周,但獄卒穿上制服和手持警棍,並在教授示意可隨意運用權力去控制「囚犯」後,很快就失控。「獄卒」為求建立身份和地位,濫用手上的權力,不斷虐待「囚犯」,甚至使用令人發指的暴力。津巴多被迫提前終止實驗,他在書中承認:“人的個性氣質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麼重要,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的壓力會讓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後來,在根據本書改編的電影《史丹福監獄實驗》的宣傳海報上,寫著一句口號:「穿上制服,卻脫下人性!」這句口號,不正是今日香港的寫照嗎?
“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昔日深受市民愛戴的香港皇家警察,是亞洲最有效率也最有法治精神的警隊;如今,這支高度專業化的隊伍,已淪為黑警,跟中國窮凶極惡的國保警察並列,亦宛如希特勒蓋世太保的升級版——虐待、強暴、殺人、毀尸滅跡,連十二歲的孩子、十月懷胎的孕婦和白髮蒼蒼的老人都不放過。香港警匪片的編劇和導演們,一定會為自己太過缺乏想象力而感到羞愧。曾被譽為香港歷史上最傑出電影的《無間道》系列,講述了一個黑社會與警隊互相派出臥底的故事,此類故事在香港警隊整體將身份轉化為黑社會的現實面前黯然失色。誰又能想到,香港民調會顯示,超過半數的市民都給警隊評分為零,七成以上的市民呼籲解散並重建警隊?
此時此刻,需要重溫一九八八年劉曉波在第一次訪問香港時,接受香港媒體人金鍾訪問時的一段話。金鍾問劉曉波,中國何時能夠實現現代化,劉曉波回答說:“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可以說,這些年來,我的香港論述就是圍繞這一中心思想展開:去中國化,是香港絕處逢生的希望所在。
香港人唱自己國歌:《願榮光歸香港》
我雖然不在抗爭的現場,但我在精神上與香港抗爭者同在。
我是看香港電影和電視劇、聽香港流行歌曲長大的,對於香港,自然要“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我是右派和獨派,跟劉曉波和奈保爾一樣擁抱以英語文明為主體的“普世價值”,當然將那些高舉米字旗和星條旗的香港人視為“同路人”。多年來,我一直關心香港議題,寫了諸多關於香港的評論文章。如今,這些文章終於可以結集成《香港獨立》這本書了。
我是最早思考香港獨立這個議題的、具有中國背景的知識人之一。記得二零零三年第一次訪問香港時,見到香港泛民陣營的前輩們,直截了當地向他們詢問港獨議題。無論是支聯會創始人、德高望重的司徒華,還是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無論是崇拜恐怖分子切·格瓦拉並自稱托派的“長毛”梁國雄,還是後來占中運動發起人、港大法學教授戴耀庭……他們個個大搖其頭說,港獨不可能,在香港有港獨“妄想”的人屈指可數。他們都是廣義的“大中華主義者”,對觸手可及的“民主中國”以及香港在中國民主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都抱有極其樂觀的想像。
然而,在二零一九年夏天開始的反送中運動中,奇跡出現了。本土派、勇武派、港獨派,雨後春筍,前赴後繼,風起雲湧。香港的年輕一代,不再是“左膠”或“大中華膠”(有趣的是,這兩個名詞都誕生自香港,「膠」源自香港網絡術語「硬膠」,帶有愚蠢、思維僵化之意,而「硬膠」是粵語髒話「戇鳩」的諧音)。他們發現了一個常識:古往今來,從來沒有一個自由邦能長存於極權帝國的繈褓之中,一國兩制是拌了蜂蜜的毒藥。所以,他們的口號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他們不迴避使用“光復”這個名詞,香港既然需要“光復”,就說明她目前處於北京政權的“再殖民”或“劣質殖民”(相比於英國的“優質殖民”而言)狀態;他們更不害怕使用“革命”這個名詞,以“革命”自詡的中共,在香港人眼中卻是壓迫者及革命的對象,歷史充滿了弔詭與反諷。
這場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逆權運動,也誕生了自己的“革命歌曲”。我剛剛撰文指出,在運動中廣為傳唱的、音樂劇《悲慘世界》中的知名歌曲《你有聽見人民的聲音嗎?》(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可以成為未來香港的國歌,港人就創作了一首可以成為國歌的本土歌曲:《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詞曲創作均匿名,在抗議者常去的網路論壇上被反復修改,它與國歌的常見特徵一樣,伴奏以銅管樂器為主,昂揚抒情,包括「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這樣的歌詞。有一位香港抗爭者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我一生都在等待一首像《願榮光歸香港》這樣的歌。……隨著人們持續在大街上、商場裡倔強地唱起這首歌,還有什麼比它更能代表我們這場無人領導的運動?香港人有慧耳,也有善心。當一首真正代表我們身份的歌曲響起,我們會知道。願榮光歸香港。”
是的,願榮光歸於香港,這首歌詠唱的正是我在這本書中反復強調的主題:香港不是早已被中共馴化的北京、上海、廣州或深圳,香港如同雅典、耶路撒冷、日內瓦和但澤,是一座充滿榮光、擁抱大海的自由之邦。香港人比表面上已經獨立的新加坡更獨立:新加坡不過是李光耀家族經營的一所幼稚園,李顯龍有什麼資格對香港人以一城敵一國的自由之戰指手畫腳?沒有人能奪走香港人的自由之心,即便威脅要將“分裂分子”全都“粉身碎骨”的習近平也不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