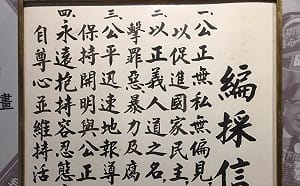現代版的《狂人日記》
六四屠殺十五週年的時候,哈金出版了以六四為主題的長篇小說《瘋狂》;六四屠殺三十週年的時候,《瘋狂》仍是惟一一本以六四為主題的高質量、有影響力的長篇小說。十五年前,哈金接受訪問說,六四到今天已經十五年,不僅真相遲遲未有報告出爐,連紀錄六四的文學也沒有!如今,又過了十五年,哈金的遺憾仍未被填補。那場屠殺短短數日就結束了,但對屠殺真相的遮掩、篡改和扭曲卻整整持續了三十年,對天安門母親群體的打壓、監控和侮辱也整整持續了三十年。
六四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哈金回憶説,「天安門事件對我的震撼太大了,使我移居美國,改用英語寫作」。《瘋狂》的初稿,早在一九八八年哈金留學美國時便完成,卻因不滿意而擱下。隔年天安門事件爆發,促使他作出「留在美國,以英語寫作」的決定,也決心將這種「民族的瘋狂」寫入書中。經過十六年、三十遍的修改,哈金終於「覺得有能力完成這本書」,將《瘋狂》完稿。這本書出版之後,哈金在美國波士頓家中接受臺灣媒體的越洋電話採訪時激動地説:「這是我第一本想寫的小說!」
《瘋狂》的三個故事
《瘋狂》仍舊是哈金式的主題:個人與集體、教條與自我價值、忠誠與背叛的衝突。故事描寫六四前夕,中國北方某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生萬堅,被系裡安排到醫院照顧指導教授和凖岳父楊教授。中風的楊教授逐漸進入瘋狂狀態:經常對著看不見的人求饒、辱罵賢慧的妻子、抗議學校的不公……萬堅一步步陷入楊教授的過去,被迫重新思考身為中國知識份子的處境。《瘋狂》同時講述了三個故事:一是楊教授的失常,二是萬堅的憂慮和覺醒,三是「六四」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小說開始於楊教授個人的瘋狂,結束時是整個民族的瘋狂,可以説是魯迅開啓五四新文學的代表作《狂人日記》的現代版和升級版。
當前熱搜:綠營高雄市長初選封關內參民調曝光 「他」奪雙冠領先
在醫院這個特殊的空間裡,楊教授不再害怕「因言獲罪」,而將心裡隱藏多年的秘密全都洩漏出來。這段故事部分是哈金的親身經歷:一九八二年,他在山東大讀研究生時,研究所裡一位教授突然中風,住進醫院。醫院沒有足夠的護理人員,哈金等幾個研究生被派去照料教授。哈金在醫院的那兩個下午,那位教授不停地胡言亂語,說出了很多平時不會說的真話與秘密。哈金對此感到非常震撼,想起了巴爾扎克在小說《高老頭》裡的話:「我們的心靈是一座寶庫:如果你將其中的財寶花掉了,你就會毀於一旦。人們不能寬恕一位真情橫溢的人,正如人們不能容忍一個身無分文的人。」
魯迅筆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況,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到中國旅行的愛因斯坦也有一番精準的觀察。愛因斯坦在日記中寫下了好幾段被後人視為涉嫌「種族歧視」的評論:在中國,他看到了「勤勞、骯髒、遲鈍的人」,「就連那些淪落到像馬一樣工作的人,似乎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痛苦。特別像畜群的民族……他們往往更像機械人,而不像人」。
魯迅常常用「僵屍」和「鬼」的意象形容自己的同胞,他在《狂人日記》中譴責中國古已有之的「食人主義」,在中國,反抗者常常被「平庸之惡」所吞噬。魯迅是悲觀的,用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話來說,「他對光明的信念最終未能驅散黑暗」。而在哈金這裡,要逃離像楊教授那樣最終走向「瘋狂」的命運,惟一的希望就是離開這個瘋狂的國度,正像哈金在詩歌中所説:「你看,碼頭上的腳步多麼沉穩/看那些離港的海輪/它們都要負重才能遠行。」惟有到了大洋彼岸,人才能成為人,自我才能成為自我,「你看,這滿天的星/哪一顆不是獨自明滅?」
中國沒有「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知識分子
據小說主人公萬堅所聞,楊教授的猝然病倒可能起因於他和系領導之間瑣碎的衝突:一是系主任宋教授嫉妒楊教授的學術成就,在其提升正教授的事情上製造一系列障礙;二是楊教授赴北美做短暫的學術訪問回國後,彭書記要讓他自付往返的旅費。正如《等待》中那個等著辦離婚和再婚手續的軍醫一再遭受有關上級的拖延,《池塘》中等待分配住房的工人因拒不行賄而備受主管幹部的刁難,楊教授也遭遇書記和主任給他穿小鞋的麻煩,陷入卡夫卡式的「城堡」之中。哈金一直在寫芸芸眾生「渺小的不幸」,他們在面對如魯迅所説的「無物之陣」時,只能表現為怯懦與恐懼。在中國,那種陰溝裡的臭味,四處彌漫,如影隨形,人人身上都沾滿了這樣的氣味。最終,人的精神承受不了這種腐爛的氛圍,在長久的忍耐之後爆發為瘋狂。
楊教授發瘋的表現之一是:在昏迷中高唱毛時代的紅色歌曲,背誦毛語錄,都都囔囔地重復《人民日報》社論中的陳詞濫調,並以首長的口氣發表演說、宣講政策,大言不慚地向虛擬的聽眾宣告從政當官的宏願。中國是一個「高壓鍋」社會,在嚴峻的生存壓力之下,各個階層的人都患有或輕或重的精神疾病,只是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將其精神創傷深深隱藏起來,只有少部分人由於某種契機的誘發而爆發——比如發病(發瘋)的楊教授,比如跑到幼稚園去殺孩子的暴徒,比如逃進美國領事館的薄熙來的打手王立軍,比如那些在廣場上唱紅歌和跳忠字舞的大爺大媽。
不過,在楊教授的瘋言瘋語中,也包含著不少真知灼見,就好像《世說新語》中那些精彩片段,中國人的真話只有在佯狂的狀態下才能說出來。楊教授滔滔不絕地批判中國社會的種種亂象,更犀利地批判包括自己在內的知識份子的奴性:「中國哪有知識份子?笑話﹗誰受過大學教育,就叫做知識份子?事實是,人文學科的所有人都是小職員,理工科裡的所有人都是技術員。告訴我,誰才是真正獨立的知識份子,那種又有獨創性思想又講真話的人?我一個也沒見過。我們都是國家的啞吧勞工——是退化的人種。」
楊教授與萬堅,象徵著中國兩代知識份子的悲劇與反抗。故事的場景幾乎都發生在醫院,象徵著兩人精神上的「孤絕」處境。「當時稍微有思想的人,都處於孤絕的狀態。」哈金如此形容一九八○年代的中國。他藉半瘋的楊教授指出中國的真相:在那樣一個「沒有獨立的人、獨立的腦子」的時代,根本沒有知識份子生存的空間。
一九八○年代後來被人們在回憶中不斷加以美化,哈金卻並無玫瑰色的浪漫想像。哈金不是因為六四屠殺才逃離中國,他與高行健一樣,在六四之前就選擇了離開。他們都比劉賓雁式的、「第二種忠誠」的愛國者更敏感、更自由主義和更個人主義。哈金在一首詩中寫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放鬆些吧。/別沒完沒了地談論種族和忠誠。/忠誠是條雙向街。/為什麼不談談國家怎樣背叛個人?/為什麼不譴責那些/把我們的母語鑄成鎖鏈的人?/這條鎖鏈把所有不同方言/禁錮在執政的機器上。/是的,我們的語言曾經像條河,/但現已萎縮成一個人工池塘,/你被困在其中,半死不活,/像寵物一樣去服從和取悅。/所以我寧可在英語的咸水裡/以自己的速度爬行。」
天安門屠殺讓中國失去心靈的鑰匙
小說的前半部分是楊教授的故事,後半部分才是萬堅的故事——當北京的學生們佔領天安門廣場之後,萬堅逃離陰沉死寂的醫院,到北京加入到那場疾風驟雨的群眾運動之中。哈金曾研究許多天安門的資料,卻因自己沒有親身經歷,怎麼寫都不滿意,「我們不能在死者的屍體旁指手畫腳!」哈金將小說改成萬堅在北京迷了路,目睹北京人民阻止軍隊進城的過程,卻沒真正走上天安門,他認為如此「能做到可信,而且負責任」。
其實,哈金的這種寫法並不僅僅是因為他不在現場、不是親歷者。雨果也不在好幾場巴黎的革命或暴動的現場,卻可以得心應手地寫出以革命為背景的《九三年》、《巴黎聖母院》和《悲慘世界》,作家是否在歷史事件的現場並非最必須的要素。哈金避開當年事件的中心天安門廣場,因為他不單譴責中共的屠殺,而且反思個人在群眾運動中的迷失:中國為什麼不能有個人的意志和個人的聲音?就天安門的那一代學生而言,他們尚未驅除文革及整個中共極權主義統治留在他們精神深處的毒素。他們作出將向毛澤東畫像潑墨的湖南三勇士「扭送」公安局的決定,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史上一個最大的汙點。
美國小說家耐爾·佛魯登伯格(Nell Freudenberger)在《紐約客》上發表了一篇關於《瘋狂》的書評,名為《中國盒子:有關天安門時期的瘋狂和回憶》。文章認為,《瘋狂》的最後幾章內容和前面有些游離:前面是醫院病房裡的幽閉性瘋狂,這幾章卻是劇烈的實質的運動性瘋狂。小說從「醫院」(「瘋人院」)到「廣場」的場景及氛圍的轉變,過於突兀,讓讀者猝不及防,前後兩部分有斷裂之勢。主人公萬堅決定去北京參加運動,目的迥異於別的學生,「我沒有什麼崇高的目的,也不憂患國家的存亡。我去參加運動的動機十分私人化:絕望、憤怒、瘋狂和愚蠢驅使我作出了這一決定」。佛魯登伯格認為,哈金描述廣場四周的氛圍時,似乎不如表述萬堅在醫院的所思所想得心應手:對話描寫更像義大利式西部片對白。比如,一個抗議者喊道:「入夥兒,趕快逃命吧!」一位軍官則威脅地吼道:「我要幹掉所有你們這些流氓!去你丫的!」
作家、文學評論家康正果則認為:「以見證六四屠城的場景作為情節推進的高潮,乃是哈金鬱然勃發的文氣勢所必至的結局,絲毫也不顯得牽強。
那是人神共憤的慘烈,敍事中不可或缺的史筆。瘡熟了,要流膿,這就是當時的情勢,也是敍事的走勢。」康正果如此分析學生的精神資源的貧乏和當局決定屠殺的必然性:「一方面,文革中挨過鬥的老人集團一直都在磨刀等待開殺戒的時機,他們本來就憋了一肚子膿水。另一方面,文革中的造反之舉沒能徹底完成,更讓後來的學生遺憾得不願善罷罷休,他們懷舊當年的抗議手段,急欲再掀起一場人民的盛大節日。新的對抗中裹挾了太多舊時失效的激情:絕食靜坐流於饑餓表演,攔阻軍車的舉措以慰勞大軍的形式施行,好像孩子去點響嚇唬人的花炮,結果卻引爆了血肉橫飛的遍地爆炸。」無論是高行健的戲劇《逃亡》,還是哈金的小說《瘋狂》,以及康正果的這段評論,都點出六四學運在思想上的空洞:大學生普遍用共產黨的語言、思想和方法來對抗共產黨。後來很多學生領袖到了西方之後,諸多共產黨員式的表現令人瞠目結舌。
天安門事件是整個國家失去了心靈的鎖匙,失去未來的盼望,失去善與美的信仰。從此,絕大部分中國人被暴力和謊言徹底征服,成為「奴在心者」。對於六四之後「為奴三十年」的中國人,哈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在極度的厭惡中又不乏同情與悲憫之情,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我可憐那些熱衷於安全和統一之輩。/他們滿足於生活在地窖裡,/在那裡飯菜飲料都是現成的。/他們的肺不用於呼吸新鮮空氣,/他們的眼睛在陽光下模糊不清。/他們相信最糟糕的活法/也勝過於及時的死亡。/他們的天堂是一桌宴席。/他們的贖救取決於一個強權者。」
殺人和吃人的國家,不是值得眷戀的祖國
小說的結尾處,萬堅燒掉學生證、決心離開故鄉,象徵知識份子的覺醒。真實生活中,哈金表示,《瘋狂》寫到了他「留在中國的末期」,萬堅的「離開」可視為他跨出「寫中國故事」的象徵。他未來有兩個寫作計畫,一是寫韓戰時期的中國人,一是美國境內的新移民故事,都不再局限於寫「中國土地上的中國人」。果然,後來哈金寫出了韓戰題材的小說《戰廢品》和新移民的小說《落地》。
與余英時一樣,哈金也是一個沒有鄉愁的人。「美國人看我是中國作家,中國人看我是美國作家。」以英語寫中國故事的哈金,感慨自己是「處於模糊狀態的作家」。哈金認為「鄉愁」是被媒體過度演繹出的概念,很多人都沒有家,談何「鄉愁」?「大夥兒都覺得有鄉愁的感覺,但是這不是對家的想念,而是對我們本身、對於生命中流失的東西挽不回來的遺憾。」他舉例《我的安東尼亞》中父親之因為思念家鄉而自殺,並不是鄉愁而是語言困境,「這跟鄉愁沒有關係的,是他整個人的參照系統都沒有了,這才是最大的恐懼。鄉愁不是恐懼最大的原因。我有鄉愁,但是我必須保持頭腦清楚,我不知道我的家鄉在哪兒。」當讀者提問哈金的「家」在哪裡時,哈金回答說,是美國,「空間上這裡就是我的家,因為現在我住在這裡」。另一層面,對於一個寫作者,「寫作就是我的家園」。
哈金曾與臺灣作家吳明益有過一場對話。吳明益問他説:「您曾提過,懷舊之情與渴望出發既是相對的,又是相連的。雖然您小說中的人物都是中國人,但您往往傾向於去描寫這些人將要抵達什麼地方,而非回歸某處。」哈金回答説:「這是受現代文學的影響。……在康拉德的小說中,他引用史詩《奧德賽》中的經典段落,寫奧德賽回到他朝思夢縈的家鄉卻給嚇壞了,荒蕪的土地,猙獰的人民,他回到家反而感覺荒蕪,因為他已經沒有家了,回歸是沒有意義的。從現代情境上來看,我們的家鄉都失落了,家鄉就在眼前,卻僅僅是某種渴望;在中國尤其明顯。所謂的思鄉,只是對自己生命中所流失的部分的眷戀之情,就像一個人愛上另一個人,往往是愛著自己的愛情本身。」哈金此前早已借《自由生活》的男主人公武男,道出對「祖國」的複雜情緒:「有一天他終於回到了心裡掛念的家鄉,見到了父母和家鄉的繁榮,他開始不明白:‘為什麼那麼多海外華人,退休後要回到這個需要賄賂和宴請他人,才可以辦成事情的瘋狂的國家。’很顯然他已經不能再適應這樣的生活。現在他更想活在美國、生在美國了。」
回歸是一場災難,無論是作為城邦的香港對中國的回歸,還是海外華人對中國的回歸;反之,離開才是自由的開端,惟有精神上擁抱自由的人,惟有「成為你自己」、建構起獨立人格的人,才能在異國他鄉幸福並快樂著,如蘇東坡所言「此心安處是吾鄉」,也如哈金所説:「你回不去了。/看,大門在你背後關上了。/對於一個從不缺少公民的國家,/你同其他人一樣,可有可無。/你會徹夜難眠,/困惑不解,想家,默默哭泣。/是的,忠誠是一個騙局,/如果只有一方有誠意。/你將別無選擇,只好加入難民的/行列,改換護照。//最終你會明白,/生兒育女的地方才是你的國家,/建築家園的土地才是你的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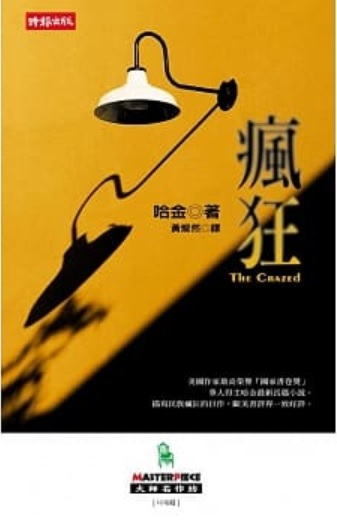
哈金《瘋狂》。 圖:翻攝自博客來官方網站